李隆基即位之初,为了立威,就在骊山阅兵仪式上,说是军容不整,找茬杀掉宰相郭元振,这可是当年和狄公掰手腕的大佬呀,四朝元老,经略西域,镇守雍凉,文武全才,刚正不阿,群臣自然纷纷求情。 那日骊山的风裹着寒意,吹得旌旗猎猎作响。郭元振被亲兵按在阅兵台前,花白的胡须在风中乱颤,身上的紫袍沾了尘土,却依旧挺得笔直。他望着高台上那个年轻的皇帝,眼神里没有恐惧,反倒带着几分惋惜——当年跟着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走过来的老臣,谁没见过朝堂风波?可借着阅兵杀人立威,还是对着他这样的肱骨之臣,未免太急了些。 兵部尚书率先跪了下去,膝盖砸在冻土上“咚”的一声。“陛下!郭相镇守西陲时,曾率三千骑兵大破吐蕃十万之众,护得河西走廊安稳十年!仅凭‘军容不整’四字就要问斩,寒的是天下将士的心啊!” 他一跪,跟着跪倒一片。文官们摘下乌纱帽,武将们按着腰间的刀柄,没人敢看高台上的皇帝,却都用沉默较劲——这刀要是落下去,往后谁还敢替朝廷卖命? 李隆基坐在临时搭建的观礼台上,手指敲着扶手。龙袍是新做的,料子挺括,却衬得他脸色有些发青。他刚从太平公主手里抢过皇权,朝堂上一半的官员都是前朝旧人,说话做事总带着“你年轻不懂”的怠慢。他需要一场“震慑”,让这些老家伙知道,如今坐在龙椅上的是谁。 可郭元振……他毕竟是郭元振。李隆基想起小时候,曾在御花园见过这位大臣,当时他刚从西域回来,身上带着风沙气,给武则天献的西域地图,摊开能铺满半间殿。那时候的郭元振,眼神亮得像星星。 “军容不整,便是军纪涣散。”李隆基的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却带着刻意的冷硬,“军纪涣散的军队,如何保家卫国?郭元振身为宰相,难辞其咎!” 郭元振忽然笑了,笑声在空旷的阅兵场里格外清晰。“陛下要立威,臣懂。”他抬起头,目光穿过人群,直直落在李隆基脸上,“可威不是杀出来的。当年臣在凉州,有小兵偷了百姓的鸡,臣没杀他,让他跟着商队跑了三个月腿,赔了十倍的钱。后来那小兵成了戍边的百夫长,带出的队伍比谁都守规矩。” 风更紧了,吹得观礼台的帷幔猎猎作响。李隆基的手指停在扶手上,指尖泛白。 “陛下可知西域的胡商怎么说?”郭元振继续道,“他们说,见了郭元振的旗帜,就像见了长安的城门。这份信任,是臣用十年时间,一天一天熬出来的。不是靠杀人,是靠做事。” 有老臣偷偷抹眼泪。他们都知道,郭元振说的是实话。当年武则天晚年政局动荡,是他在西域稳住阵脚;唐中宗昏聩,是他顶着压力整顿边军;太平公主把持朝政时,也是他暗中给李隆基递消息,助他发动政变。 李隆基看着台下那片黑压压的头颅,忽然觉得龙椅有些硌人。他要的是“威”,可这些人跪的,分明是郭元振的“功”。 “陛下!”户部侍郎哽咽着开口,“去年关中大旱,是郭相亲自带人挖渠引水,三天三夜没合眼。他的手磨出的血泡,臣亲眼见过!” “陛下!”边将出身的将军朗声道,“郭相说过,将士的命是用来杀敌的,不是用来给陛下立威的!” 这话够冲,几乎是指着鼻子骂了。李隆基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握着剑柄的手松了又紧。 郭元振忽然喝止众人:“都住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哪来这么多废话!”他转向李隆基,深深一揖,“只求陛下杀了臣之后,能记得‘军纪’二字,不只是给别人看的,更是给自己立的。” 观礼台上静得能听见风吹过旗角的声音。李隆基盯着郭元振花白的头顶,想起昨夜太平公主的旧部在朝堂上阴阳怪气:“新皇年纪轻,怕是镇不住场面哟。”又想起郭元振前几日递的奏折,劝他“少用雷霆手段,多用怀柔之策”。 原来这老头,什么都懂。 他忽然站起身,龙袍的下摆扫过案几,把上面的茶杯带倒了。茶水泼在明黄的地毯上,像一摊深色的渍。“郭元振”,李隆基的声音有些哑,“你可知罪?” “臣知罪。” “念你有功于社稷,免去死罪。”李隆基顿了顿,一字一句道,“贬为新州司马,即刻启程。” 郭元振叩首谢恩,起身时踉跄了一下,被亲兵扶着往外走。经过观礼台时,他抬头看了李隆基一眼,那眼神里,惋惜少了些,多了点别的什么——像是期许,又像是担忧。 群臣山呼万岁,声音里却没多少喜悦。风卷着地上的尘土,迷了不少人的眼。 后来有人说,那天骊山的风,吹掉了李隆基的戾气,也吹醒了他的帝王心。他终究没敢动郭元振,不是怕了群臣,是怕了自己心里那点还没被权力磨掉的敬畏。 只是郭元振到了新州,没过半年就病逝了。消息传到长安时,李隆基正在批阅西域的奏折,看着上面熟悉的地名,忽然把笔扔了,对着空殿发呆。 他终究还是失了那位能和狄公掰手腕的老臣。而这场没杀成的“立威”,像根刺,扎在开元盛世的开端——提醒着后来的人,帝王的权柄再重,也该留几分余地给那些真正做事的人。 参考《旧唐书·郭元振传》《新唐书·玄宗纪》《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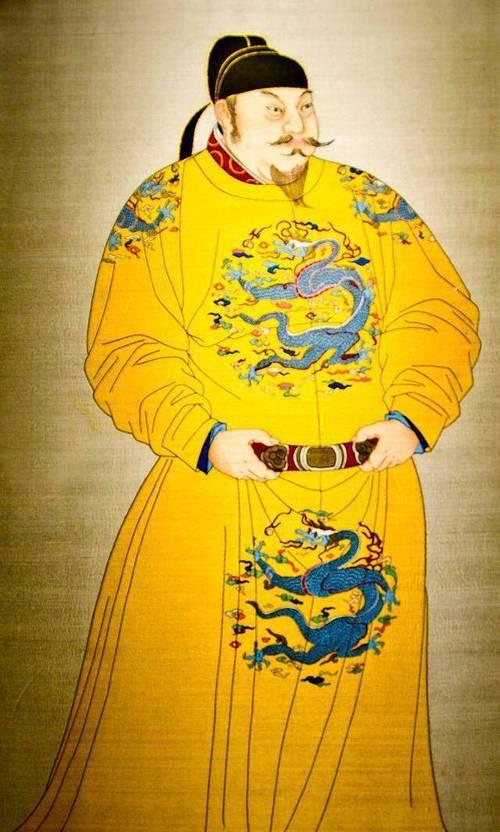



用户10xxx65
瞎编。 再说。夺儿子的老婆,导致安史之乱这两件事,唐玄宗已经永远被钉上了耻辱柱。历史上最昏的君之一。
模头 回复 08-21 10:21
不知道是不是瞎编,但你都说的事情都是之后的事情啦
坐望云起
这么说吧,被政变后他儿子居然没弄死这人渣也是能忍
贪吃的猫 回复 08-22 20:30
又不是被抢了老婆的那个儿子当皇帝,自然要留点脸面
似风的坎坷
一日杀三子的畜牲
铁马冰河
确实人品很差
昨昔遗老
逼死王忠嗣之时,可曾回想当初
出淤泥而不染
就一个二世祖,根本不懂经济民生,大臣为了压武则天才不断抬举他,结果一下就飘了,越来越昏庸无道。
用户16xxx88
李隆基就是活得太久了,以他的能力远不如活了五十岁的太宗皇帝,后期都是在胡搞乱搞,昏庸不堪,帝国最终毁在他手里。
闪闪红心
自媒体+AI=无法无天,历史都敢瞎编: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骊山讲武,郭元振因军容不整之罪被流放新州。后唐玄宗思其旧功,又起用他为饶州司马。但郭元振遭此挫折,心情抑郁,最终在赴任途中病逝,终年五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