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一天,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裘锡圭,收到一封信。信是一位叫蔡伟的地摊小贩写来的。裘锡圭看完信后,大吃一惊。
寄信人是个叫蔡伟的辽宁锦州青年,信封上的落款地址是个普通居民区,职业栏潦草写着"摆地摊"三个字,让教授没想到的是,这封字迹工整的信件里,藏着对学术难题的精辟见解。
当时裘教授刚发表研究汉代《神乌赋》的论文,文中提到"佐子"这个让他琢磨不透的古语,这个摆地摊的年轻人却大胆提出新解——"佐子"应该读作"嗟子",是古人说话时的感叹词。
信里密密麻麻引着《诗经》《楚辞》里的句子,连《说文解字》的页码都标得清清楚楚,裘教授对着窗户反复读了三遍信纸,茶缸里的水凉透了都没顾上喝。
通信往来中,蔡伟的人生故事逐渐清晰,这个高考落榜生在锦州街头摆了八年地摊,白天守着卖日用品的塑料布摊位,晚上就着路灯抄书。
图书馆不让外借的《尔雅》《史记》,他硬是整本整本誊在旧账本上。家里五斗橱抽屉里码着四十多本手抄古籍,边角都磨得起毛边了。
裘教授动了爱才之心,几次三番劝他考研究生,可三十出头的蔡伟上有老下有小,妻子在纺织厂做工累出了肺病,儿子刚上小学。
每天蹬三轮拉货挣药费,根本没有时间学英语备考,有次回信里夹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学问在心上,不在文凭上。"
在2003年,复旦大学要整理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这种涉及大量生僻字的文献整理正需要蔡伟这样的"活字典"。
裘教授动了爱才之心,几次三番劝他考研究生,可三十出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妻子在纺织厂做工累出了肺病,儿子刚上小学。
直到某天讨论会上,蔡伟指着竹简上的"寍"字脱口而出:"这是楚地写法,和《包山楚简》里'安'字同源。"
满屋子人这才知道,这个闷声不响整理资料的中年人,肚里装着整部《战国文字编》。
在复旦古籍所三年,他白天跟着专家们校勘文献,晚上就睡在资料室行军床上,有回为查证某个字形演变,他翻遍资料库三千多张拓片,硬是找出七处同类写法。
项目收尾时,中华书局的老编辑看着校样直咂舌:"这校对水平,比我们社里老专家还细。"
2008年春天,他联合另外两位资深教授,给教育部写了封特别的推荐信,信里说这个摆地摊出身的中年人,实际水平早就超过普通博士。
那年秋天,38岁的蔡伟穿着妻子特意买的新衬衫,坐在复旦大学博士生入学考场里,监考老师看着这个比周围学生大一轮的考生,特意给他换了盏更亮的台灯。
六年寒窗不寻常,同龄人都在评职称、带项目的时候,蔡伟得从头补本科课程,古汉语课上,他笔记记得比学生还认真;英语课上,他兜里总揣着单词本。
有回在食堂打饭,他举着饭盆跟学生讨论甲骨文,把打菜阿姨听得直发愣,2014年博士论文答辩那天,台下坐着二十多位白发学者。
当蔡伟讲到楚国简帛中的特殊用字规律时,有位老教授掏出老花镜,把论文图表贴近了看。
毕业季招聘会上,45岁的蔡伟揣着复旦博士证跑了八场双选会,企业嫌他年纪大,高校嫌他没海外经历。
最后还是贵州安顺学院抛来橄榄枝,校长说了句实在话:"咱这偏远地方,就缺坐得住冷板凳的真学问家。"
现在蔡伟带着三个研究生,整天泡在地方文献馆里,有学生见过他办公桌上摆着本泛黄的笔记,翻开里面全是工整的钢笔字——正是当年手抄的《说文解字》残页。
当年给裘教授写信用的蓝格信纸,如今躺在复旦校史馆的玻璃柜里,旁边解说牌上写着:"民间学者与学院派碰撞的火花,见证学术精神的真谛。"
偶尔有参观者嘀咕:"这蔡伟要是当年考上大学,说不定还没这么大学问呢。"这话传到裘锡圭耳朵里,老先生扶着眼镜笑了:"学问这回事,从来不在门第高低,而在心思诚不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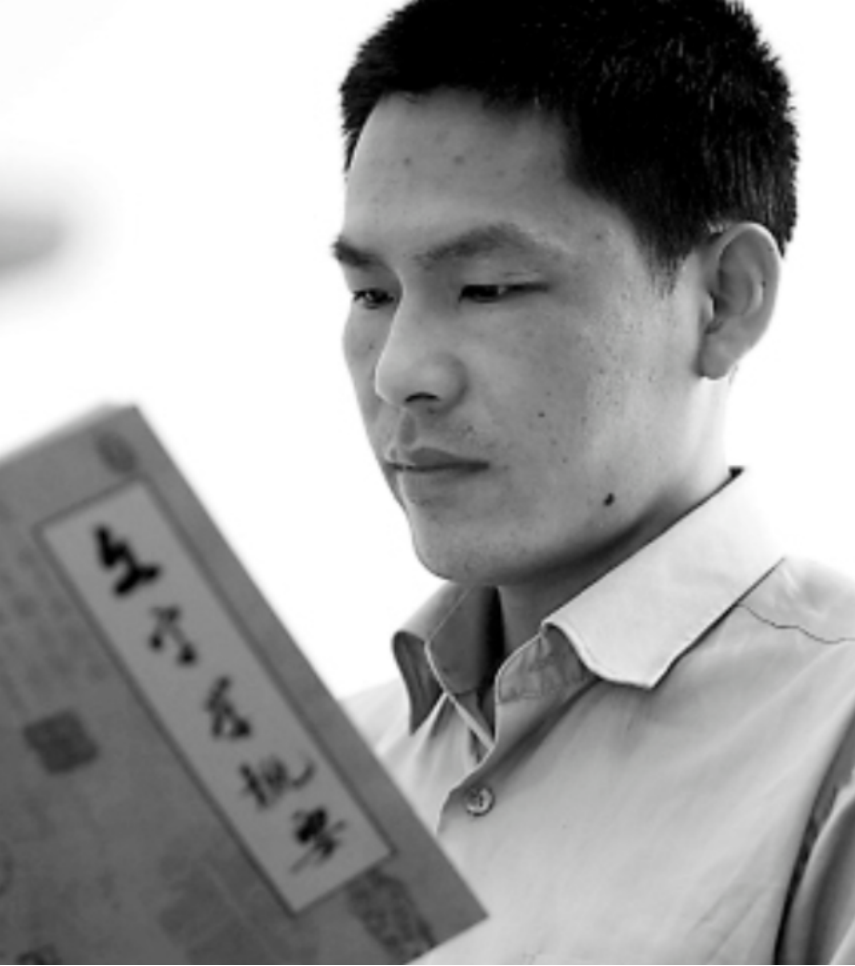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