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当上皇帝后,突然想起自己和初恋曹寡妇还有一个儿子,就悄悄地跑去沛县找人。两人一见面格外激动,一宿过后,刘邦满意地说:“随我进宫吧,以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曹寡妇当时正蹲在灶台前烙饼,闻言手里的锅铲“当啷”掉在地上。她抬起头,鬓角的碎发沾着面粉,眼里又惊又疑。这刘邦,还是当年那个蹭吃蹭喝的泗水亭长模样吗?明明穿着龙袍,说话却还是那股子痞气,可眉宇间的威严,又让她不敢像从前那样随意啐他。 曹寡妇本名叫曹月娥,在沛县街头开了个小面摊。 当年刘邦还是亭长时,常带着弟兄们来蹭吃蹭喝,吃垮了她三个面案。有回大雪封门,他缩在面摊角落喝冷酒,是曹月娥端了碗热汤面,往他手里塞了双棉手套。一来二去,俩人就好上了。后来刘邦犯了事跑路,她才发现怀了娃,取名刘肥。 这十几年,她一个寡妇带着娃,被地痞欺负过,被乡邻指点过,硬是靠着那口面锅,把刘肥养得虎背熊腰,都能帮她揉面了。 刘肥这会儿正在后院劈柴,听见屋里动静,扛着斧头就闯进来。见一个穿龙袍的陌生男人坐在炕边,娘的脸煞白,当即就红了眼:“你是谁?敢欺负我娘!” 刘邦哈哈一笑,拍着炕沿:“小兔崽子,不认得爹了?” 刘肥愣了愣,他听娘提过爹,说当年是个英雄,可眼前这男人,怎么看都像戏文里的皇帝。 曹月娥赶紧把儿子拉到身后,对着刘邦福了福身:“陛下,孩子不懂事,您别见怪。” “啥陛下不陛下的,”刘邦挥挥手,从怀里掏出个金元宝,往桌上一扔,“娥儿,跟我走。宫里的房子比你这面摊大十倍,金银珠宝堆成山,保准你和肥儿吃香的喝辣的。” 曹月娥没看那金元宝,只是低头绞着围裙:“陛下,您还记得当年在我这吃面,总说葱花要多放吗?” 刘邦一愣,随即笑了:“咋不记得?你烙的饼,就着葱花汤,比啥都香。” “那宫里的厨子,知道您爱多放葱花不?”曹月娥抬起头,眼里的疑云散了些,多了点别的东西,“知道您喝醉酒爱踢被子不?知道您跟人吵架时,左手总不自觉摸后腰吗?” 刘邦被问住了。这些年南征北战,身边的人要么敬他怕他,要么算计他,谁会留意这些? “陛下是真龙天子,”曹月娥拿起地上的锅铲,在围裙上擦了擦,“可我就是个烙饼的,住不惯金砖铺的地,也咽不下山珍海味。在这儿,我闻着面香踏实。” 刘肥在旁边听着,突然插嘴:“娘说了,爹是干大事的,咱不拖后腿。” 刘邦看着这娘俩,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他当皇帝后,见惯了谄媚讨好,听够了阿谀奉承,曹月娥这几句话,糙是糙,却比任何颂歌都让他舒坦。 他想起当年跑路前,曹月娥把攒了半年的碎银子塞给他,说:“你出去闯,混好了别忘回来看看;混不好,回来我还给你烙饼。” 那会儿他觉得这女人傻,现在才明白,这傻里藏着多真的情。 “你真不去?”刘邦又问,语气软了不少。 曹月娥摇摇头,指了指后院:“肥儿快成年了,我打算给他盖间房,再娶个媳妇,守着这面摊过一辈子,挺好。” 刘邦沉默了半晌,站起身。他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眼灶台,锅里的饼已经烙得金黄,香气飘了满屋子。 “肥儿,”他对着愣头青似的儿子说,“跟爹走,爹给你封王,让你当一方诸侯。” 刘肥看了看娘,曹月娥点点头:“去吧,跟着你爹学本事,别学他当年蹭吃蹭喝就行。” 刘肥咧嘴一笑,扔下斧头就跟刘邦走了。 刘邦走的时候,没再劝曹月娥。只是让随从留下了一箱子金银,还有一队亲兵,说是“给曹大娘护院”。 后来,刘肥被封为齐王,成了汉初最有权势的诸侯王之一。他总惦记着沛县的面摊,每年都要回去几趟,带着一车车的米面油盐,帮着曹月娥把面摊扩大成了酒楼。 有人说曹月娥傻,放着皇后不当,偏要守着破面摊。她听了只是笑,手里的锅铲照样翻飞。 刘邦后来也回过沛县,没摆皇帝的架子,就坐在酒楼角落,吃着曹月娥烙的饼,喝着葱花汤,跟当年的老弟兄们吹牛皮。喝到兴头上,还拔剑斩了案几,吼着当年的小调。 曹月娥就在旁边看着,给他添酒,提醒他:“慢点喝,别又醉倒在灶台边。” 这世上的荣华富贵,各有各的活法。有人爱龙椅的尊贵,有人就爱灶台的烟火气。曹月娥没选错,刘邦也没逼她,或许这就是他们之间,最好的结局。 (根据《史记》等史料及民间传说整理)



![嘉靖:练得身形似鹤形,不怕宫女勒脖颈[吃瓜]为什么几个宫女要弄死嘉靖呢?](http://image.uczzd.cn/17894692397373469023.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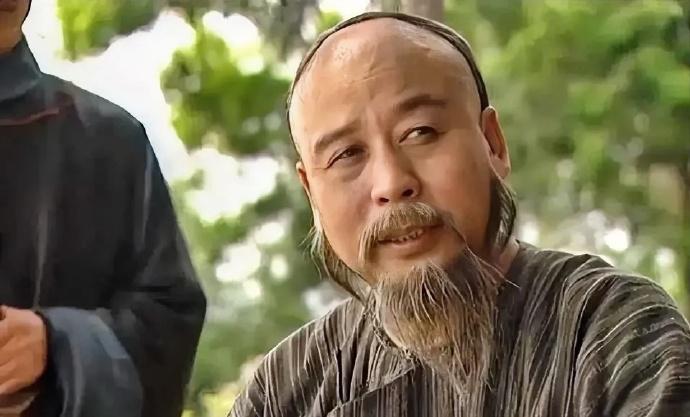




月岩
人生就是来来回回,曹是大智慧的女人!
用户16xxx30
小编应个梦说出来象真的一样。
强扭的瓜就是甜
编的还挺像,连名字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