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医生根据罗健夫的遗愿剖开了他的遗体,发现他全身都布满了癌肿,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大,现场的医生和护士都忍不住流泪。
那年6月16日,西安医学院解剖室里弥漫着刺鼻的福尔马林气味,当手术刀划开罗健夫的胸腔,主刀医生的手突然僵在半空。
谁承想那颗还在渗血的肿瘤竟比成年人的拳头更大,赫然压在被癌细胞蛀空的胸骨上。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低分化淋巴瘤已侵蚀全身80%以上器官,骨转移导致胸骨密度接近朽木。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此时被癌症啃噬得千疮百孔的身体,三个月前还在绘图仪前修改Ⅲ型图形发生器的电路图。
护士长记得那天转运遗体时发生的诡异声,。搬运工稍微倾斜担架,死者后背突然渗出黄褐色液体,浸透的白布单下露出蛛网状的溃烂伤口。
根据病理切片显示,腐烂组织里藏着至少两年以上的癌变痕迹,没人想得通,每天准时出现在骊山微电子公司实验室的男人,怎么能在脊椎神经被肿瘤压迫的情况下,坚持完成精密仪器的脉冲电路调试。
令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他在工作笔记最后一页所写的:"6月4日,示波器波形仍存在0.3微秒延迟,建议更换TL494芯片。"
时间拨回1970年春天,北京中关村的苏联专家刚撤走半年,留给中国的只有几箱残缺的集成电路手册。
图形发生器作为制造导弹制导芯片的核心设备,被列入"巴黎统筹委员会"严格禁运清单。
28岁的罗健夫站在陕西临潼的土坯房里,面前是从北京拆运来的生锈机床,一度陷入沉默,他接下来要做的是攻克连专业教材都没有的微电子技术。
1971年7月到9月间,罗健夫有43个深夜的出入登记,最晚一次签到是凌晨3点17分。
而在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总放着三样东西:俄英电子词典、胃痛药片以及写给妻子的道歉信。
有次暴雨冲垮厂区围墙,其他人都开始往外跑,只有他折返回去蹲在漏雨的库房里,用身体挡着潮湿的晶体管元件。
1972年冬天,美国《电子工程时报》刊登了英特尔4004微处理器问世的消息,罗健夫托人在香港买回半本被海关剪碎的期刊。
工程师张为民回忆,他像解码密电般研究那些残缺的电路图,有天突然冲进车间大喊:"老张!用TTL门电路代替分立元件!"
但正是这个灵感让图形发生器的体积从衣柜缩小到电视机大小。
次年春天,当第一块国产集成电路在发生器上刻出0.1毫米精度的轨迹线,整个车间响起《东方红》乐曲时,但那时罗健夫的身体已经出现问题,正躲在厕所吐血。
1981年,一次体检意外发现白细胞异常增高,当他询问医生是何意时,医生用红笔圈出"疑似血液病"四个字。
他悄悄把化验单折成纸飞机扔进锅炉,转身去给新来的大学生讲解光刻机原理。
直到次年2月昏倒在调试台,同事们才从他锁着的抽屉里发现三张没交的住院单。
病床上他坚持要听实验进度,护士不得不把心电图机推到病房,让他看着示波器指导徒弟修改程序。
在最后那段日子里,被止痛针灼烧得神志不清的他,总在幻觉中重复调试动作。
有次突然扯掉输液管,对着空气喊:"老蔺!晶振频率不对!"吓得护工按住他枯枝般的手臂。
去世前一周,他让妻子把未完成的图纸铺满病床,用颤抖的手指在上面画了七个红圈,这些标记后来成为Ⅲ型图形发生器量产的关键改进点。
骊山脚下的烈士陵园有块特殊的墓碑,上面既没刻生卒年月也没写职务职称,花岗岩表面蚀刻着密密麻麻的集成电路图案,阳光照射时会在地面投下芯片般的阴影。
信息来源: 新华社《国家记忆:致敬航天英模罗健夫》 央视新闻《共和国不会忘记》 《中国航天报》"航天精神人物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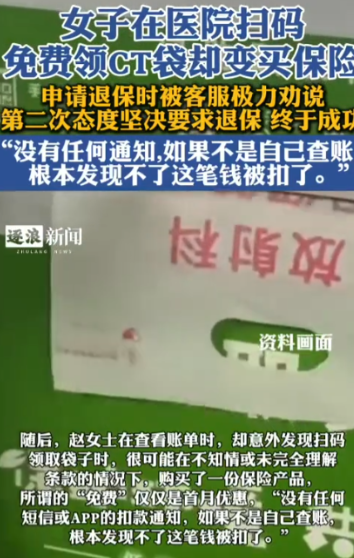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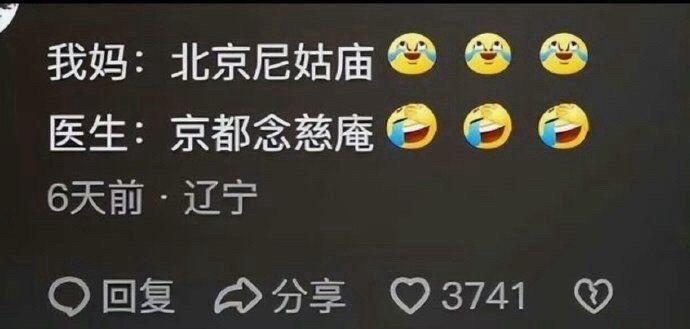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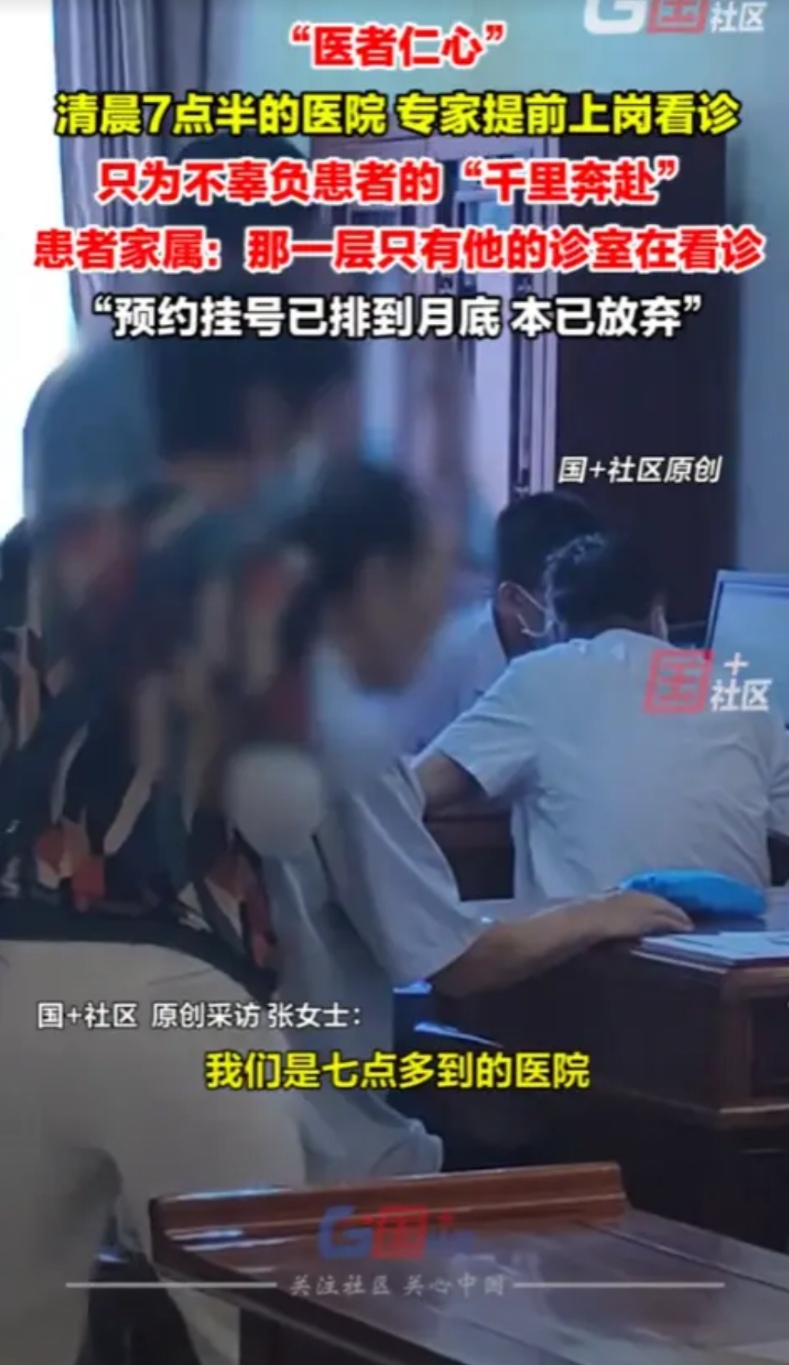

幸福多一点
致敬
9494316
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