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20年时间,花了国家那么多钱,搞成这样,我是有罪的。”1993年冬天,高伯龙在实验室里盯着那台“罢工”的激光陀螺工程样机,声音沙哑地对团队成员说出这句话。
1993年,国防科技大学实验室气氛凝重。
年过花甲的高伯龙院士站在专家组面前,神情肃穆。
他牵头研制的激光陀螺工程样机在关键鉴定中未能完全达标。
面对结果,高伯龙沉默良久,最终低沉自责道:“我花了20年,国家还花了那么多钱,搞成这模样,我有罪!”
这句话重重砸在现场每个人心上,成为这位科学家晚年难以释怀的心结。
高伯龙毕生奉献激光陀螺研究,临终前仍对妻子表达对国家的愧疚,认为自己是个“罪人”。
这背后,是一位科学家对祖国深沉的挚爱与近乎苛刻的责任感。
高伯龙生于1928年战火纷飞的年代。
1944年,日军铁蹄踏至广西,他就读的高中被迫解散。
逃亡途中,少年高伯龙亲眼目睹同窗在炮火中丧生。
这惨烈一幕点燃了他强烈的报国志向——定要让祖国强大起来!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深知科技强则国强,毅然选择物理学作为毕生方向。
毕业后,高伯龙进入哈军工物理教研室工作十几年,后随校南迁长沙,进入国防科大任教。
此时,美国在激光陀螺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这种新型惯性导航器件具有精度高、稳定性好等革命性优势,迅速成为飞机、导弹等精确制导的核心部件。
高伯龙敏锐意识到此技术关乎国家战略安全,中国绝不能落后!
但当时国内在此领域几乎空白,技术封锁严密。
关键时刻,钱学森院士伸出援手。
1971年,他亲自点将,推动高伯龙调入国防科大应用物理系,负责筹建激光研究室主攻激光陀螺。
钱学森的信任让高伯龙深感责任重大,从此他的人生与激光陀螺紧紧捆绑,开启艰辛的科研长征。
激光陀螺涉及精密光学、激光物理等尖端领域,技术门槛极高。
高伯龙团队从零开始,面对经费紧张、设备简陋、资料稀缺等重重困难。
他将全部身心投入,实验室成第二个家。
常工作至深夜甚至通宵,休息时间压缩到最少。
炎夏穿着洗得发白的廉价褂子,汗流浃背守在设备旁。
为省时间,扒几口饭就回工作台。
他几乎牺牲所有个人生活和家庭时光——父母住院未能尽孝,妻儿需要陪伴常常缺席。
面对不解,他总坚定回答:“他们会理解我。”
国家需要高于一切。
历经无数次失败摸索,团队1978年迎来重大突破:成功研制我国第一代激光陀螺实验室样机!
中国成为继美、德后第三个独立掌握此技术的国家!
而高伯龙未沉浸喜悦。
他深知实验室样机距工程化实用化路还长。
更紧迫的是,美国得知中国进展后,迅速重启更先进的“四频差动激光陀螺”研究。
这意味着稍有松懈,差距又会被拉大。
高伯龙未停歇,立即带队攻关更精密的四频差动激光陀螺。
这场与时间赛跑的硬仗严重透支他的健康。
实验室多次因劳累晕倒,稍作休息又固执回到岗位。
妻子见他日渐消瘦白发丛生,心疼劝其退休。
高伯龙总摇头拒绝:“国家需要这个,美国有的中国一定要有!不能停。”
妻子最终选择理解支持。
科研道路崎岖。
为赶进度,有次实验室区域因暴雨只能夜间供电。
高伯龙立刻带队通宵工作。
长期昼夜颠倒极度劳累使他身体每况愈下。
晚年几乎在医院实验室间奔波,病床上牵挂的仍是技术攻关。
1993年,凝聚团队二十年心血的工程样机迎来关键鉴定。
样机未完全达到预期高精度指标。
面对结果,高伯龙感前所未有挫败自责,那句沉痛“我有罪”是内心极度愧疚的真实写照。
这种苛刻要求源于对国家深沉的爱与强烈责任感。
2017年,高伯龙生命走到尽头。
弥留之际,他仍念念不忘奋斗一生的事业,对病床前妻子说出最后心声:“国家在我身上花那么多钱,投入那么多资源,可成果……还是不够……我对不起国家,是个罪人……”
这位将毕生奉献祖国国防科技的科学家,临终未留丰厚物质财产,却留下沉甸甸的精神遗产与无尽遗憾。
他最大愿望是看到祖国强大科技自立,并为此殚精竭虑至死方休。
高伯龙的“愧疚”非真正罪过,而是赤子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的体现。
他将一生与国家需要紧紧相连,置个人得失于度外。
正是无数如他般默默奉献的科学家,用智慧汗水乃至健康奠定中国国防科技基石,换来国家安宁与尊严。
他的故事是爱国情怀与科学精神最生动的诠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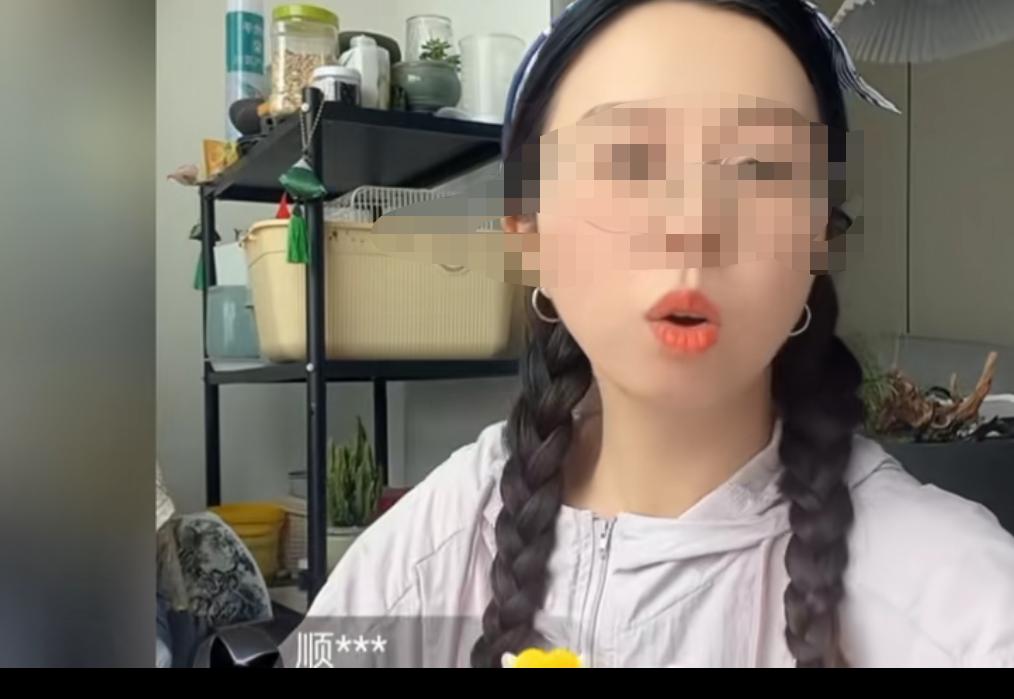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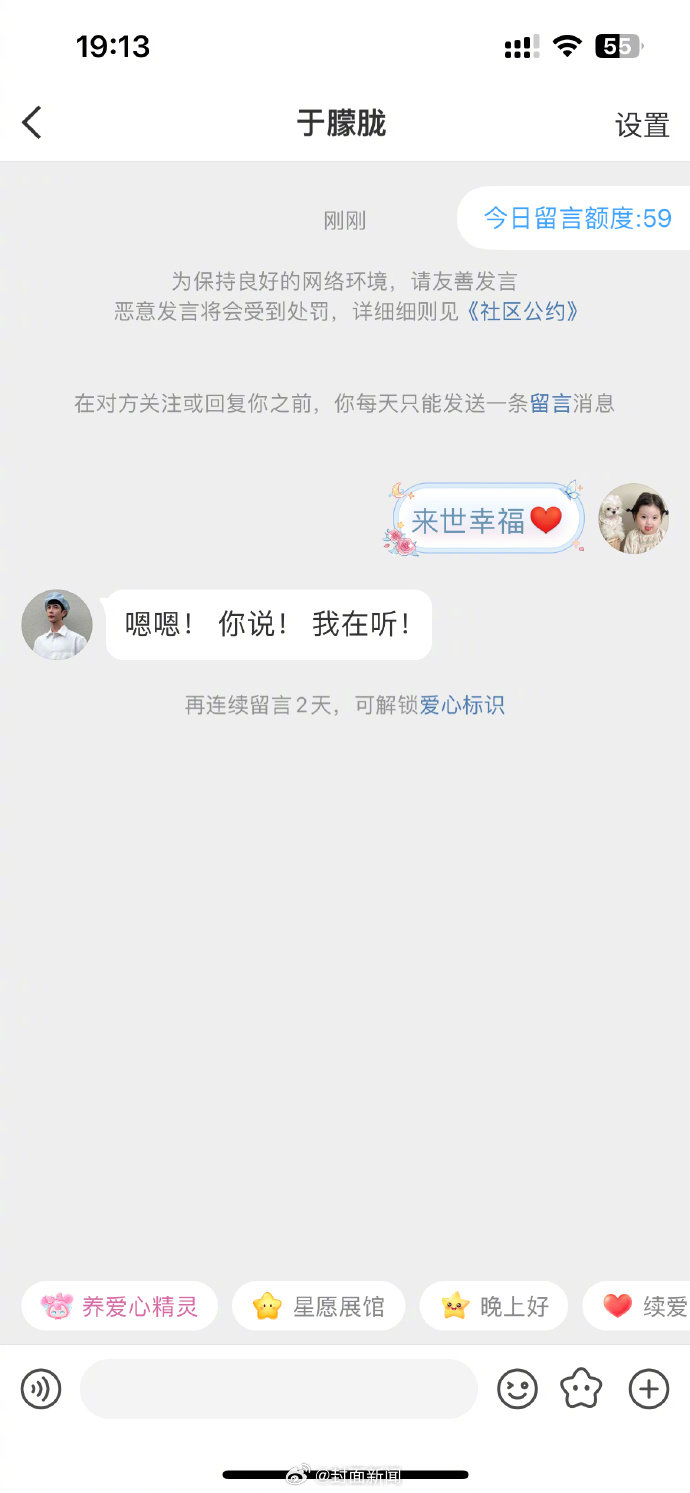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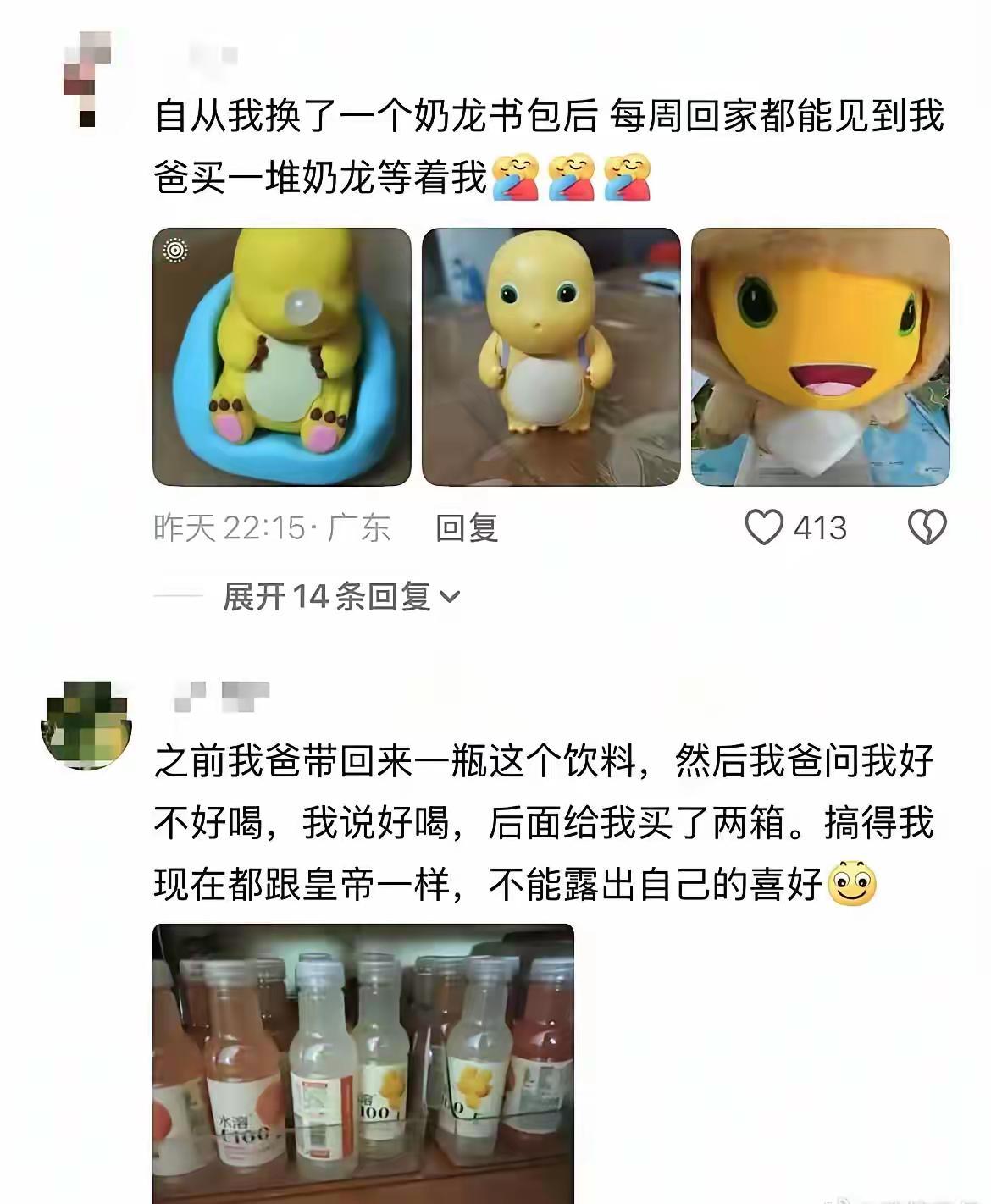

![我真的嫉妒了[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2599347546326358698.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