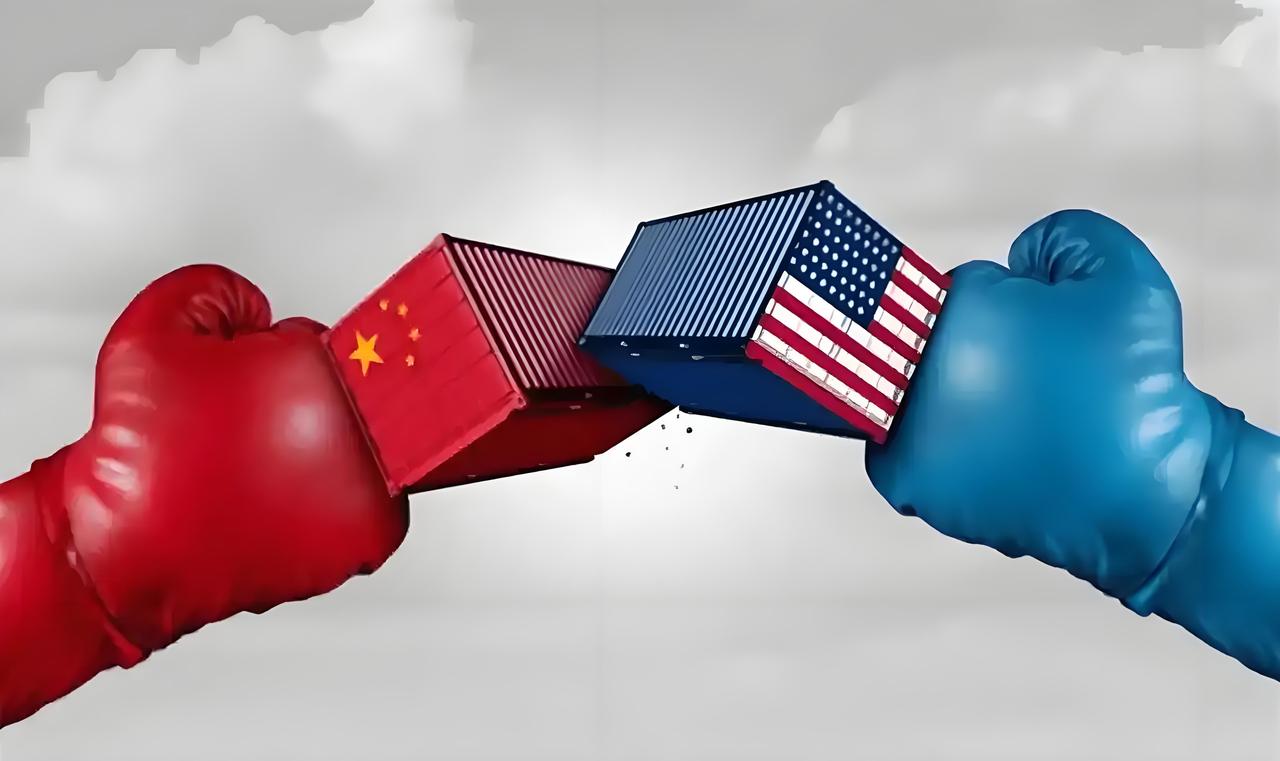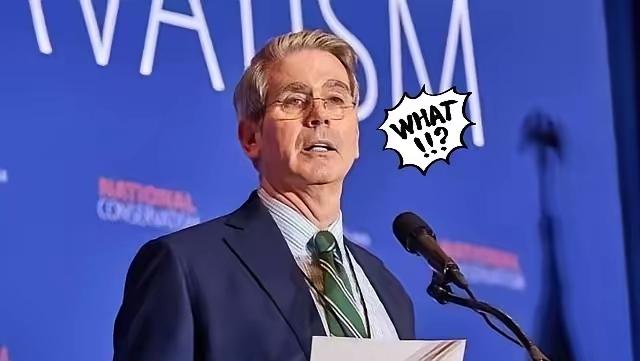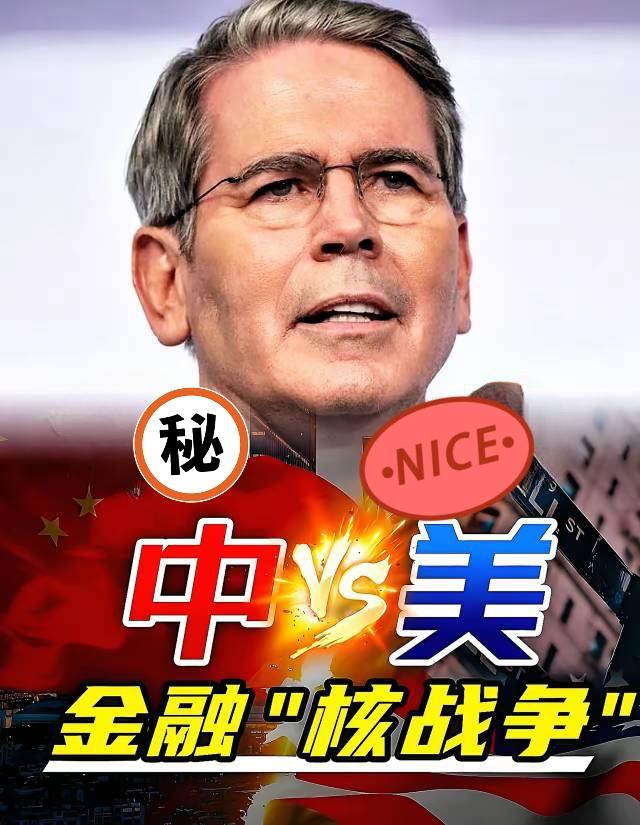东大目前只剩7300亿美债了,刚刚东大又抛弃了200多亿美债。美国国债规模已膨胀至36.2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30%以上。 2025年上半年,到期债务高峰期尤为严峻,6月单月就有6.5万亿美元需要借新还旧。这些旧债多源于疫情期间的1.8%低利率,如今置换时利率逼近5%,额外利息支出直达两千亿美元。财政部官员面临国会质询,预算空间被利息蚕食,国防和福利项目首当其冲。穆迪机构5月将主权信用从Aaa降至Aa1,信号明确:债务可持续性存疑。外国持有者占比约25%,但国内机构仍是主力买家。这种滚雪球式的融资模式,让美国经济如履薄冰,任何外部变量都可能放大风险。 中国作为昔日美债第二大持有者,其仓位变迁折射出双边贸易的起伏。早在2011年峰值时,中国持有1.32万亿美元,占外汇储备的显著份额。那时,对美出口顺差高达数千亿美元,美元盈余需找安全港湾,美债收益率稳定,汇率风险可控。进入2022年后,顺差缩水明显,2025年上半年同比下滑20%,美元流入量减少15%。供应链外迁政策加速,企业订单流失,资金池子变浅。6月末持仓7564亿美元,已低于1万亿大关,连续多年小步减持,体现出资产多元化的渐进策略。 减持的深层动因不止于贸易失衡,还牵涉地缘与信用双重考量。台湾海峡巡航频次上升,美方军舰穿越达每月三次,情报显示潜在冲突风险放大。若局势升级,美债作为美元资产,可能面临冻结威胁,如俄乌事件中俄罗斯资产遭封锁的先例。中国外汇管理者审慎评估,优先缓冲此类不确定性。同时,美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大,2025财年预计超2万亿美元,债务/GDP比率攀升,信用下调进一步侵蚀吸引力。减持并非仓促,而是系统性避险:转向黄金和欧元资产,8月末外汇储备达3.322万亿美元,黄金占比悄然提升。这步棋,既护航国内流动性,也回应外部施压。 7月减持257亿美元的行动,标志着仓位滑至7307亿美元,创2009年以来新低。美国财政部TIC报告显示,此举分批执行,短期国库券占比60%,中期债券40%,避开市场高峰以防剧震。同期,日本增持36亿美元,总额达11514亿美元,稳居海外首位;英国猛增413亿美元,至8993亿美元,跃升第二。韩国和澳大利亚响应美方信号,加仓中期债,填补空缺。外国整体持仓升至9.16万亿美元,连续五月破9万亿大关。中国此轮操作后,排名退至第三,出口数据同步显示对美顺差进一步压缩,资金内流支持基建和科技投资。 全球美债持有格局正经历洗牌,日本作为最大债主,其持仓占外国总量的12.5%,得益于日元贬值和美联储宽松预期。英国增持源于伦敦作为离岸中心的枢纽作用,吸引欧洲资金流入。加拿大和印度则同步减持,前者571亿美元,后者因贸易摩擦持续下滑。 总体看,美国不愁买家,盟友体系确保需求稳定,但中国退出加剧了收益率上行压力,10年期债从4.2%微升0.05%。这反映出多极化趋势:新兴市场转向本地货币债券,减少美元依赖。减持虽小,对中美金融脱钩的隐忧却在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