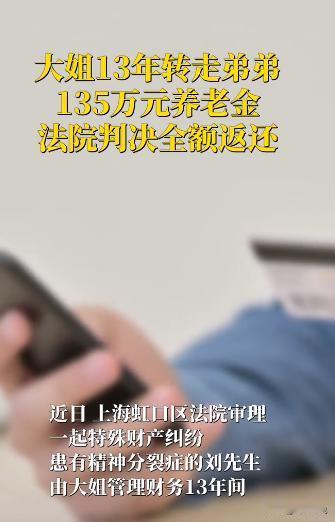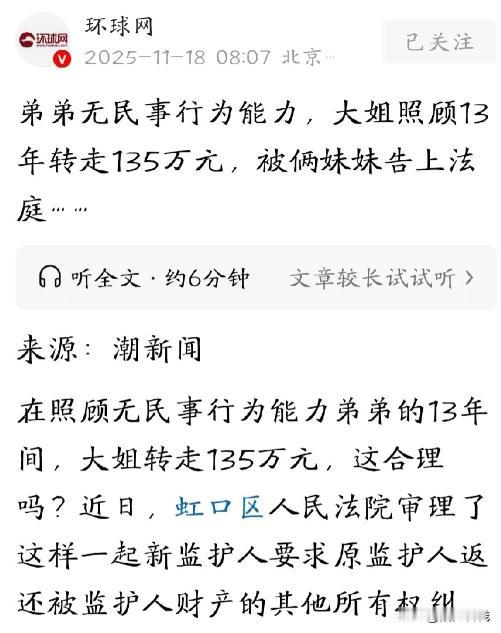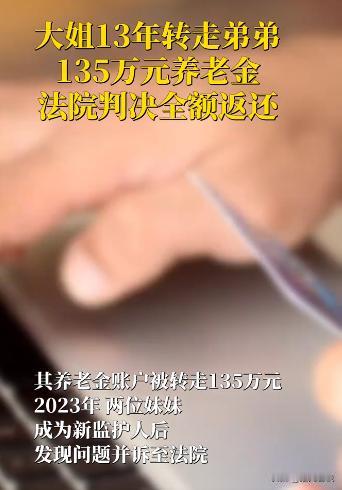上海,男子患精神分裂,未婚未育,退休后被姐姐和两个妹妹送到了疗养院长期居住。他每月退休金五六千,还攒了上百万元,都交给姐姐代为保管。谁知13年后,妹妹竟然发现姐姐悄悄从哥哥卡上转走了135万余元,但只有很少一部分花在了哥哥身上,其他的全进了姐姐腰包。于是,两妹妹将姐姐告上法庭,要求立刻还钱。法院经过调查,却发现了更加震惊的真相。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的审判庭内,70万元的返还判决敲定的那一刻,原告席上的两位妹妹指尖微微发颤,被告席的大姐则始终垂着脑袋。 这场横跨13年的手足纠葛,终究以法律划下底线,可那份被金钱啃噬的亲情,却再也回不到最初的模样。 故事的核心,是被监护人刘先生半生的孤苦与无奈,年过六旬的刘先生,自青年时确诊精神分裂症后,人生便少了寻常人的烟火气。 他终身未娶,无儿无女,父母早逝后,三位姐姐成了他唯一的亲人。 2010年退休前夕,考虑到刘先生的病情需要专业照护,三姐妹坐在一起商量,最终决定将他送入辖区内的精神卫生中心长期托养。 那时姐妹仨握手约定,要一起把弟弟照顾好,谁也没料到,这个温暖的承诺会在岁月里变味。 更没人能想到,这位常年住院的病人,竟是个“隐形的小康之家”。 刘先生退休后每月有5000多元退休金,加上每月600元的交通补助、300元的残疾人专项补贴,再算上每季度300元的敬老卡福利,月均收入近6000元。 更关键的是,他病前是出了名的“铁公鸡”,工资除了基本开销全存起来,日积月累攒下了百万积蓄。 更省心的是,原单位有明确政策,精神卫生中心的护理费能报销大半,日常吃喝用药几乎不用额外掏钱。 大姐是老大,做事稳当,钱交她管我们放心,基于这样的信任,三姐妹约定,刘先生的三张存折、身份证、医保卡等全部交给大姐保管,日常开销由大姐记账支出。 此后13年里,两位妹妹从没过问过账目,在她们看来,亲姐姐总不会亏待亲弟弟,这份毫无设防的信任,反倒给了私心滋生的空间。 2023年的一场遗产之争,成了引爆矛盾的导火索,因为父母留下的老房子拆迁款分配不均,三姐妹从拌嘴升级到对簿公堂,昔日的温情彻底消散。 争吵中,有人无意间提起“弟弟的钱一直是大姐管着”,这句话点醒了两位妹妹。 她们随即向法院申请:宣告刘先生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更换监护人。 法院的初步调查就让人心头一沉:大姐的银行流水显示,她多年来频繁从刘先生账户取现,部分款项直接转入自己和女儿的账户,存在明显的财产混同。 最终,法院依法宣告刘先生无民事行为能力,并指定两位妹妹为新监护人。 交接账户时,两位妹妹翻看着银行流水,越看越心惊:13年间,大姐从弟弟账户累计取现、转账高达135万元! 他天天在医院,吃穿用都有保障,这钱到底花在哪了?带着这个疑问,姐妹俩以刘先生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大姐告上法庭。 庭审时,大姐抹着眼泪辩解,自己13年里“掏心掏肺照顾弟弟”,我每月都接他出来住,租房、看病、买营养品,哪样不要钱?房租年年涨,花销根本降不下来! 可当法官让她出示大额支出凭证时,大姐却支支吾吾拿不出来,而 两位妹妹当庭拿出的证据,更戳穿了这份“委屈”。 她们查访发现,大姐口中“给弟弟租的周转房”,其实一直是大姐和女儿一家住着,屋里的装修风格还是外甥女喜欢的北欧风,但这笔十多万元的装修费,赫然出自刘先生的账户。 更让人气愤的是,有三年刘先生因病情加重,医生明确要求“不可离院”,可大姐一家照样住着那套房子,每月3000多元的租金全从弟弟账户扣除。 更离谱的是,刘先生名下还有一套小平米住房,本是父母留下供他偶尔出院暂住的,却被大姐悄悄挂在中介转租,近十年的租金全进了自己腰包。 我们去精神卫生中心调了出入记录,13年里弟弟总共就出来66次,平均每年才5次,每次都是看病或过年聚餐,最多住一两天,哪需要常年租着房子? 妹妹的质问,让大姐哑口无言,法官当庭算了笔明白账:刘先生每月近6000元收入,加上单位报销的护理费,日常开销完全覆盖。 即便算上每年6到8次的外出就医、节日聚餐,13年的合理支出撑死不过20万元,与135万元的差额悬殊太大。 我国《民法典》第三十五条早已明确:监护人履职必须“最有利于被监护人”,除了维护其利益,绝不能动用其财产,这不是空洞的条文,而是切实的保障。 虹口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大姐的诸多支出远超“为弟弟利益”的范畴,已构成财产侵权。 但考虑到她确实有过接弟弟出院、购置生活用品等履职行为,最终酌情判决返还70万元。 刘先生的遭遇警示每个家庭:监护从来不是“单个人的信任游戏”,而是需要规则约束的责任。 唯有守住这份底线,才能让监护权回归初心,让亲情不再被金钱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