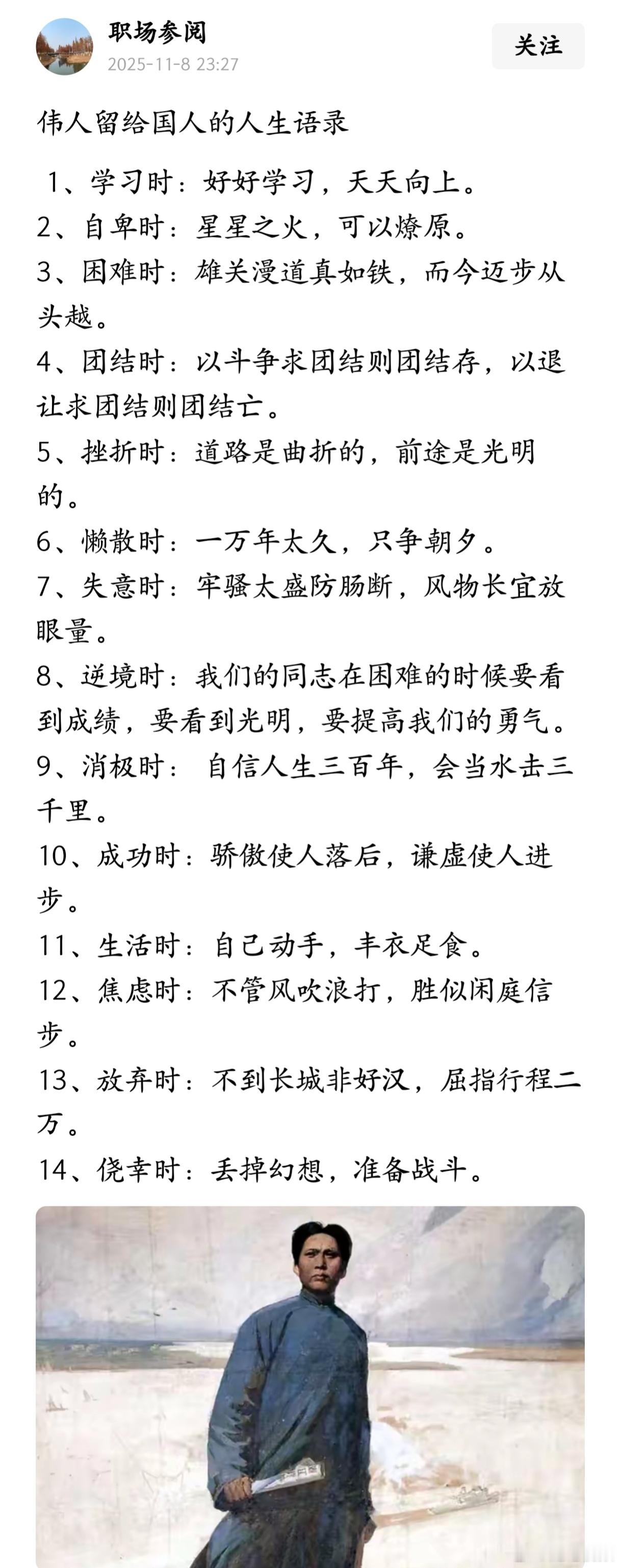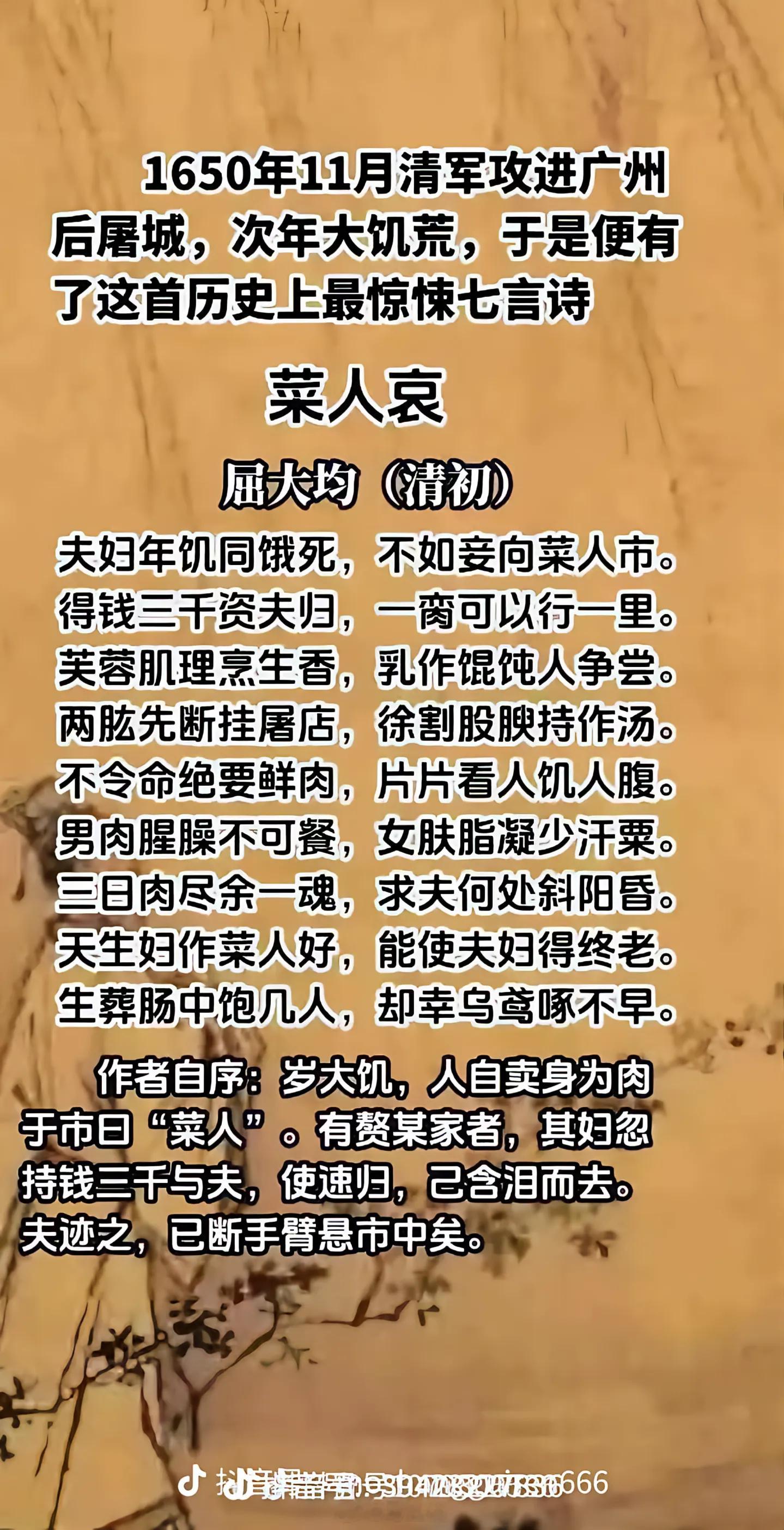1962年,范曾拿着毕业作找郭沫若题字。郭沫若大为兴奋,在上面写了首48句长诗。不料,学校却以投机为由,拒绝让它参展。 原本是开心的去,却没想到学校的态度很强硬:这幅画,不能参加毕业展。 这下范曾傻眼了。机关算尽,若是连毕业展都上不了,那不是成了笑话? 关键时刻,还是导师蒋兆和心软了,或许是惜才,或许是不忍看年轻人受挫太深。经过一番调解,学校给出了一个折中方案:画可以展,但必须把郭沫若的题字遮起来。 于是,在当年的毕业展上,出现了一个极其荒诞的画面:范曾的《文姬归汉图》挂在墙上,但画的一角被一张白纸死死盖住。 那张白纸,盖住的是郭沫若的诗,却盖不住范曾那颗躁动不安的野心。这一幕,极其精准地隐喻了范曾的一生:才华是有的,但才华之上,永远覆盖着一层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机巧”与“算计”。 这件事并没有让范曾收敛,反而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在名利场上,才华只是基础,人脉和手段才是杠杆。 尝到了甜头的范曾,毕业后把这个套路运用得更加炉火纯青。这一次,他瞄准了性格温厚、当时正在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沈从文。 为了接近沈从文,范曾使出了“肉麻”战术。他给沈从文写信,信里竟然写道:“梦见沈先生生病,竟连夜从天津赶来探望。”这种话,别说那个年代,就是放在现在,也足以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 可沈从文是个实在人,心软,被这个年轻人的“赤诚”打动了。他不仅帮范曾调动工作,还让他在自己身边当助手,甚至在范曾生活困难时,拿出自己的工资接济他。 那时候的沈从文绝对想不到,自己怀里揣着的,不是一块美玉,而是一条会咬人的蛇。 十年浩劫来临,风向变了。沈从文成了被批斗的对象。 那个曾经口口声声说“梦见先生生病”的范曾,转头就贴出了几百条罪状的大字报。他不仅揭发沈从文,还给恩师列出了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甚至在沈从文指出他画作错误时,指着沈先生的鼻子大骂:“你那套过时了!” 沈从文后来提起这事,用了四个字形容自己的心情:“巨大震动”。 他说:“揭发我的居然是范曾。” 这不仅仅是背叛,这是在恩人的心口上狠狠捅了一刀。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或许人人都在求自保,但像范曾这样“吃着恩师的饭,砸着恩师的锅”,甚至还要踩上一万只脚的,实属罕见。 如果说对沈从文是“狠”,那对李苦禅就是“狂”。 李苦禅,大写意花鸟画的一代宗师,也是范曾的老师。范曾成名后,对这位恩师却逐渐失去了敬意。他甚至在公开场合对李苦禅直呼其名,态度轻慢。 李苦禅是个山东汉子,眼里揉不得沙子。他在临终前,留下了那句振聋发聩的评价:“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这句话,几乎成了范曾身上撕不掉的标签。甚至在李苦禅去世后,李家人坚决拒绝范曾扶灵,连灵堂的大门都不让他进。师徒一场,最后落得如此决绝的下场,怎能不让人唏嘘? 再看他与黄永玉的几十年恩怨,那更是堪称文艺界的“泥石流”。 黄永玉画画讽刺他,他就写文章骂回去。他骂黄永玉是“蝜蝂”,攻击对方的人品画品。两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把文人的脸面都撕得粉碎。 最有意思的是,范曾曾自评:“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 甚至狂言自己是“坐四望五”的巨匠——前面也就是画圣吴道子那个级别的,他范曾就是五百年一出的奇才。 这话传到黄永玉耳朵里,老头子直接画了一幅画,上面题字:“你他妈又吹。” 他的一生,就像是一部精心编排的大戏。 他有才华吗?当然有。他的线条功底,他的白描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确实独树一帜。他的《文姬归汉》如果抛开那些场外因素,依然是一幅佳作。 但他更擅长的是“经营”。他经营人设,经营关系,经营名声。他把书画变成了一种可以在名利场上流通的硬通货。他太懂这个社会运转的潜规则了,也太懂如何利用人性的弱点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从1962年那个在郭沫若门口蹲守的青年,到2024年这个牵着36岁娇妻手的高龄新郎,范曾从来都没有变过。 他始终是那个精明的“狩猎者”。 他猎取名声,猎取地位,猎取财富,也猎取爱情。 有人说他“缺德”,有人骂他“无耻”。但范曾似乎从不在乎这些。他活在自己构建的逻辑闭环里:只要我赢了,过程并不重要。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一层遮盖在《文姬归汉》上的白纸,它就像一道符咒。 揭开那张纸,你看到的是郭沫若的墨宝,是范曾的才气;但盖上那张纸,你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荒诞,和一个人为了往上爬而不顾一切的吃相。 历史是公平的,它不会因为你嗓门大就记你的好,也不会因为你活得久就抹去你的过。 如今,86岁的范曾依然活跃在热搜上。他享受着流量带来的红利,也承受着舆论的枪林弹雨。 对他来说,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毕竟,对于一个演了一辈子戏的人来说,最大的悲哀不是被骂,而是被遗忘。 只要还有人议论他,他就觉得自己还活着,还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