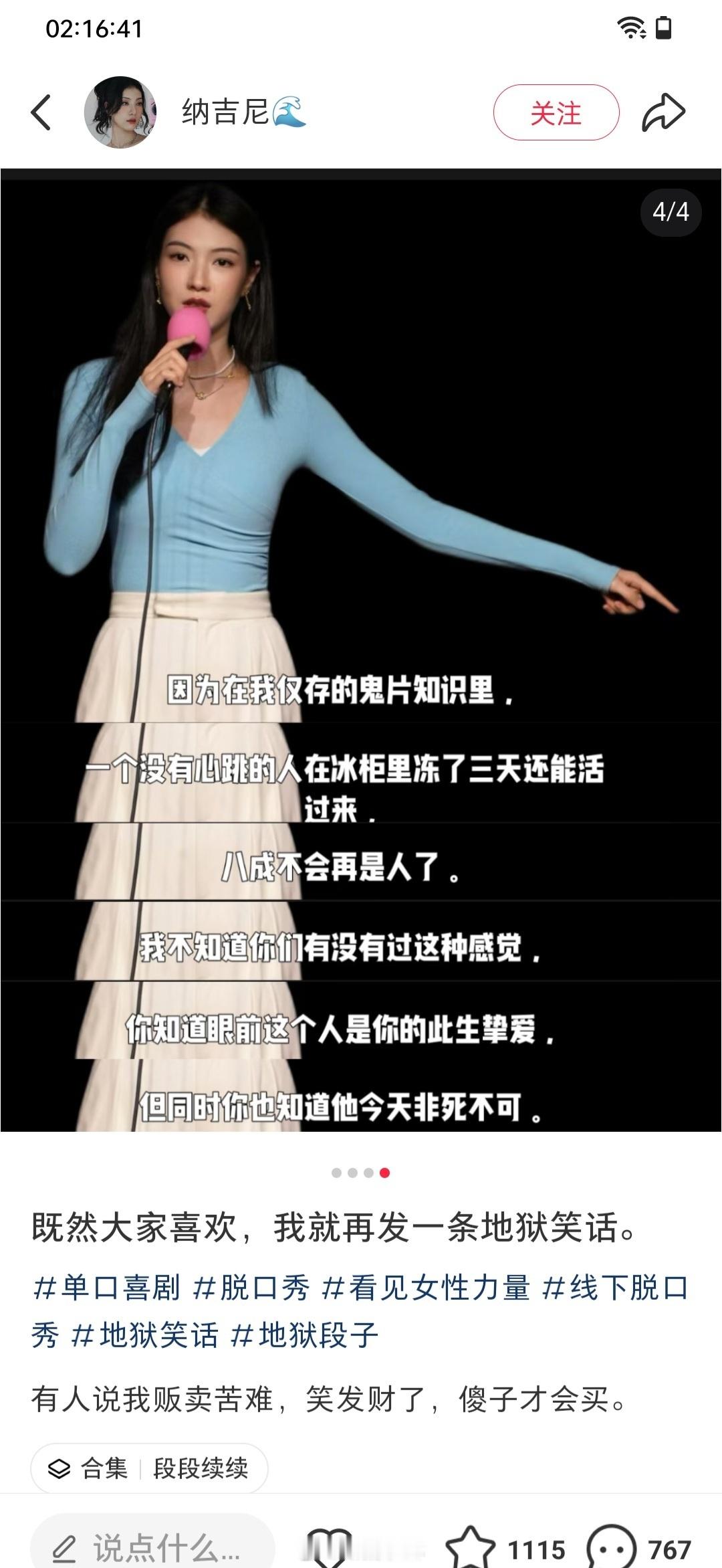1955年,志愿军翟文清衣锦还乡,全村五十余同乡只剩他一人归来。 翟文清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脚底下是熟悉的黄土路,可眼前的一切都变了样。他走的时候是冬天,树叶子落得精光,现在槐树绿得发亮,蝉在里头叫得人心慌。背包里装着立功喜报和几块军功章,沉甸甸的,可他总觉得手里空落落的,像是丢了什么东西找不回来。 进村的路不长,他走得慢。路过李二叔家的院子,墙塌了一半,里头长满了蒿草。翟文清记得,当年李二叔给他塞过两个窝窝头,说路上吃,别饿着。李二叔的儿子栓子跟他一块儿参的军,分在一个班。栓子话多,打仗的时候也堵不住嘴,说打完仗回去要盖新房子,娶媳妇。上甘岭那场仗,栓子替他挡了一块弹片,话还没说完就没了声息。 再往前走是刘家大院,刘大爷有三个儿子,全送上了战场。老大走的时候媳妇刚怀上孩子,老二还没说上亲,老三才十七,虚报了年龄跟去的。翟文清记得老三那张娃娃脸,笑起来露出两颗虎牙。他们在战壕里分过一壶水,老三说哥,等回家我请你喝井水,咱村的井水甜。 现在那口井还在,井台上长满了青苔。 翟文清站在井边发了一会儿呆。村里静得很,连狗叫声都没有。他想起当年出发那天,全村人都出来送,敲锣打鼓,放鞭炮,大姑娘小媳妇往他们怀里塞鸡蛋。五十多号人,穿得破破烂烂,可一个个腰杆挺得笔直,眼睛里冒着光。他们唱着歌走的,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那歌声震得老槐树上的鸟都飞了。 现在他一个人回来了。 走到自家门口,土坯房还在,屋顶的茅草换过了,门板上贴着褪色的春联。翟文清站在那儿,手抬起来又放下,不知道怎么敲门。他娘在里头吗?他爹呢?走的那年爹就咳嗽得厉害,说等他回来盖新房。 门开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探出头来,眯着眼睛看了他半天,突然身子一软,靠着门框滑了下去。翟文清冲上去扶住,喊了一声娘。老太太抓着他的胳膊,手指头掐进肉里,浑身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他才知道,爹去年没了。临死前还念叨他,让娘一定等他回来。 那些天,翟文清把带来的军功章摆在爹的坟前,烧了纸,磕了头。然后他挨家挨户去敲门,给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家里送信。他把栓子、老三、还有那些同乡最后说过的话,能记住的都说给他们的亲人听。有的人家听完就哭了,有的人家干坐着,一滴眼泪都没有,眼珠子直愣愣的,像两口水井。 翟文清心里头堵得慌。他不觉得自己是英雄,也不觉得那些回不来的人想当什么英雄。他们就是想打完仗回家,盖房子,娶媳妇,喝井水。可他们留在了那个叫朝鲜的地方,埋在异国的山坡上,再也回不来了。 村里人还是把他当英雄待,请他吃饭,给他敬酒,夸他有出息,立了功,光宗耀祖。翟文清笑着应酬,可每吃一顿饭,心里就重一分。那些空着的座位,那些端酒时颤抖的手,那些欲言又止的眼神,比战场上任何东西都让他难受。 有时候他一个人走到村后的山坡上,看着山下的村庄,炊烟袅袅,鸡犬相闻,跟走的时候一模一样。可他知道不一样了。五十多号人,就剩他一个。他们的魂还飘在战场上,飘在上甘岭的坑道里,飘在那条叫不出名字的河边。 战争的账,从来不是数字能算清的。一个人回来了,五十多个人没回来,这账怎么算?那些没回来的人,他们的爹娘谁来养老送终?他们的媳妇等了一辈子等了个空?他们没见过面的孩子,管谁叫爹? 翟文清后来留在村里,娶了媳妇,生了孩子,种地,养鸡,过起了普通日子。可每年清明,他都要去村后的山坡上烧纸,朝着北边磕头。他说栓子、老三、还有那些弟兄们,回不了家,他就替他们守着这个家。 村里人渐渐忘了那些没回来的人,只有翟文清记得。他记得每个人的脸,每个人说话的声音,每个人临死前说过的话。那些记忆像刀刻的一样,一辈子都磨不掉。 有时候他想,要是他也留在那儿了,会怎么样?他娘会不会也像那些人家一样,天天站在村口望?他爹会不会到死都闭不上眼? 可他回来了,活着回来了。这算不算一种幸运?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从那以后,他一个人活成了五十多个人的样子。他替他们吃饭,替他们干活,替他们看着这个他们再也没能回来的村子。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