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宗教中国化的议题颇为热门,天主教也面临同样的考验,需要切实研究如何进行中国化的实践。值此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百年将近之期,笔者讲述一历史事件,即关于在礼仪中脱帽的问题。
在2015年和2020年的中华圣母节将临之际,笔者曾经两次就同一主题撰写文章,也引起了一定的争议。而今天笔者所谈的话题相信同样会引起争议,然此为笔者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道光二十二年(1842),在张家口外西湾子新建成的第五座教堂中,蒙古代牧区宗座代牧孟振生开始了他的礼仪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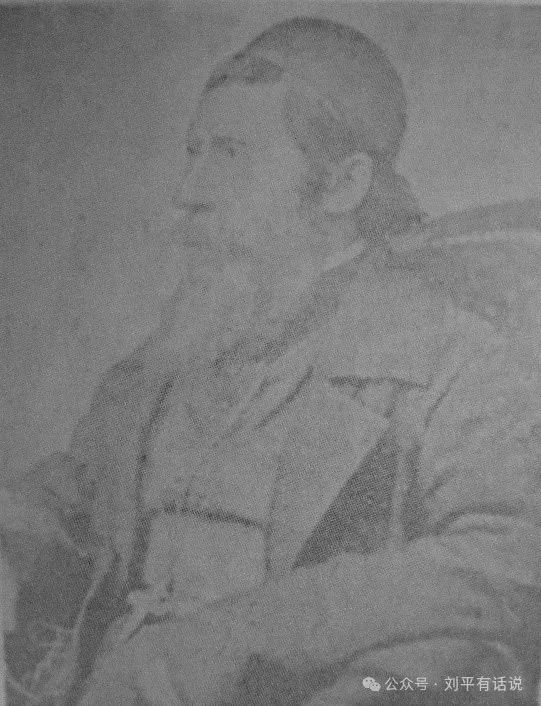
一、五项改革措施
首先是在那一年恢复了百年禁教时期中断的大礼咏唱弥撒。教友们在额我略圣咏的曲谱上方标注汉字发音,咏唱的部分有垂怜曲、光荣颂、信经、圣三颂、除免天主赦罪羔羊,其他部分则是奏乐,由十个辅祭的儿童领唱并以双笛做和音。
其次是在主日弥撒中加入了祝福面包的礼仪,然后将这些面包分发给信徒。在起初,孟振生认为这是一个古老的罗马礼传统。然而它只持续了大约十年后就被取消了,因为后来孟振生才知道那只是一个法国教会的习惯。经过与会长商议后,这一引进了十年的习惯被取消。
第三,西湾子是在百年禁教之后的中国境内第一个庆祝圣体圣血节的地方,这要归功于遣使会的传教士们,他们会在弥撒后在村里的每条街道上举行隆重的圣体游行礼以庆祝“天主节日”。
第四,孟振生命令本代牧区的神职班在弥撒礼仪中取消祭巾。
第五,其继任者达京又命令教友们在圣堂中应该脱帽。
最后这两点才是重点,它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和习惯。
二、利玛窦冠帽的文化意义
2013年,笔者曾在《浅谈利玛窦冠帽的文化意义》一文中提到在中华服饰的变迁上可以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意志。至明一朝则更为严格,因其推崇程朱理学,实行三纲五常,尤为突出皇权,总体更加细化。
在描绘利玛窦形象的画作中,国籍耶稣会修士游文辉(Manuel Pereira Yeou,1575-1633)在利玛窦去世前(1610)所留下的画作是目前最为标准的利玛窦像,画中的利玛窦头戴东坡巾,这是当时士大夫或称儒者阶层的体现,从而使其与“僧”区别开来而逐渐接近中华文明的核心。

此外另有传教士的画像戴有方巾,四方平定巾即方巾,是明代士大夫或称儒者最具代表性的巾式。《三才图会•衣服》述其来源谓:“方巾,此即古所谓'角巾',制同云巾,特少云文,相传国初服此,取四方平定之意。"

一个时代的服饰可以实证这个时代的文化现象,从黄帝“垂衣而治天下”的传说到中国古代冠服制度的完整出现,这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其至少具备了两方面的含义,既具礼仪意义,又具象征意义,且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即成年的象征、礼仪教化的象征、身份地位的象征、华夏民族的象征。
从春秋时期开始,戴帽子就成为中原文化区别于蛮夷文化的标志之一,虽经战国之动乱,但行冠礼和对于冠服的重视却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一脉相承,直到清朝开始剃发易服才逐渐丧失了这种传统。
有一种误区认为只有书生才会戴帽,其实成年男子均要戴帽,具体则分为冠、帽、巾,当然,这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在此不做赘述,并且其也在不断演变,随着时代而发生变迁。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逐渐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呈现出一派全盘西化的格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会了来自于中世纪欧洲表示服从与尊重的脱帽礼,这就是从蒙古代牧区第二任宗座代牧达京开始的。然而在中国,这具有截然相反的意义。中国人历来对“冠礼”尤为重视,这种来自于周礼的成人礼在男人为“冠礼”、在女人为“笄礼”,是一种比命还重要的礼仪,代表了成年以后必须担负的家族和社会责任,在皇家则是是否可以参与国家事务的治理和管辖之权,典型案例便是利玛窦所在万历朝的”国本之争“,其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故而对中国古人来说,”去冠“是最大的否定与伤害,同时对重视名节的文人士大夫来说更是充满了侮辱的意味,而”解剑“则是针对武人而言,所以当利玛窦开始佩戴“东坡巾”或“四方平定巾”,也就说明他开始进入了这个圈子,开始有了这个资格去接近中华文明的核心,才开始真正直面中国社会的主流儒家文化,这不仅是冠帽服饰的改变,更是意识形态的转变,所以他才会这样说:
我们全部身着中国服饰,只留下方帽以纪念十字架。今年,我改戴一顶类似主教礼冠式的帽子,非常奇怪,尖尖的。这样,我就完全打扮成了中国人的样子。[6]
三、孟振生取消祭巾
天主教的司铎们曾经出于尊重中国礼俗习惯中以戴帽来表示对于上级和对方尊重的需要,所以在礼仪中、在司铎举祭时有着使用祭巾的习俗,这祭巾是一顶方形小帽,帽子后方有两条长长的带子,让人想到主教的品帽。
只有最诚的公民或正直的官员才可以享有在国家更高官长面前戴帽子,有罪的人,即使再富有,按中国礼俗也不能带帽,尤其在长官前应保持脱帽。我们所有的人,神父和教友,在天主台前都是罪人,当我们来到天主台前,或至少我们做礼拜时,或向天求思或求赦时,应该脱掉头上的帽子,如同有罪的市民在他们的长官面前。即使是教外人不是也有求恩和谢罪的谦逊态度吗?所以教友们,尤其在礼仪中也应露出头,在天主台前犹如罪人在长官面前。[7]
孟振生是从罪人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人的冠帽习俗并且首先在神职班中加以改变。在蒙古地区改变这个旧礼俗时,[8]孟振生并不担心教友们会感到讶异。他之后诉说了这一改革的结果:“开始时在教友们中间引起一点奇怪的反应,过了一段时日之后,他们很自然的就习惯了。”
但是对于信友们戴着帽子参与礼仪的习惯,孟振生却什么也没提,他想教友们看见神父的做法后也许比较会容易改掉他们在堂里戴帽子的习惯,所以他让教友自由选取。当然,在笔者看来这也许是为了避免出现强烈的反弹。至于女教友在堂里罩头巾这个好习惯很早就有,神父们也一直让保留这个好习惯。这是一种谨慎而且值得赞扬的做法,孟振生只是改变了司铎们的习惯,而他的继任者达京则是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礼俗。
四、达京命令脱帽
在达京继任后,经过考虑,他决定在所辖蒙古地区取消男教友带帽的旧习。他曾出过布告:
我决定在本教区实行圣保禄宗徒的教导:我们应按天主所愿的方式来恭敬天主,在他台前按宗徒对教会的敬礼规定去做,男人应脱帽。从保禄宗徒的话中我们得知,天主愿意男人在堂内露出头来恭敬他,所以男人恭敬天主,在堂里不得戴帽子。
在法文的版本中,达京在写给欧洲的信件中提到了这一点:
在圣神的弥撒中,我一看到那些带着帽子参与礼仪的高傲行为,心中就非常难过。
笔者不知道达京是否受到了当时颇为流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至少在他的这一段文字中明显地看到了这种倾向;同时也幸而在他的神职班内并未出现像山西代牧区国籍司铎王廷荣那样的“中式民族主义”的践行者,不然这又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争端。[9]
总之,是达京在蒙古人的地区率先改变了中国人的礼俗习惯,而这本属于披发左衽的异族地区的汉人始终处于挣扎求存的状态,又加上清廷属于中国历朝历代以来中中央集权最为强大的时期,同样作为异族的统治者对于汉人历来实行了高压的政策,经过二百余年的岁月,原有的棱角已渐渐磨平,就连耶稣会传教士都经历了从“适应“到”服从”的转变,那么就遑论平民百姓了,也就难以再出现清初时期由于剃发令而产生的强烈反弹了。但可惜的是在日后的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这种强制性的外来输入代替了中国人本有的文化,从而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冲突与对立的反讽,在教会内形成了全盘西化的格局。[10]于是,这种脱帽的习惯在日后扩散到中国广大的教友群体当中而最终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就像西方的礼仪一样,一切都成了西方的样式。
[1] 刘平:《浅谈利玛窦冠帽的文化意义》,载于“刘平有话说”公众号,2023年11月20日。
[2] (汉)许慎著:《说文解字》卷七下,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56页。
[3] 伏兵:《中国古代的巾、帽弁和帻》,载于《四川丝绸》,成都:四川省丝绸工业研究所,2000年,第4期,第42-46页。
[4] 苏东坡字“子瞻”。周汛、高春明著:《中国古代服饰大观》,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5] 魏亚丽、杨浣:《西夏“东坡巾”初探》,载于《西夏学》,银川: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2013年,第9辑,第280-282页。
[6] 《利玛窦中国书札》,云娸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82页。
[7] 隆德理著:《西湾子圣教源流》,张保禄、苏俊杰编译,内部资料,2016年版,第39页。
[8] 在法文的版本里,孟振生也加以说明,他在所管辖的地区所做的并不与其他传教区相抵触。只要符合总体的原则,每个传教区可以自由地运用教会的宽免。
[9] 刘平编著:《天主教大同教区简史》,内部资料,2022年,第56-57页。
[10] 刘平著:《中国天主教艺术简史》,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4年,第260-261页。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