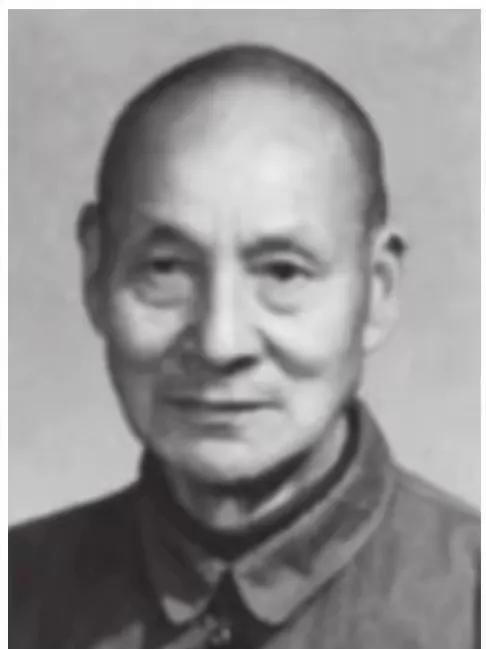孙立人台湾被捕前,力助张灵甫遗孀王玉龄赴美国,为她避开政治漩涡,但有个条件:不许嫁外国人.......
王玉龄19岁那年,丈夫张灵甫死在了战场。
宋美龄要接见殉职将领遗孀,19岁的王玉龄跟着其他遗孀一起去了总统府。
等了很久,武官出来告诉她们:“夫人今天身体不舒服,你们请回吧。”
多年后,王玉龄依旧很寒心地说:“对宋美龄没有什么好感,(这些殉职将领)把性命都送掉了,可她……”
年轻的王玉龄抱着孩子,带着老母亲站在台湾混乱的土地上。
本来已经十分艰难,然而很快,她就被骗光了所有的积蓄。
在她走投无路之时,是孙立人伸出了援手,将她送到了美国。
而孙立人对她的要求,只有一句警告,她记了大半生……
01
王玉龄出身于长沙的显赫家族。
王家在清末民初便深耕湘地商界,从粮油贸易到绸缎庄铺,几乎垄断了长沙西长街半数的商业资源。
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儿,王玉龄可谓是万千宠爱于一身。
父母拒绝让她遵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规,特意请了留洋归国的先生教她英文、算术,还送她进了长沙有名的“明宪女子中学”。
良好的新式教育,让她养成了既独立又骄傲的鲜明个性
她的人生本该是继续在校园中深造,考上上海或南京的女子大学。
或是由家族安排,嫁入另一个门当户对的商贾或官宦家庭,从此相夫教子,享受安稳顺遂的一生。
然而,命运却在她17岁时,猛地推了她一把。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王玉龄的远房舅舅,当时在国民党军中担任参谋的李树正,引荐王玉龄和张灵甫相见。
那一年,张灵甫42岁,是国民党军队中声名显赫的高级将领,正担任七十四师师长之职。
那时候的七十四师刚经历过湘西会战的惨烈厮杀,是蒋介石口中“御林军”,号称“五大主力”之首,张灵甫更是凭借战功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
张灵甫外形魁梧英俊,身高近一米九,军装穿在身上格外挺拔,在军中早有“儒将”的美名。
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也饱受世人争议。
他曾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高才生,为了投笔从戎,他毅然退学报考黄埔军校,最终毕业于黄埔四期,与林彪、刘志丹等人同为校友。
他还精通书法,尤擅楷书,不少同僚都曾向他求字。
张灵甫身上的“英雄光环”,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王玉龄后来在采访中也承认,初见时,她对张灵甫怀有几分出于少女情怀的崇拜与仰慕。
但横亘在两人之间的,是难以逾越的现实障碍。
17岁与42岁,这整整25年的年龄差距,足以让任何一个重视门风的家庭望而却步。
更何况,张灵甫已经历过三段婚姻。
第一任妻子邢凤英是父母包办的旧式女子,两人感情淡薄。
第三任妻子高艳玉因性格不合早已分开。
最让外界议论纷纷的,是第二任妻子吴海兰。
1935年,张灵甫怀疑吴海兰是间谍,在陕西西安的家中,亲手用手枪结束了她的生命,酿成了当年轰动一时的“团长古城杀妻案”。
而王玉龄,是王家捧在手心的掌上明珠,王玉龄的母亲罗希韫,从一开始就对这门亲事表达了明确的反对。
她怕女儿嫁给一个有过如此复杂过往的男人,将来受委屈;更怕张家的风波,会牵连到王家。
然而,张灵甫对王玉龄展开了军人般热烈而直接的追求。
给王玉龄带上海最新出版的言情小说,给罗希韫带杭州的丝绸手帕。他会坐在客厅里,和王玉龄的父亲聊时局,也会耐心听王玉龄讲学校里的趣事,展现出一个成熟男性的多重魅力:既有军人的果断坚毅,又不失文人的儒雅风度。
1945年的国民党政权,正处于战后的“全盛时期”,张灵甫作为“王牌师”师长,前途不可限量。
对王玉龄的家族而言,经历过抗战期间的商业动荡,他们太需要一个有权势的“靠山”。
与这位手握重兵的将军联姻,无异于为家族的未来绑定了一份最有力的保障。
1945年秋,两人的婚礼在上海顶级的金门饭店举行,轰动一时。
当时的金门饭店,是上海租界内最豪华的场所之一,能在这里办婚礼的,非富即贵。婚礼当天,国民党军中的不少高官都前来道贺,七十四师的军官们更是集体出席,场面盛大。
17岁的王玉龄,身披洁白的西式婚纱,头戴珍珠头纱,在父亲的陪伴下,嫁给了42岁的张灵甫,成为他的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
她的人生,自此便与这个男人,以及他所卷入的时代洪流,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
婚后的时光,虽然短暂,却也称得上是幸福的。
张灵甫不久后晋升为七十四师师长兼任南京警备司令,手握南京城的防务大权。王玉龄作为“司令夫人”,居住在南京五台山附近的豪华花园别墅中。
那是一座带泳池和网球场的西式洋房,是国民党当局专门为高级将领配备的住宅,这样的生活,足以让当时的许多人艳羡。
王玉龄迅速地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转变为一名合格的军官妻子。
她跟着家中的老佣人学做饭,学着打理别墅里的大小事务,甚至会提前打听张灵甫同僚的喜好,在他宴请客人时帮忙招待。
王玉龄周到地照顾着丈夫的日常起居,知道张灵甫有晚上看书的习惯,她会提前暖好被窝,在床头放一杯温水;知道他胃不好,从不让厨房做生冷的食物。
尽管张灵甫天性严肃,不善言辞,在军中以严厉著称,但他对这位年轻的妻子却十分呵护。
他从不向她提及战场上的血腥与残酷,从不在她面前抱怨军务的繁琐。
“他从来不跟我说军事上的事。”王玉龄后来在回忆这段时光时,眼神里还带着温柔,“让我觉得,好像只要他在,我在哪里都不害怕。”
即便在前线战事最紧张的时候,比如1946年七十四师奉命开赴苏北作战时,张灵甫依然坚持一个习惯:“每天一定打一个电话回家。”
电话内容总是很简单,不过是寥寥几句。他会先问:“家里好不好?”听到王玉龄说“好”,再叮嘱几句“照顾好自己”,便匆匆挂了电话,军中纪律严格,他不能在私人电话上花费太多时间。
但就是这几句简单的问候,成了王玉龄那段日子里最安心的慰藉。他用这种内敛而笨拙的方式,维系着对家庭的全部关怀。
那时的王玉龄还太年轻,刚满18岁,她并不真正理解战争的重量,不明白“国共内战”这四个字背后意味着什么。
她只是全然沉浸在新婚宴尔的甜蜜中,沉浸在即将成为母亲的喜悦之中。
1947年初,在南京的寒冬里,王玉龄诞下了儿子。张灵甫为孩子取名“张道宇”,寄托着他对儿子的期许。
这个新生命的降临,给这个军人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温暖和对未来的美好期许。张灵甫只要有空回家,就会抱着儿子不肯撒手,还会笨拙地学着给孩子换尿布
1947年5月,孩子出生才刚满百日,解放战争已进入了关键的转折点。
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对国民党军发起了猛烈进攻,孟良崮战役爆发。
张灵甫和他引以为傲的“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彻底围困在孟良崮的山顶上。彼时的孟良崮,光秃秃的石头山,没有水源,没有粮草,七十四师的士兵们只能靠空投的物资勉强支撑,陷入了绝境。
1947年5月16日,国民党当局通过广播发布消息:整编第七十四师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兵败身亡。
那一年,王玉龄年仅19岁。
她成了寡妇。
02
一个19岁的寡妇,怀里抱着尚在哺乳期的婴儿,身边只有同样需要人照顾的年迈母亲。
丈夫的死讯,将王玉龄推入了无底的黑暗深渊。
她终日以泪洗面,悲痛到几乎无法自已。
1947年下半年,孟良崮战役的硝烟刚散,解放战争的态势已彻底扭转。
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站稳脚跟,晋冀鲁豫野战军又强渡黄河,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接连受挫,原本的“全面进攻”被迫转为“重点进攻”,颓势一天比一天明显。
南京城内的高官眷属,开始悄悄收拾行李,空气中都弥漫着“要走”的恐慌。
就在王玉龄还沉浸在丧夫之痛中无法自拔时,她周遭的世界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剧变。
原本门庭若市的国民党党部,如今进出的人都步履匆匆,脸上没了往日的傲慢;连家里的老佣人买菜回来,都会压低声音说“城外的兵又换防了”,
她的安稳的日子,早就没了。
同年12月,国府向七十四师孟良崮战役阵亡官佐遗族发放抚恤金五亿元,其中拨给师长张灵甫遗族一亿元。
但以1947年8月一斗米(6.9公斤)售价二千万元的物价计算,一亿元只能购买五斗米。
王玉龄的娘家远在长沙,是深耕湘地几十年的富商。王家在长沙西长街有十几间铺面,从粮油到绸缎,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就算战乱年代,也能靠着囤积的物资和人脉,让一家人衣食无忧。
如果按照她自己的意愿,她最想做的,就是带着母亲和幼子返回长沙老家。
可是,当时的局势,已经容不得她这样一个19岁的寡妇自己做出选择了。
“总统府”的电话,开始频繁地打到她的家中。
第一次接到电话时,是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刚打响不久。
电话那头是个陌生的男声,语气还算客气,说“奉上面指示,请张师长遗孀做好转移准备”,没提具体去哪里,只让她“随时等候通知”。
王玉龄当时没放在心上,只当是例行公事的提醒。
可没过半个月,电话又打来了。
这次的语气明显急迫了许多,直接点明“请夫人尽快收拾行李,目的地是台湾”,还强调“这是为了保护您和孩子的安全”。
王玉龄起初非常抗拒。
她从小在长沙长大,后来随张灵甫到南京,从未离开过大陆。
台湾?在她的认知里,那只是地图角落里一个遥远的海岛,连气候、语言都不知道和家乡差多少。
她不想离开生她养她的故土,更不想带着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第三次电话打来时,语气已经变得强硬。
电话那头的人不再客气,直接说“夫人,这不是商量,是命令”,还毫不掩饰地警告她,如果她们选择留下,“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
王玉龄虽然涉世未深,但她不是傻瓜。
王玉龄知道,丈夫是国民党的“烈士”,而她这个“烈士遗孀”,早已不是普通的寡妇,而是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政治符号。
当局绝不会允许这个“符号”流落到对岸,更怕她被当成“统战对象”。如果她不听话,别说回长沙,恐怕连南京的家都待不下去。
1948年底,在巨大的恐惧和深切的无奈之下,王玉龄做出了她人生中第一个艰难的决定。
她让老佣人把张灵甫的书画、军装仔细打包,又给母亲和儿子收拾了几件冬衣,她不知道台湾冷不冷,只能尽量多带些衣物。
她带着刚满1岁的儿子张道宇,搀扶着不停抹眼泪的母亲罗希韫,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再从上海转乘轮船,驶向那个未知的海岛。
她不断地安慰自己,丈夫毕竟是“抗日名将”,是为党国“壮烈成仁”的。就算到了台湾,国民党当局总会念及这份功劳和情面,不会亏待她们孤儿寡母。
她觉得,凭借丈夫生前的威望和“忠烈”身份,自己和家人理应得到应有的照顾,至少能有一间安稳的房子,能让母亲安度晚年,让儿子有饭吃、有学上。
然而,当轮船缓缓靠上台南的码头时,她所有的幻想,都在踏上土地的那一刻,被现实击得粉碎。
眼前的景象,让她惊骇不已。
码头上挤满了人,大多是穿着破烂军装的士兵,还有拎着包袱、一脸茫然的难民。
混乱的人群中,不时传来争吵声、孩子的哭声,还有士兵粗鲁的呵斥声,完全没有“避难所”该有的安稳。
当时的台湾,刚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脱离不久,国民政府接收后还没来得及整顿,就因为内战,短时间内涌入了近百万军队和难民。
有限的资源被迅速耗尽,整个岛早已陷入了彻底的失序和混乱。
这些失去军纪的士兵,在街头巷尾四处游荡。
今天抢了街角的杂货店,明天又在菜市场和小贩打架,甚至有士兵大白天闯进民宅,抢走百姓家里仅有的粮食。
王玉龄当时才20岁,穿着一身素雅的旗袍,容貌出众,一看就是外来的“大陆太太”。
身边跟着年老体弱的母亲,怀里抱着嗷嗷待哺的幼子,在这样野蛮生长的混乱环境里,她们无疑是最容易被盯上、被伤害的目标。
当局给她们安排的“住处”,是台南郊区一间破旧的平房。屋子只有十几平米,墙壁上满是裂缝,下雨天还会漏水。
里面只有两张木板床,一张桌子,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和南京的别墅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王玉龄每天所能做的,就是待在房间里,透过窗户上糊的旧报纸,惊恐地望着外面混乱不堪的街道。
带来的积蓄很快就会花光,而当局承诺的“照顾”,迟迟没有兑现。
母亲罗希韫也整日里提心吊胆,常常坐在床边偷偷抹眼泪。
带来的积蓄很快就会花光,而当局承诺的“照顾”,迟迟没有兑现。
王玉龄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摸出藏在床板下的小布包,数着里面剩下的几张纸币。
就在她为生计愁得夜不能寐时,一个穿着灰布西装的男人,敲响了她的房门。
03
男人看起来三十多岁,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手里拎着一个旧皮公文包,说话时带着几分斯文的客气:“请问是张灵甫将军的遗孀王玉龄女士吗?”
王玉龄警惕地挡在门口,问他有什么事。
男人笑了笑,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到她面前:“我是做粮油贸易的,听说您近来有些难处,想着或许能帮上忙。”
王玉龄看着名片上模糊的字迹,心里依旧防备,在这混乱的地方,陌生人的“好意”总让她不安。
可男人似乎看穿了她的顾虑,语气愈发诚恳:“我知道您现在不信我,可眼下这世道,光靠省是撑不下去的。您手里要是有闲钱,不如做点小投资,我这边有渠道能拿到低价粮油,转卖出去能赚不少,足够让您和家人安稳度日。”
王玉龄想起母亲偷偷抹泪的样子,想起儿子饿肚子时瘪着的小嘴,想起自己连日来的焦虑,心里的防备开始松动。
接下来几天,男人又接连来了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