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78年,17岁的郑智化,穿着一身黑,去见一个穿一身白的女孩子。
女孩是某校刊主编,约他写稿。稿子主题是“对现代医生的观感”。郑智化两岁得小儿麻痹,跟医生打了半辈子交道,一肚子话想说。
两人约在台北工专对面的“吉和利”西餐厅,女孩讲话慢慢的,不愠不火,眼神很静。郑智化说,他讨厌医生。女孩问,如果我将来也是个医生呢?
郑智化愣住了,看着她长长的睫毛,想了半天说:
如果你将来是个医生,你要有感情。
稿子他写了,题目是《一个有感情的医生》。后来去参加作者茶会,一帮大学生作者在那儿引经据典,什么社会学、人文结构、教育缺失、全民医保……郑智化听得脑仁疼,轮到他发言,他站起来,撑着拐杖,扔下一句话就走了:
我认为你们很无聊!
稿费都没拿就扬长而去。
这股劲儿,又倔又狂,像块石头。但那个白衣女孩,似乎就喜欢他这股劲儿。她打来电话,说至少得把稿费拿走。郑智化心里闪过一个念头,问她:“你翘过课吗?”
“没有。”
“我想翘课,把稿费花掉!”
“好啊!”她答应得干脆利落。

第二天,一辆红色小金龟停在他面前。车门打开,驾驶座上坐着的,是一个穿黑色皮茄克、紧身迷你裙的女人。郑智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笑了,有点反击的味道:
有时看人不能只看外表!
她开着车往阳明山狂飙,在一幢别墅前停下。她说这是她爷爷的房子,爷爷死了就没人住了。她爷爷是医生,也是剑道高手,家里除了奶奶,一水儿的医生。
在那栋空旷的别墅里,女孩给他看泛黄的老照片,听没有贝斯的日本老歌,还为他研墨,看他提笔,写下八个字:
颜心如一,率性而行。
这是他的人生信条。他把稿费全买了红玫瑰,在女孩飙车的路上,把花瓣一片片撕碎,从车窗扔出去,像一场血红色的雨。
他们就这样好上了。一个是叛逆的少年,一个是骄傲的富家女。
故事的结局,并不意外。
女孩的父母要请他吃饭。他们住在一栋大厦的顶层,门口有养着金鲤鱼的喷泉,大厅里是波斯地毯、古董家具、米罗的版画和张大千的字画。
刚见面,女孩父母就撂过来一对鄙视的眼神,不知是因为郑智化瘸着的腿,还是因为穷,总之,饭桌上冷言冷语,暗示他知难而退。
饭没吃完,郑智化就走了。他没生气,他知道,他们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女孩追了出来,满脸是泪。那一晚,他们喝得烂醉,在旅馆里,她像大海一样淹没了他。
从此,他再也没见过她。
这段夭折的初恋,后来被他写成了一首歌,叫《别哭,我最爱的人》。原名叫《昙花》,歌里唱:
是否记得我骄傲的说
这世界我曾经来过
不要告诉我永恒是什么
我在最灿烂的瞬间毁灭
多年以后,这个曾经又倔又狂的,叫郑智化的男人,因为在深圳机场跟工作人员闹了点不愉快,被拱上热搜。然而,很多00后一脸问号:
这人谁啊?

-2-
对9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郑智化不是一个名字,是一个符号。
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整个中国像一口烧开了的水,到处都是蒸腾的热气和翻滚的欲望。旧的秩序正在瓦解,新的规则还没建立,无数年轻人正经历着从“革命青年”到“求知青年”再到“置业青年”的身份转换。他们从单位、从乡村涌向市场经济的洪流,寻找自己的位置。
那是充满机遇的时代,也是信仰真空的时代。人们迷茫、焦虑,迫切需要抓住点什么。港台流行文化,就像打开了一扇窗,让大陆的年轻人看到了另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就在这时,郑智化的歌传过来了,在一众港台歌手里,显得异类。《水手》和《星星点灯》,几乎是一夜之间,响彻了中国所有城市的录像厅、理发店和大学宿舍的破录音机里。
苦涩的沙 吹痛脸庞的感觉
像父亲的责骂 母亲的哭泣
……
如今的我 生活就像在演戏
说着言不由衷的话 戴着伪善的面具
总是拿着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
这歌词,没有华丽的辞藻,简单、粗粝,却砸进了一代人的心巴上。在那个集体主义消散,提倡个人奋斗的年代,这首歌成了无数小镇青年在大城市打拼时的精神图腾。它告诉你,别抱怨,别哭,靠自己。
郑智化说,《水手》的灵感,是他在浴缸里泡澡时想到的。他想象自己躺在船上,看着星星,那种漂泊无依的感觉,正是那个时代所有年轻人的内心写照。
还有《星星点灯》: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
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
这简直就是写给那个时代,所有离乡背井、前路茫茫的年轻人的。郑智化的歌,用最朴素的方式,重建了一种世俗的、个人的信念:坚韧、希望、不认命。
所以,当三十年后,电影《万里归途》里再次响起《星星点灯》的旋律时,很多70后、80后当场泪崩。他们哭的不是电影,是自己回不去的青春,是那个在黑暗中摸索,抬头寻找星光的自己。
但如果00后们以为郑智化只是个写励志歌曲的心灵鸡汤大师,那就太小看他了。励志,只是他最温情的那一面。
他骨子里,是个斗士,是个握着手术刀的解剖者。他的另一面,藏在那些没那么流行的歌里,锋利得能划出血。
比如,那首神作《大国民》。
1993年,他用一种近乎戏谑的口吻,把当时台湾社会的种种怪状骂了个遍:
美丽的谎言说过多少遍
说来说去从来没实现
宣传的口号说大家都有钱
贫富的差距假装没看见
这不再是个适合好人住的岛
礼义廉耻没有钞票重要
这不再是个适合穷人住的岛
一辈子辛苦连个房子都买不到
歌词辛辣,撕开了整个社会的荒诞和虚伪(事实上,虽然他写的是那个“岛”,但在当时大陆青年听来,也同样适用)。这首歌,在当时岛内引起巨大争议,但郑智化不在乎——他天生就是个“问题学生”。
上小学时,生活与伦理课考试有道是非题:“下课要赶快跑,才能到福利社买到零食吃?”标准答案是“×”。郑智化毫不犹豫地写了“○”,因为这就是事实。结果,被老师罚站了一节课。
从那时起,他就明白了大人的世界有多虚伪。他讨厌被说教,讨厌循规蹈矩。这种叛逆,贯穿了他的一生。
国中时,他和国文老师争辩“智者不惑”。他认为越聪明的人疑惑越多,“智者不惑”根本是无稽之谈。结果被班导师狠狠甩了一巴掌,耳朵嗡嗡响了一个礼拜。
从此,他变得沉默,他知道在那种环境里,强出头没用。
这种沉默,后来都变成了歌词里的愤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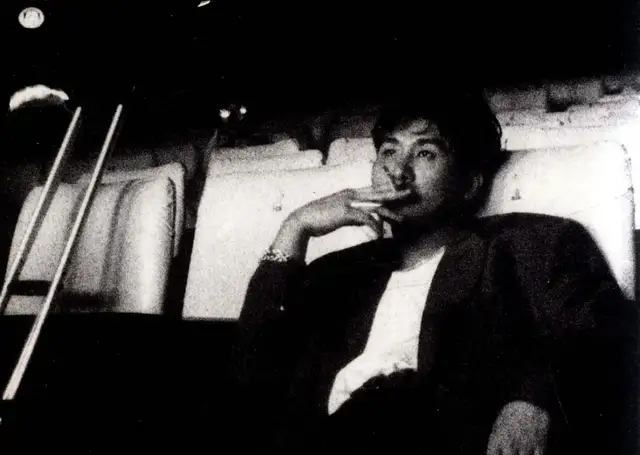
-3-
他关心社会底层,关心那些被遗忘的人。
他的第一张专辑叫《老么的故事》,灵感来自1984年台湾海山煤矿的一场真实矿难。他亲自跑到矿区,和矿工家属同吃同住一个月,写下了小人物的悲歌:
黑色的煤渣 白色的雾
阿爸在坑里不断地挖 养活我们这一家
娇纵的老幺 倔强的我
命运是什么我不懂 都市才有我的梦
谁说宠坏的孩子不哭
就在悲剧发生的那一瞬间
泪水呐喊换不回 阿爸在淹没的矿坑里面
他还写《堕落天使》,讲一个在台北林森北路风尘女子阿玫的故事。郑智化曾经在自己的书里,写下了这个真实的故事。
阿玫为了给身体不好的爱人治病,十六七岁就从嘉义跑到台北“做那个”,每个月寄钱回去。后来她用攒下的钱和爱人开了家鸡肉饭店,以为可以开始新生活。结果以前的客人找上门来,戳穿了她的过去。丈夫受不了打击,她也只能默默关掉店,消失在人海。
就把灵魂装入空虚的口袋
走向另一个陌生
无可救药的歇斯底里和一派的天真
刻意的美丽包装着一个嫉妒的女人
是你攻陷别人
还是别人攻陷你最后的防线
他的歌里,没有那么多风花雪月,更多的是人间的真实、挣扎和无奈。
这种批判精神,三十多年没变过。他后来不做音乐了,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写书法,点评时事,言辞依旧犀利。他发过一段文字,被网友称为是对台湾现状最深刻的诠释:
这里的人不讲英文但帮美国看门,这里的人不讲日文但认日本祖宗,这里的人讲中文写中文但视中国(大陆)为敌人。
你看,从17岁那个敢在茶会上说“你们很无聊”的少年,到60多岁还在网上硬刚的“老炮儿”,他还是那个“颜心如一,率性而行”的郑智化。
郑智化的人生,就是他那首《水手》的现实版。只不过,他面对的风暴,来得更早,也更猛烈。

-4-
两岁时,一场高烧,小儿麻痹症夺走了郑智化奔跑的能力。七岁以前,他都是靠爬行移动身体。
他后来回忆,“爬行的姿势是趴着;双腿走路是站着,天生注定我看东西的角度和其他人不一样。”
因为身体的缺陷,他成了敏锐的观察者。为了医好他的腿,家人带他看遍了台湾的医生,尝试了各种治疗。他最怕的是移骨推拿的拳头师傅,五岁那年,在一次治疗中,他痛得几乎昏过去。
从那以后,他对医生就没了好感。
七岁那年,为了能上学,他接受了手术。从手术室醒来,双腿打着石膏,又痒又痛,像被蚂蚁啃。他想哭想挣扎,但护士告诉他,如果乱动,碰到伤口,就一辈子不能走路了。
于是,他忍了下来。
一个月后,拆掉石膏,又是长达一个月的物理治疗。他扶着双杠,吃力地移动脚步,重新学习走路。他说:
我会走路了!虽然比别的小孩整整慢了六年。
身体的磨难没有让他自卑,反而让他从小就成了个“不好惹”的孩子。小学四年级,一个高年级的男生从背后用脚勾倒他的拐杖。
他没哭,假装爬起来,趁对方不备,用拐杖重击他的腿,又一拐杖打中他的头,对方流血不止,缝了十二针。
从此,“不好惹”的封号传遍全校。
他还学会了做生意。把打弹珠赢来的弹珠和纸牌分类,低价卖给同学,后来还雇了几个“学有专精”的同学帮他赢货,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直到被老师告密充公。
这段经历让他明白,自己将来一定很会“赚钱”,不会成为家里的累赘。
从台北工专毕业后,他先是在工程公司做结构计算,每天穿着制服,过着朝九晚五的日子。他觉得那种太过规律的生活会让人变得迟钝。
有一天,他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店,看到一群穿着黑色皮衣的年轻人,充满了一股自由的活力。他看看自己身上的制服,手上的设计图,问自己:难道我就这么过一生?
不!绝不!
回到公司,他立刻辞了职。
辞职后,他决定去做广告。
一个对广告一窍不通的门外汉,看到报纸上招聘“COPYWRITER”(文案撰稿),以为是“影印抄写员”,就寄了简历。笔试时,他看着题目上的“Catch&Body”,举手问面试官:“请问为什么要‘抓住’、‘身体’?”
全场傻眼。 (其实“Catch&Body”是“标题和文案”的意思)
但广告公司的总经理看中了他身上那股劲儿,居然录用了他。
为了补上差距,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疯狂学习广告知识。一年后,他策划的“开心洗发精”广告大获成功,他为广告写的歌《开心女孩》,也传遍大街小巷,并因此被唱片公司看中,一脚踏进了音乐圈。
在广告界干了六年半,他说,最大的收获,不是创作了多少广告,而是学会了如何思考,如何包容各种不同的人。

-5-
1999年,在事业巅峰期,他突然宣布退出歌坛,结婚生女,一头扎进IT行业,成为一家科技公司的CEO,开发股票决策软件和幼教软件。
他的人生,一直在跨界,一直在折腾,从没被“残障”或“歌手”的标签定义过。他画画、写诗、搞IT,样样都玩得转。
所以,很多年轻人听着被包装过的偶像唱着甜腻情歌时,可能很难想象,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歌手。他的歌声沧桑、粗糙,甚至有点“难听”,但他唱的是时代的真相,和一个不屈服的灵魂。
这次,郑智化与深圳机场的风波,我们不想探究孰对孰错,但有人讽刺他为了“追逐名利”,这个就属于“小人之心”了。其实,在发微博当下,他可能是愤怒的不满的抱怨的,但唯独不会有对于“名利”的诉求。
因为,他很早就说过,“我不想做空心的偶像:或是到处谄媚逢迎的、汲取名利的小丑。”
在郑智化最巅峰的时候,他不用粉丝打榜,也没有资本加注,他只是把自己看到的世界,和内心的挣扎,写成歌,像冰雹一样,砸向这个世界。
然后,激流勇退。
这,就是00后没听过的郑智化。
一名用拐杖撑起一个时代,用歌声戳破所有伪装的“问题学生”。
本文参考书目:
《郑智化的传奇》(中国青年出版社 郑智化著)
撰稿 | Jana策划 | 文娱春秋编辑部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