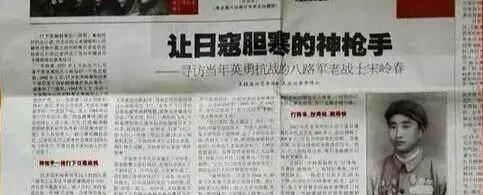1942年5月6日,山西临汾市吉县安平村的一间窑洞里,发生了奇怪的一幕,若干名侵华日军的高级军官,正与几位身着便装的中国人“亲切交流”,这便是抗战期间鲜为人知的“安平会谈”。双方头目的身份更是惊人:一边是日寇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另一边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山西省主席、陆军一级上将阎锡山。
《亮剑》中的老鬼子筱冢义男,想必读者印象都很深刻,历史上也确有其人,时任日寇第一军司令官,不过这家伙并没有一直呆在太原。
1941年6月底,筱冢调回本土担任陆军士官学校的校长,接替职务的,便是日本国内“中部防卫军”的司令官岩松义雄,抗战初期的第15师团长。
日阎这次会谈的中心内容,是讨论阎锡山如何叛变投敌的问题,会谈中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少将(这厮是“九一八事变”的元凶之一),要求阎锡山应尽早发出所谓的“和平通电”,而且是“如果可能就在五月内发出”,阎锡山不肯答应,坚持说还需要些时间。
阎锡山反而提出,日军应提供更多的钱款、物资和军火,然后才能进入”实现和平“的实质性操作,几乎到了漫天要价的程度,日本人后来在报告中写道:“内容多有超过曾经约定的条件”。
岩松义雄当场大为不满,指责阎锡山出尔反尔,阎老西也不甘示弱,声称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此一时彼一时也,日本人无奈之下,建议双方暂时休会,抽抽烟喝喝茶吃点东西再谈。
阎锡山之选择在安平村会谈,是因为此地距离两军防线分别为15公里,属于军事真空地带,不料就在喝茶期间,晋绥军的警卫人员突然发现:远处蜿蜒的山路上,突然有日军大队前来!

一、阎锡山的抗日态度趋于消极
应该说,阎锡山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抗日态度还是比较坚决的,毕竟日本人所觊觎的三晋大地,是他经营多年的地盘和老窝,当然不肯拱手相让,遂有惨烈的忻口会战和太原保卫战,期间晋绥军还算是比较卖力气的。
山西当时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而阎锡山的理论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企图周旋于日军、中央军和八路军之间,尽量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料到了1939年前后,三个鸡蛋几乎都快踩破了,阎锡山的处境变得十分困难。
首先是与八路军的关系,因“山西新军”问题撕破了脸,1939年12月,阎锡山在重庆当局的蛊惑下,悍然发动“晋西事变”,晋军“新旧”两军刀兵相见,这样的倒行逆施,后果是灾难性的:12万新军大部分参加了八路军,而阎系部队也被揍得鼻青脸肿。
日寇驻山西的第一军,也不断步步蚕食,当时山西全境共有105个县,被日伪控制的多达85个,再加上中央军和八路军的控制区,阎锡山的防区被压缩到10几个县,兵源、财政、粮食的获取渠道,接近枯竭。
而驻晋南(主要是中条山防区)的中央军各部,为了争夺粮饷,也在不停地“欺负”晋绥军,比如第27军范汉杰所部、第93军刘戡所部,都把防区内的县长,强行换成了自己的人。阎锡山多次要求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约束,然而范、刘都是胡宗南系统的部队,根本没戏。
因此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阎锡山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他能够控制的地盘最惨的时候,只剩下4个县;晋绥军也由于连战连败,以及补充的困难,虽然还撑着四个集团军的番号,实际只剩4万余人的兵力。
随着晋绥军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作为一名老牌军阀,阎锡山开始打起歪主意了,企图借助山西日寇的力量,恢复并扩大他的反动势力和实力,终于萌生了突破民族大义这个底线的龌龊念头。

在1940年晚些时候的一次谈话中,阎锡山曾对心腹赵承绶说道:“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 老蒋要借抗战的名消灭咱们, 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 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八路军对咱们更不好, 到处打击咱们,把老百姓都拿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 那就只有被消灭”。
阎锡山最后的结论是:“权衡情况, 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 才能发展咱们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 也是咱们唯一的出路”。要说军阀就是军阀,面临生死关头之时,什么大义和气节都可以抛在脑后。
二、阎锡山加快叛变投敌的脚步
对于阎锡山的处境,日本人也看得很清楚,鉴于华北方面军兵力并不充足,同时也为了拉拢各地方实力派反对重庆政府,驻山西第一军开始了对阎锡山的诱降工作,并得到了北平方面军司令部和南京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支持,代号“伯工作”。
1940年初,日军通过阎锡山的表侄曲某和商人阎宜亭,与晋军建立了秘密联系渠道,甚至派出大特务直接来到“克难坡”,与阎锡山当面谈判,核心内容是日军和晋绥军应实施停战,共同对付八路军和决死队,同时“实行物资交换, 互通有无”。
所谓的“克难坡”,是位于吉县西北30公里处的一个黄土山头,阎锡山在1940年之前,曾一度狼狈地逃过黄河进入陕北,短期在秋林县落脚。1940年返回山西境内后,选中这个山头大挖窑洞,将二战区长官部、山西省府等机构,全部设于此处。
在双方秘密勾结之初,阎锡山的态度还是比较暧昧的,不肯轻易”反水“,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仍在观望国际国内形势;其二是担心实力不济,一旦投敌必遭国共军队的联合打击;其三是内部思想也很难统一,并不是每个晋绥军将领都愿意当汉奸的。
这一拖就是一年多,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两次重大事件,直接刺激了阎锡山的神经,对抗战的前途更加悲观,从而加快了与日军勾结的脚步,还秘密派出高级军官赴太原谈判,叛变投敌的征候愈发明显。
第一件事,是1941年5月爆发的中条山会战,又称为”晋南会战“,在这次战役中,卫立煌第一战区遭遇惨败,中央军驻晋南的两个集团军20万大军损失殆尽,阎锡山不免有兔死狐悲的感觉,认定自己也绝难招架日军的攻击。
第二件事,是1941年6月《日苏中立条约》的签署,苏联为集中力量对付纳粹德国的威胁,放弃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与日本达成妥协,这让阎锡山感到抗战前途的渺茫,立场开始动摇。

在这样的形势下,阎日之间的勾结开始提速, 1941年6月26日,日寇第一军向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汇报说:“对伯工作志在必得, 阎即将出马, 只要日方不提出无理要求, 就几乎会成功”。
至6月30日,日军与阎方代表刘吉甫在太原会面,就阎锡山投敌的几项条款,基本达成共识(协议内容后来有所调整):
1、晋军扩编至30万人(绥远已是傅作义的地盘,不能计入), 军械给养由南京伪政权转拨。
2、阎政权发行三千万纸币的晋钞,由日方提供准备金,同时发还阎锡山在太原的财产,晋北的13县也交还给晋军控制。
3、双方8月1日左右在太原签字后, 阎须宣布脱离重庆政府, 加入所谓的“东亚新秩序”, 签字代表日方为司令官或其参谋长,阎系代表为赵承绶、王靖国。
汪逆精卫也在日本人的压力下,开出价码,同意阎锡山未来可出任南京伪政权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华北国防总司令、山西省主席”,日军为表示“诚意”,还提议可自晋南、晋西13县撤军, 将其交还给晋军,阎锡山的投敌活动,此刻已是箭在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