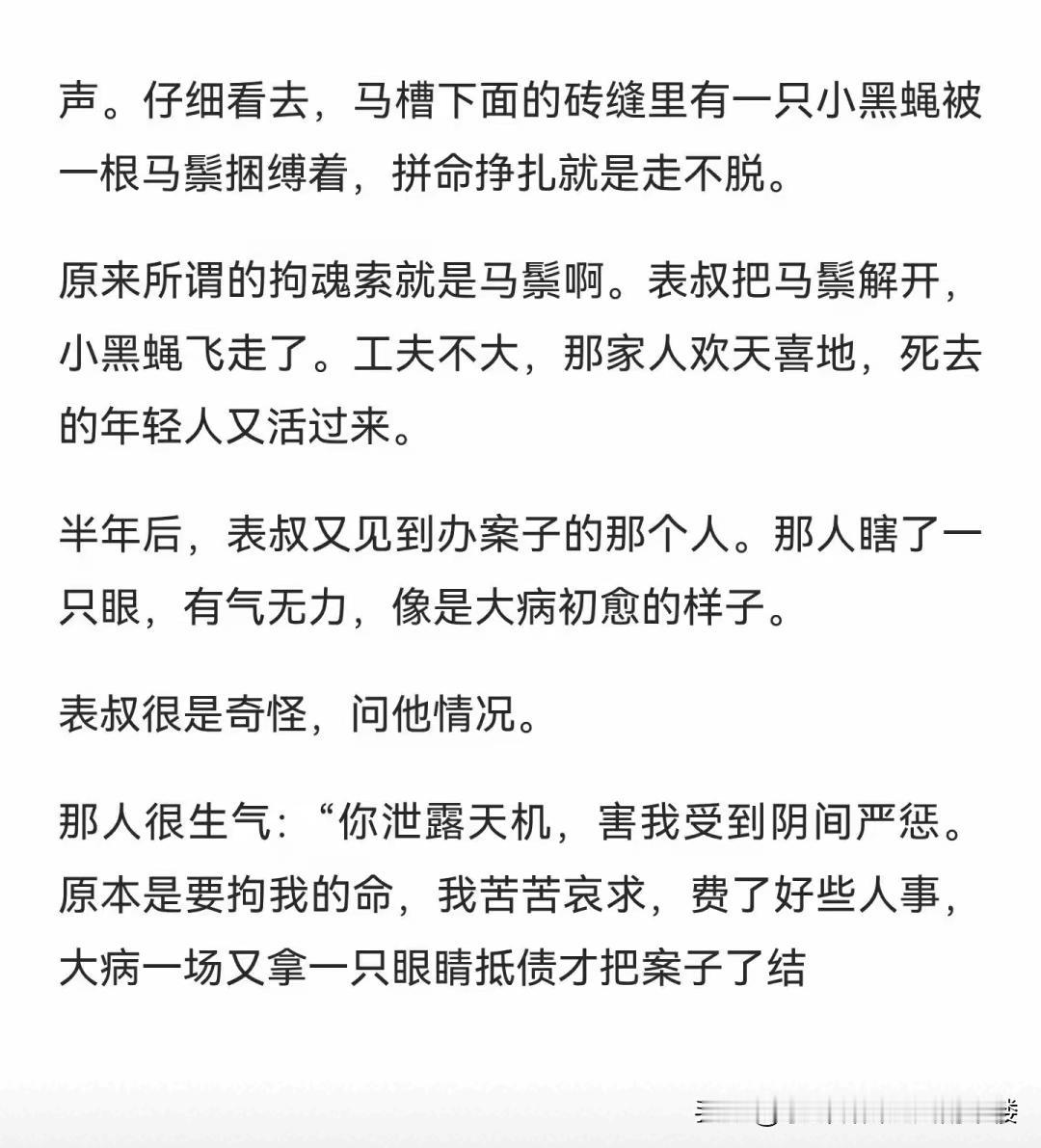“没有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登天的路,我也能一步一步爬上去!”
那天,在滇缅公路上,为了完成那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拉着最后一车军火冲进日军包围圈...
保山运输站的油毡棚顶被山风吹得哗哗响,我蹲在门槛上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手,盯着老站长往我军用水壶里续了第三遍茶。
“承远啊,这趟货得加把劲。”老站长的旱烟杆在桌子上敲得咚咚响,“100箱德制迫击炮弹,前线等着炸鬼子的钢炮呢。”
我捏着任务单的手紧了紧,油印的字迹有些模糊:“老站长,上回张大胆的车队在龙陵翻了车,您说这趟...”
“上回是暴雨冲垮了路基,这回不一样。”老站长突然压低声音,烟锅头几乎要戳到我鼻尖,“这三天我眼皮子跳得慌,你记着,装车时在右后轮挡泥板刷蓝漆……别问为啥,照做就是。”
我盯着他眼角的皱纹,那里面藏着比滇缅公路还深的故事。三个月前他还只是个管仓库的,现在成了运输站站长,听说前两任都在伏击里没了。
“铁柱!带弟兄们装车!”我把任务单往怀里一揣,冲外头喊了一嗓子。副队长王铁柱晃着铁塔似的身子进来,腰间的驳壳枪撞得门框哐当响:“周队,听说这回是德械?咱卡车能颠散架不?”
“颠散架也得拉!”我拍了拍他厚实的后背,“你开首车,我压尾。”

车队出发时刚过晌午,72道拐的山雾像团湿棉花,裹着卡车的排气管往上涌。王铁柱的卡车喷着黑烟冲在最前,后车厢的油布被风掀起一角,露出里头蓝漆刷的箭头……老站长非说这是“防调包的记号”。
第三道弯的急坡刚转过一半,我突然听见头顶传来金属摩擦声。“卧倒!”王铁柱的吼声混着机枪点射的脆响炸开来,一颗子弹擦着我耳朵飞过,在卡车门上凿出个焦黑的洞。
“鬼子!是九二式重机枪!”副驾驶的小刘抱着脑袋尖叫。我猛打方向盘,卡车歪歪扭扭撞上路边的岩石,后视镜里王铁柱的首车正被火舌舔舐……后车厢的炮弹殉爆了,橘红色的火光裹着弹片炸上天空,连卡车的铁皮都被掀得像张纸。
“铁柱!”我跳下车往回跑,鞋跟在碎石路上磕得生疼。王铁柱趴在驾驶座上,胸口的血把蓝布工装染成了紫黑色,右手还死死攥着方向盘。我蹲下去想给他合上眼,却见他脖颈处插着半片弹壳,边缘还沾着蓝漆……和挡泥板上的记号一个颜色。
“周队!”小刘举着块焦黑的油布跑过来,“您看!鬼子的子弹专打蓝漆的位置!”油布上三个弹孔排成直线,每个孔周围都留着蓝漆的残迹。
山风卷着硝烟灌进领口,我突然想起老站长递任务单时发抖的手。三个月七次伏击,头回有鬼子能精准打穿伪装。蓝漆记号是昨夜才刷的,除了我和铁柱,就剩老站长...
“收队!”我扯下脖子上的毛巾,盖住王铁柱的脸,“把卡车残骸推下山,今晚宿在废弃驿站……都给我睁大点眼!”
卡车的轰鸣声在山谷里撞出回音,我摸了摸怀里的任务单,纸角已经被冷汗浸得发皱。蓝漆、伏击、精准到厘米的弹着点...这趟浑水,怕是比怒江的漩涡还深。
断墙后藏着的血色日程
卡车碾过驿站前半腐的木栅门时,我听见车底传来枯枝断裂的脆响。这破驿站少说荒废了十年,青瓦顶塌了半边,墙皮像老树皮似的往下掉,墙角还堆着半爿发黑的马槽……倒像是专门给我们这种丧家犬躲雨的。
“小刘、二壮,去东边山梁放哨。”我扯下脖子上的脏毛巾擦脸,汗水混着硝烟在毛巾上洇出个灰黄的圆,“阿旺,你跟我进屋看看有没有漏风的窟窿。”
傈僳族向导蹲在门槛上,刀尖在墙皮上轻轻一挑。“周队,这墙有问题。”他话音未落,一大块墙皮“啪嗒”掉在地上,露出里头贴的泛黄油纸……竟是半张地图。
我凑过去,油纸上用红笔圈了七八个日期:“3月2日”“3月9日”“3月16日”...最后一个圈里的字被撕了,只留半截“25”。“这是...”
“滇缅运输路线图。”苏慕秋不知何时站在身后,她的护士服沾着血渍,手里还攥着块从卡车上拆下来的油箱盖,“日军画的,标着72道拐每个弯道的坡度、卡车通行时间。”
我脊梁骨发凉。三个月七次伏击的日期,正好和红圈对上。“上回张大胆车队翻在龙陵,是3月2日;李麻子的车在芒市被烧,是3月9日...”
“还有铁柱的首车。”阿旺的刀背敲了敲“3月16日”那个圈,“今天。”

苏慕秋突然把油箱盖递过来:“周队长,您看这个。”金属盖内侧刻着个指甲盖大的三角,边缘还沾着机油。“我检查了三辆卡车,每辆车的油箱盖都有这个标记。”
“保山补给站的油枪。”我脱口而出。三天前我们确实在保山加过油,站长老陈还拍着胸脯说“这趟给你们灌最好的壳牌”。
阿旺突然哼了声:“老陈的儿子小海,半年前在缅甸被鬼子抓了。”他蹲下来用刀尖拨弄地图碎片,“山民说鬼子拿小海的命逼老陈,要他在加油时做记号……三角,是不是?”
![老祖宗往地上吐了口吐沫,呸,烂泥扶不上墙[笑着哭][笑着哭][笑着哭]](http://image.uczzd.cn/13957620197389541355.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