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死亡的害怕,怕的是什么?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一针见血:“其实不是怕死的时候的肉体的痛苦,死亡意味着唯一无二的自我将永远消失,万劫不复,这才是对虚无的真正的恐惧。” 生死一瞬,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触及的迷。 王德峰教授这种“彻底的虚无”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名状的,但它却始终如影随形,成为许多人的恐惧根源。 有人可能想象过自己在身体死亡的那一刻,有没有可能有一丝意识依旧存在?是否在周遭的黑暗和寂静中,还会残留一丝对生的牵挂? 对于这一问题,王教授的回答无比果断:当一个人再也不被任何人记起,那便是真正的死亡。 对于他而言,真正的“终极告别”包含三个过程:一是生物学上的死亡,那是生命体生命的终止;二是肉体的消亡,或许会因土葬或火葬而消失于物理世界;最后,也是最不可控的阶段,是被世人遗忘。 但是为何这种虚无令人感到深切的恐惧? 王德峰认为,比起“生”,中国人对“死”拥有更深层次的执念和矛盾情感,这种复杂的情感源于对亲人、家庭甚至土地的割舍之痛。这种割舍所带来的痛苦感和牵挂往往比死亡本身更为撼动人心。 牵挂是活着的证明,它让人们在死亡面前生出更多对生命的眷恋。牵挂既是生命的重量,又是人们面对死亡时的精神枷锁。王教授这样解释,“牵挂”不仅是情感的链条,更是一种文化认同,是中国人特有的生命哲学。 在中国文化中,“牵挂”这种情感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 牵挂就像看不见的绳索,一端紧紧绑着生者,另一端系着逝者。中国人普遍相信,人在世上的责任和情感并不会随着死亡而消失,而是会延续到后人,甚至与家庭、土地和族群共存。 在亲人尚在的时代,人们会通过日常的琐事、家族的纽带不断地彼此连接,而这种情感一旦形成,就难以在死后解脱。 因此,当一个人即将面临死亡时,对牵挂的思虑往往比对死亡本身的恐惧更深。离开这片故土、离开亲友,甚至离开那些熟悉的场景,中国人对“去向”充满了不确定性。 虽然牵挂让人心生对死亡的恐惧,但这种恐惧并不意味着懦弱。 中国人一方面因为牵挂而惧怕死亡,另一方面也因为这种情感而拥有赴死的勇气。如电影《长津湖》中那位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雷公。 雷公的决定不是因为他对生无眷恋,而恰恰是因为他深知自己的死可以换来队友和后代的生存空间。他的这种行为是对家人、后代的深切牵挂,是对未来的责任感。 在这种无私的选择背后,牵挂既是束缚,也是力量。 许多中国人心甘情愿为后人承担种种负担,甚至可以在死亡面前无惧而行。 无论是一个普通农民还是一位年长的长辈,他们对故土、子孙、家庭的那份牵挂是无论生死也无法割舍的。正是这种情感支撑着中国人穿越历史的变迁,使他们在生死之间找到坚韧的力量。 王德峰教授提出:“牵挂让人产生对生命的真正意义,它让人不畏死,因为有比死更值得珍惜的东西。” 而正是这些“值得珍惜的东西”,让许多普通人的生命延续了长久的影响。王德峰希望人们在思考死亡时,也学会欣赏活着的每一刻,从那些与他人相连的牵挂中找到活着的理由。 这种牵挂并不是负担,而是赋予了人生更多价值的存在感,是一种激励、责任和爱的交织。 【信息来源:海峡新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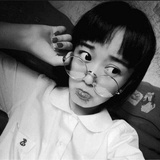
琼花似水
断灭论不休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