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华裔家庭,从小便目睹父母为了生计而奔波劳作的艰辛。他们一家生活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城市,父亲是技工,母亲则在一个小作坊里做着重复单调的针线活。家中并不富裕,但他们始终相信,读书是孩子通往未来的唯一途径。 小时候的陈宇晖聪颖好学,对数字极为敏感。在同龄人还在为乘法口诀烦恼时,他已经能够熟练地解出初中代数题。他的老师曾评价:“这个孩子的脑袋像是天生为了学习数学而生。” 他的成绩长期位列年级前列,各类竞赛奖项接踵而至,成了街坊邻居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但优秀并未带来真正的快乐。陈宇晖的成长过程伴随着孤独和不被理解。他不像别的孩子会调皮捣蛋,总是一人静静坐在角落看书或写字,因此常被嘲笑为“怪胎”。 更令他感到煎熬的是,他的梦想与身边环境格格不入。许多亲戚劝他放弃“出国梦”,说那是“洋人”的世界,华人永远融不进去。 高中毕业后,陈宇晖顶住家人的压力,毅然选择远赴美国。他拿到的是纽约市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父母卖掉了家中唯一一处旧宅,只为给他支付第一年的学费与生活费。母亲在送机时眼含热泪说:“你去追梦,但不要忘了自己是谁。” 初抵美国,他兴奋地记录每一个新鲜事物,纽约的高楼大厦、五光十色的地铁广告、校园里来自不同国家的面孔。可这份新鲜没能持续太久。 课堂上,他因为口音和害羞常常被忽略,社交圈始终无法突破肤色和文化的屏障。一次组队作业中,他的提案被当作“太亚洲化”而被否决,那一刻他感到羞愧至极。 努力想要融入的他,开始穿着打扮模仿美国同龄人,学习用俚语讲话,甚至强迫自己去参加那些不适合自己的派对。他不断想,自己还不够“美国”,所以才被拒绝。就在这种内耗与挣扎中,一个大胆的念头悄然生根——参军。 “如果我能像他们一样为美国而战,我就能真正被接纳。”陈宇晖如是对室友说。 2011年夏,他做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决定之一:参军。他对家人只字未提,怕父母担心,更怕他们反对。他在报名表上坚定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志愿奔赴阿富汗前线。 军营的生活极其严苛,但陈宇晖并未抱怨。他主动加练体能,认真学习战术,甚至在周末还自费购买专业书籍钻研军事历史。他以为,只要表现得足够优秀,就能赢得尊重。 但现实比战场更冷酷。他的排长是个身材魁梧的白人男子,一向以强硬管理闻名。在这个连队中,陈宇晖是唯一的亚裔面孔。他的存在,本就让一些士兵感到“不适”。 他们讥讽他是“黄猴子”,有人在他的床铺上撒尿,有人将他的饭盒丢进垃圾桶,只为看他默不作声地清理。 某日清晨,陈宇晖因病请假未参加晨练,排长大为恼火,命他在基地外的碎石地上匍匐前进。那片土地烈日灼烤,地表滚烫。 他一边咬牙坚持,一边感受到血液从后背缓缓渗出。周围的士兵不但未加劝阻,反而围观起哄,甚至有人拿出手机录像,仿佛这是一场滑稽的表演。 2011年10月3日,那场惨剧悄然降临。当天中午,陈宇晖因未执行“规定动作”而被排长点名体罚。他再次被命令在地面匍匐,但这一次,队友开始朝他扔石头。 没有人制止,没有人伸手拉他一把。太阳直晒,他口干舌燥,浑身是血,却依旧一言不发。几个小时后,陈宇晖在一间简陋的医疗帐篷内停止了呼吸。 验尸报告写着:因身体多处外伤导致内出血,兼有严重脱水反应。军方却在通报中草草定性为“疑似自杀”。 噩耗传至国内,陈宇晖的父母几近崩溃。两位老人匆匆赶赴美国,只求弄清儿子到底经历了什么。面对军方的封口令与诸多推诿,他们并未妥协,而是发起民事诉讼,请求公开真相。 案情披露后,引发美国华裔社群的强烈关注。数十名退役军人站出来作证,揭露军营中对少数族裔的歧视现象并非个例。案件的主审法官最终裁定施虐者罪名成立,判处18年监禁,但仅一个月后,该人竟被“暂时释放候审”,舆论一片哗然。 对于陈家而言,等待正义的过程比丧子之痛更加煎熬。他们一次次出席听证会,拿着儿子的遗照,重复讲述那个不公的故事。他们希望通过法律让施暴者受到应有的惩罚,更希望让社会正视那种深藏于制度和文化中的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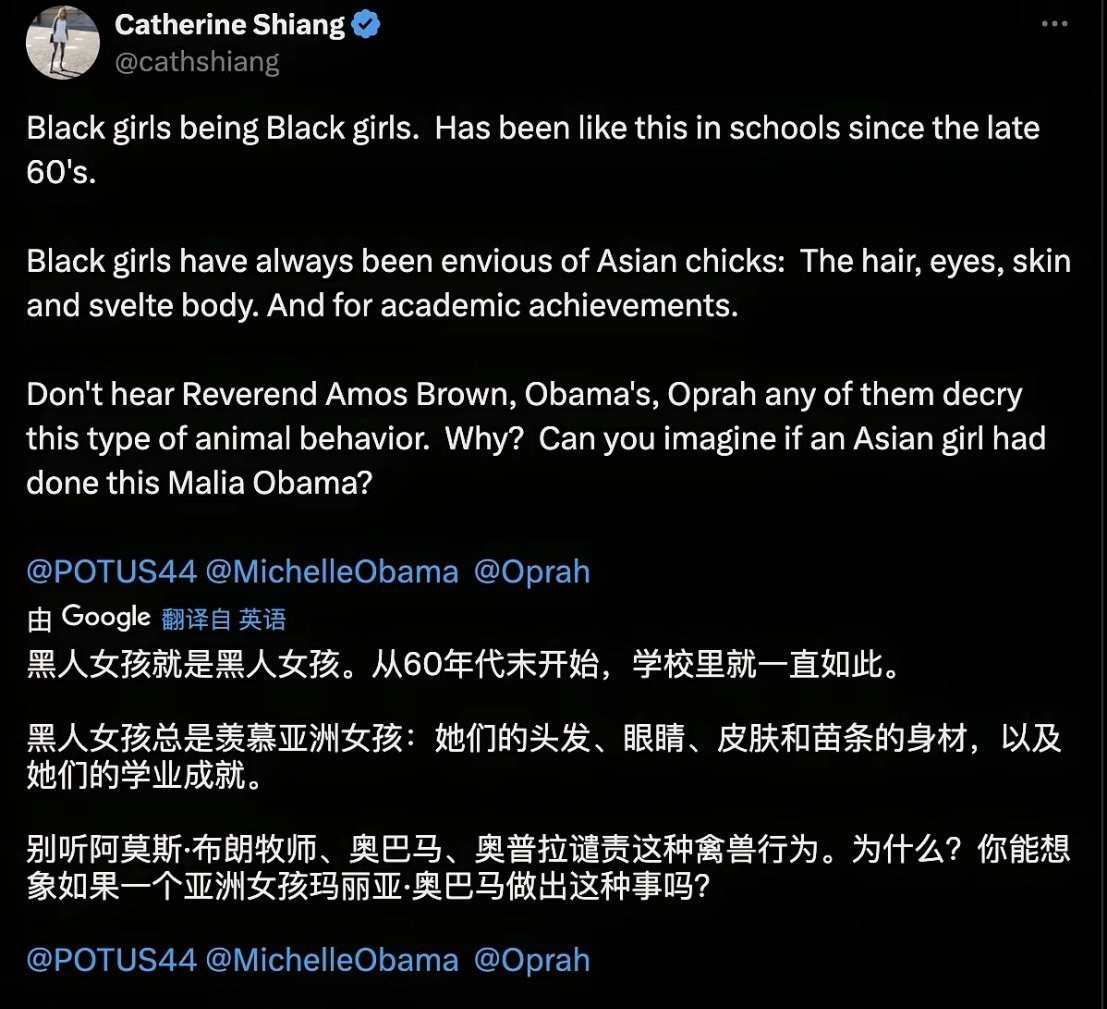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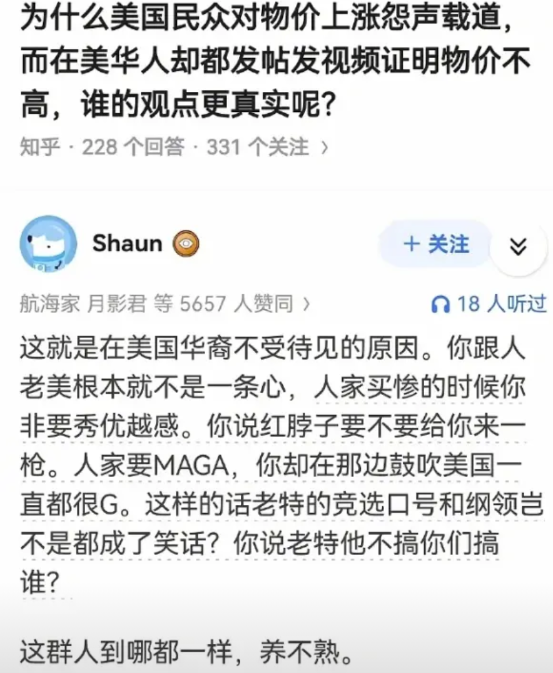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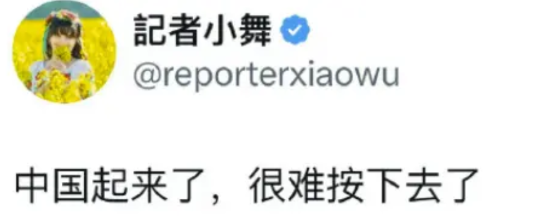



不知晦朔 无意春秋
为了他心目中的信仰而四,四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