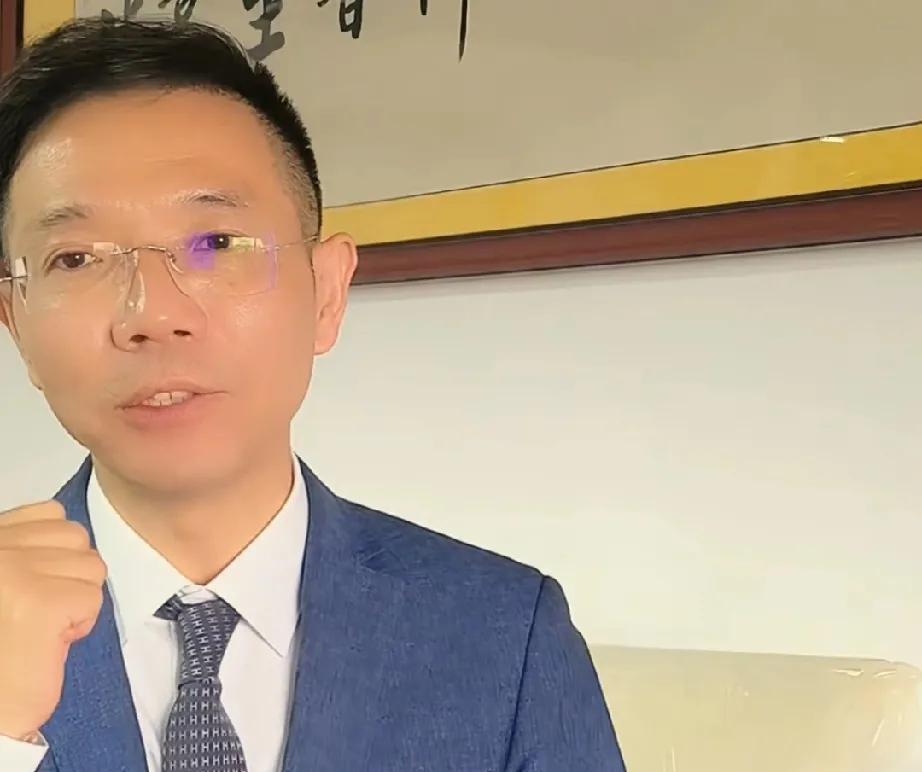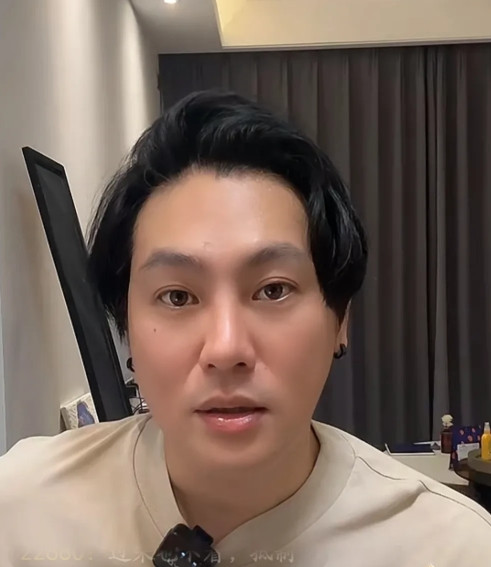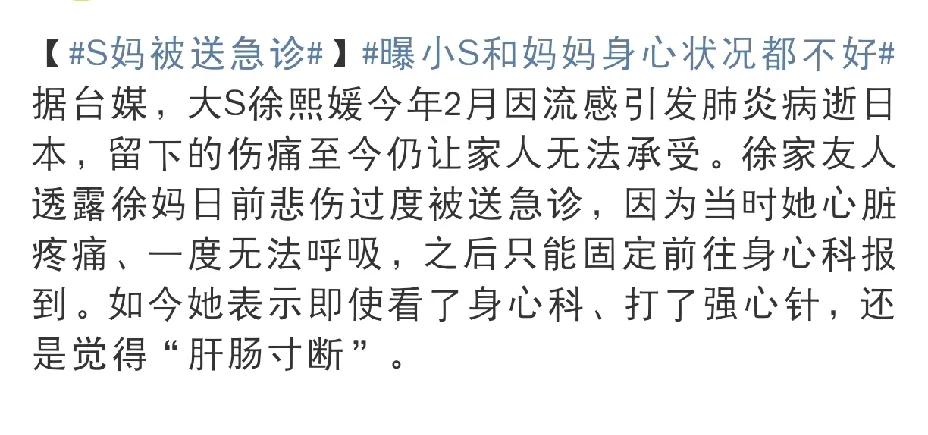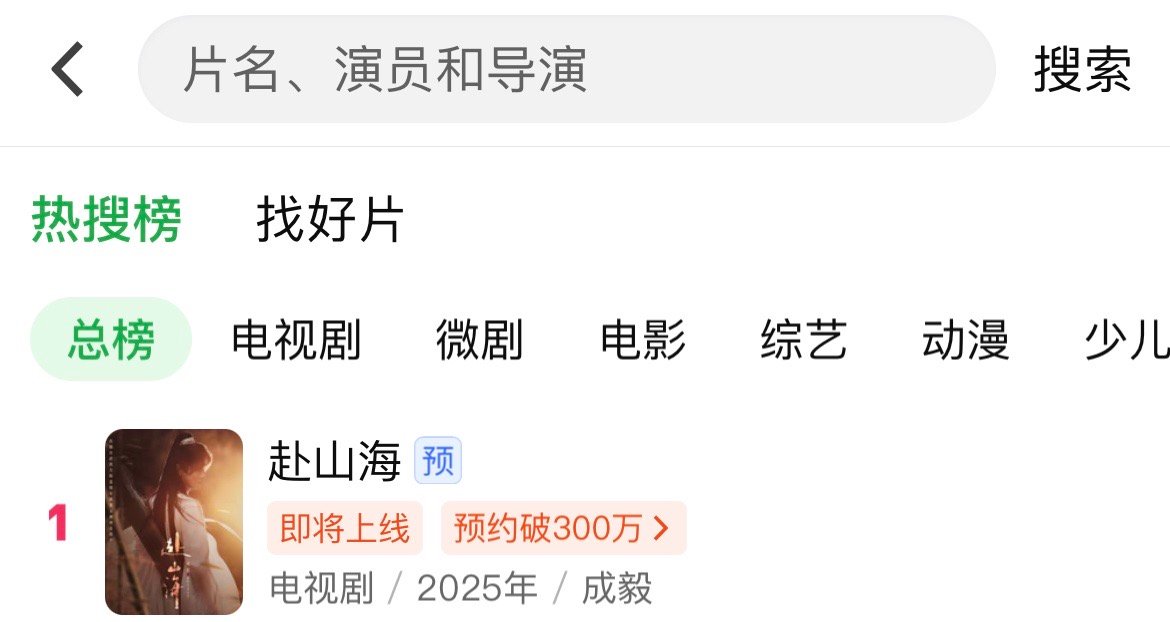1963年,上海一位机床工人奄奄一息地躺在担架上被送进医院,他看见值班医生陈中伟,紧紧抓住他的手,用微弱的声音恳求:“医生,求你帮我把这只手接上吧。”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新中国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中。城市中的机床厂、钢铁厂、造船厂昼夜运转,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贡献着不可替代的力量。 王存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默默奉献的普通工人。他是上海一家大型机床厂的技术骨干,年纪虽不大,却已凭借稳定的操作技术和敬业的态度赢得工友们的尊敬。他性格内敛,话不多,但操作起机床来一丝不苟,是车间里出了名的“老实把式”。 而陈中伟,此时正担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的一名年轻骨科医生。他出身医学世家,从医之初便立志要在骨伤治疗领域作出突破。 陈中伟思维敏捷,勤奋严谨,尽管年纪不大,却已经在手术台上历练出一身沉稳和果敢,逐渐成为医院中值得信赖的中坚力量。 二人原本毫无交集,却因一次突如其来的工伤事件而命运交织在一起。 1963年冬,王存柏所在的机床车间仍在为年终任务全力冲刺。天气寒冷,车间机器日夜不歇,操作环境极为严苛。那天,王存柏加班已经超过12小时,身心俱疲。 就在他例行检查一台自动化数控机床时,突如其来的机械故障令安全装置失灵,他右手在毫无预警中被高速转动的齿轮吞噬,整只手臂从肘部以下被硬生生撕裂。 一瞬间,鲜血喷涌,工友们惊慌失措。有人立即将电源切断,有人找来毛巾试图止血,有人抱起他的断臂,众人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将他送往最近的长征医院。 进入急诊室的那一刻,王存柏血压骤降、神志恍惚,断臂已经因失血严重而发白发冷。担架推过走廊时,他看到了穿着白大褂、正在处理前一位骨折病人的陈中伟。 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费尽最后一丝力气,攥住医生的手:“大夫,求你帮我把手接起来吧,求求你了。” 这个请求震撼了在场所有人。在那个年代,肢体再植还只是世界医学研究中的“梦想话题”,尚无任何成功范例在国内被广泛验证。而眼前这个年轻工人的眼神中,没有绝望,只有无法割舍的渴望。 陈中伟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短暂地沉默。他凝视着断裂面,判断神经、血管、骨骼的损伤程度,同时飞快思考手术可能的路径和风险。 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尝试再植,这将是一次开创性的挑战,也是对自己职业信仰的最高考验。 手术团队立即组织起来。断臂被送入特制的冰盐水中冷藏以保细胞活性,同时手术室里展开紧张而有序的准备。陈中伟亲自制定方案,选定极细的缝合丝线用于神经接驳,采取显微操作法进行血管吻合,并尝试一种改良型夹板固定方式,以稳固骨折端。 为了确保血液通畅,他们必须在两个小时内完成主要血管缝合,这几乎是人类生理极限下的挑战。凌晨时分,随着最后一根动脉缝合完成,手术室内静得连呼吸都清晰可闻。 就在所有人心跳加速等待奇迹发生时,王存柏的手指尖开始微微泛起红润——血液开始流通。 手术成功了,但这只是胜利的第一步。 术后的恢复期,是一场更为漫长的战斗。 王存柏被安置在特护病房,接受每日两次的血管通畅监测。为了防止术后排异反应,陈中伟采用了一种刚刚从国外引入的新型免疫抑制剂,并密切记录用药后的生理变化。 这种药物对于患者免疫系统是一种严峻的挑战,王存柏一度因副作用引发发热、乏力和恶心反应。 陈中伟坚持亲自巡视病房。他每次都会鼓励王存柏,不只是讲恢复的进度,更谈他曾研究过的国外战地断肢再植案例,讲述那些幸存者如何面对痛苦重建生活的故事。这些言语如同无形的力量,激励着王存柏一次次地熬过疼痛的夜晚。 为帮助王存柏恢复神经功能,医院专门组建了康复小组,包括物理治疗师、运动指导师、心理咨询师等组成的多学科团队。每天,王存柏要反复进行手指张合训练,还要借助水疗设备进行血液循环恢复练习。 起初,他连举起一只空杯子都困难重重。到了第三个月,他可以稳定地写下自己的名字。这小小的动作让整个团队都为之欢呼。 一年后,王存柏竟然回到了工厂,重新开始接触熟悉的设备。他虽然不再进行高强度操作,但却以自己的经验指导年轻工人,成为厂里的技术顾问。 陈中伟则将这次手术的全过程整理成论文,投递至国际权威骨科杂志。文章一经刊登,立即引发全球关注,被誉为“东方的再植奇迹”。 几年后,陈中伟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并被授予“共和国医学功勋”的称号。他继续深入研究再植与再生领域,推动中国显微外科技术进入世界前列。他的名字被写进医学院的教科书,也被镌刻在无数患者心中。 王存柏晚年生活平静,每次接受采访时,他总是语气平淡却眼中含泪:“是陈医生给了我第二次握住生活的机会。” 他和陈中伟保持终身友谊,逢年过节常常会携家人登门致谢。 这段医患情谊,如同那只重新鲜活的手臂一般,穿越时间与命运的刀锋,重塑了人类面对痛苦的勇气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