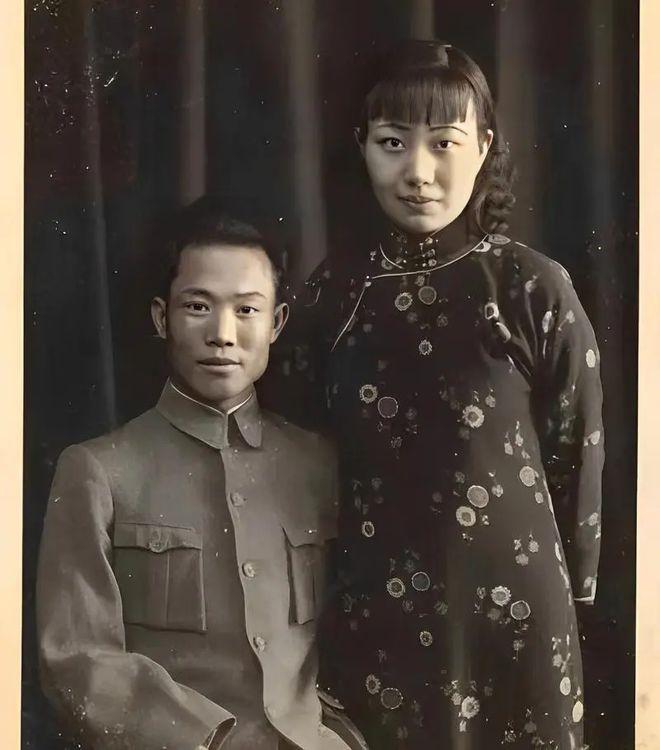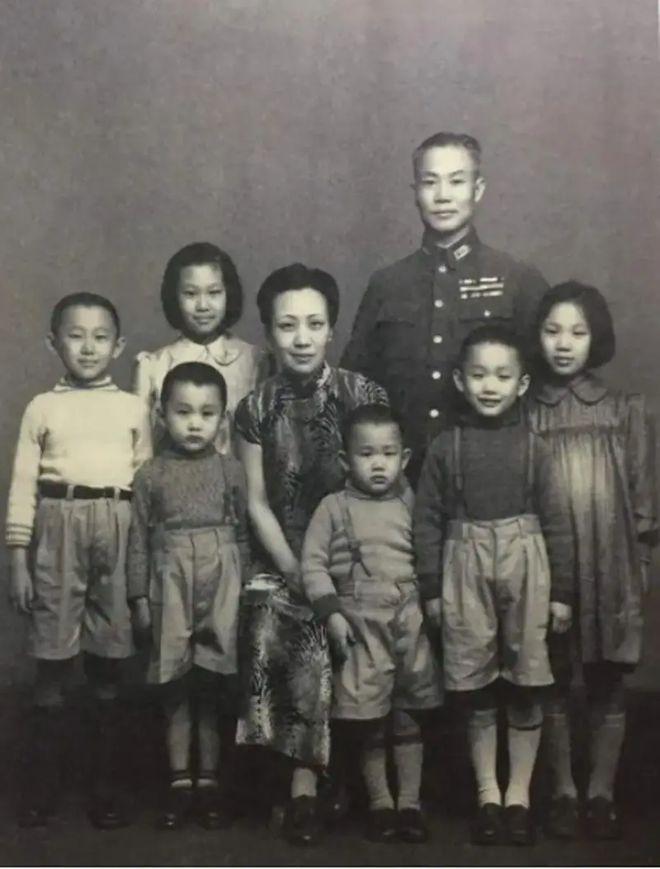1925年,黄埔名将陈诚回家奔丧,7年未见的妻子想同房,谁料被他一脚踢下。妻子一怒之下抓起剪刀,直插自己的喉咙。陈诚一惊,赶紧跑到门口大喊:快来人,舜莲寻死啦! 1925年深秋的浙江青田县,陈家大宅门前挂着的白灯笼被夜风吹得摇晃,院子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啜泣声。 刚从广州赶回的陈诚跪在父亲灵前,军装下摆沾着赶路时溅的泥点,膝盖在青砖地上跪得生疼。这是他离家七年来第一次返乡,却没想到是给父亲送终。 灵堂里飘着线香的气味,烛火映照着陈诚紧皱的眉头。他余光瞥见角落里那个裹着素色棉袄的身影——妻子吴舜莲正垂着头烧纸钱,三寸金莲缩在绣花鞋里,走起路来像踩着棉花。 这个画面让他想起七年前的新婚夜,红盖头掀开时看到的那张怯生生的脸,还有那双被裹得尖尖的小脚。当时他只觉得喉咙发紧,连夜收拾行囊逃去了省城读书。 守灵到后半夜,陈诚独自爬上吱呀作响的木楼梯。阁楼里的雕花木床还挂着成亲时的红帐子,被褥倒是新换的素色。 他刚脱下军靴,就听见木楼梯上传来细碎的脚步声。吴舜莲端着铜盆热水,小脚在楼梯上走得摇摇晃晃,盆里的水溅出来打湿了衣襟。 陈诚盯着她青布鞋尖上绣的梅花,突然想起在广州见过的那些穿高跟皮鞋的女学生,她们走路时清脆的声响和眼前这个细碎的步调形成鲜明对比。 "放着吧。"陈诚别过脸去,军装领口的铜扣硌着脖子。吴舜莲却蹲下身要给他洗脚,缠过的小手刚碰到他的裤脚,陈诚突然像被火烫了似的往后缩。 木盆翻倒在地,温水泼湿了楼板。吴舜莲跌坐在水渍里,发髻散开几缕,月光从木窗格里漏进来,照着她苍白的脸。 楼下传来母亲慌乱的询问声,陈诚烦躁地扯开领口。七年前离家时的场景突然涌上心头——吴家把女儿的嫁妆换成银元塞给他当盘缠,老丈人拍着他肩膀说"读书人要争气"。 此刻看着地上发抖的妻子,那些银元仿佛变成了烧红的炭块,烫得他坐立难安。 后半夜的冷风灌进祠堂,吴舜莲摸着黑回到自己房里。梳妆台上的剪刀映着月光,刃口闪着寒光。她想起前些日子收到的家信,堂姐在信里说省城现在时兴"文明离婚",那些读过书的男人都在闹着要自由恋爱。 剪刀刺进喉咙的瞬间,温热的血溅在梳妆镜上,惊醒了睡在隔壁的陈母。 陈诚被母亲的尖叫声惊醒时,正梦见自己在黄埔军校的操场上练兵。他冲下楼看见母亲用土方子往吴舜莲脖子上糊鸡毛,鲜血混着黑羽粘了满手。 村里的大夫提着药箱赶来时,天边已经泛起鱼肚白。陈诚站在院子里,闻着晨雾里混着的血腥味,突然想起上个月在惠州战场上闻过的硝烟味。 这场变故成了乡邻茶余饭后的谈资,陈诚躲在书房给广州的同僚写信,毛笔尖在信纸上洇开墨团:"家事纷扰,度日如年。" 信还没寄出,就收到蒋校长托人捎来的密函。信里说谭延闿的三小姐刚从法国回来,宋美龄有意做媒。陈诚盯着信纸右下角的青天白日徽记,忽然觉得喉咙发紧——三年前在南京拜会谭院长时,那个穿着洋装喝咖啡的少女,和此刻躺在厢房里生死未卜的妻子,仿佛隔着两个世界。 半个月后吴舜莲能下床了,脖子上缠着厚厚的纱布。陈诚把离婚书放在八仙桌上时,她正给婆婆熬药。 药罐子咕嘟咕嘟冒着泡,吴舜莲盯着离婚书上鲜红的手印,突然抓起毛笔在末尾添了句话:"生不同衾,死当同穴。"陈诚签完字才发现这行小楷,笔锋凌厉得像是要戳破宣纸。 1932年春天,上海法租界的教堂里飘着栀子花香。陈诚挽着谭祥的手走向神父时,突然想起老家后山那片开白花的油茶树。 吴舜莲签完离婚书那天,油茶花落满了天井。远在青田的陈老太太后来写信说,吴氏依旧住在老宅东厢房,每天清早还是会给婆婆梳头,只是脖子上永远系着条素色丝巾。 1948年的台北阳明山上,陈诚在书房整理旧物时翻出一张泛黄的信笺。那句"死当同穴"的誓言被时光磨淡了墨色,他想起上个月收到的家书里说吴舜莲病逝了。 暮色透过百叶窗照在陆军一级上将的肩章上,副官进来请示是否要把夫人的骨灰迁来台湾。陈诚摆摆手,盯着窗外飘落的榕树叶说了句"落叶归根"。 二十年后,浙江青田的陈家祖坟修葺时,乡亲们发现吴舜莲的墓孤零零立在油茶树旁。碑文上既无夫家名讳也无生卒年月,只有深深凿进去的五个字——吴氏舜莲墓。当年给陈家做过长工的老汉说,下葬那天有人看见个穿中山装的老者在不远处站了很久,但没人看清他的脸。 信息来源:《我所知道的陈诚》 文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