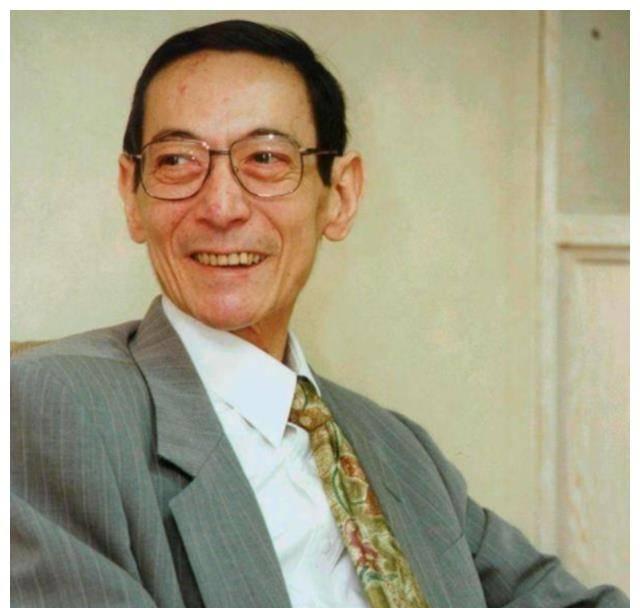1995年12月16日晚,蒋孝勇在美国旧金山的家中,先是觉得不舒服,后到洗手间吐出了一口鲜血,他的妻子方智怡连忙打电话给远在台北的“荣民总医院”院长彭芳谷,对方建议最好住院仔细检查一下。检查结果惊人大吃一惊,竟是四期食道癌。 敬请有缘人留个“关注”,可以发表一下您的精彩见解~ 1995年12月的旧金山,蒋孝勇攥着餐叉的手突然剧烈颤抖,银器砸在瓷盘上的脆响惊动了妻子方智怡,她抬头时正撞见丈夫踉跄奔向洗手间的背影。 马桶冲水声里混着压抑的咳嗽,当她冲进去时,鲜红的血迹在白瓷上绽开,像极了台北士林官邸里那株被台风刮断的老梅。 回台北,蒋孝勇抹去嘴角的血沫,这个在商海沉浮半生的男人,此刻眼底竟浮起孩童般的惶恐。 他太清楚荣民总医院彭院长的脾气,若非凶险万分,这位老战友绝不会在越洋电话里连叹七声。 专机降落松山机场时,夜雨正斜斜拍打舷窗,他望着舱外闪烁的警灯,或许忽然想起二十年前随父亲蒋经国巡视金门的夜晚——那时炮火声都比此刻心跳来得安稳。 高级病房的消毒水味呛得人发慌,蒋孝勇盯着输液管里滴落的药水,恍惚看见1988年父亲临终时的场景。 同样苍白的墙面,同样刺鼻的药味,只不过这次躺在病床上的是自己,探病的人潮从清晨涌到深夜,花篮在走廊堆成小山,每张笑脸背后都藏着打量的眼神。 他强撑着应付,直到深夜才敢让护士撤了氧气罩,在备忘录上潦草写给妻子:想回浙江。 方智怡的手覆上他冰凉的手背时,他正盯着日历上1996年的数字发呆,祖父百岁冥诞就要到了,可自己怕是等不到那天。 作为蒋家第三代里最谨小慎微的一个,他从未像两个哥哥那样追逐权力,可命运偏要把他推到风口浪尖。 就像1972年那个闷热的午后,父亲突然把他叫到七海官邸:从明天起,你去接管中央玻璃纤维公司,经国先生说,蒋家人总要有个懂经济的。 多年后,当他在党营事业董事会上力排众议叫停高价工程转包时,耳边又响起父亲的话,那些年他活得像把精巧的瑞士军刀,在商界与政坛的夹缝里闪转腾挪。 此刻躺在病床上,听着窗外木棉絮飘落的声音,他忽然厌倦了这种如履薄冰的日子。 秘密返乡的计划比想象中更周折,方智怡变卖了两套台北房产才打通关节,当他穿上旧渔民的粗布衫站在基隆码头时,海风味道竟比病房里的空调更让他踏实。 轮船鸣笛声中,他摸出贴身收藏的蒋氏族谱,泛黄纸页上"浙江奉化"四个字被磨出了毛边,这是他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也是最后一次。 溪口镇的青石板路被雨水润得发亮,他踩着祖父少年时的足迹,在蒋氏宗祠前长跪不起。 香火缭绕里,他忽然想起1994年劝儿子蒋友柏改学设计的那个雨夜,政治是吃人的漩涡。 当时他攥着儿子大学申请表,笔尖在"政治系"三个字上戳出个小洞,此刻望着宗祠里斑驳的"忠孝传家"匾额,他忽然明白,有些宿命终究逃不过。 回台后的化疗比想象中更煎熬,每当吗啡针管在护士手中泛起冷光,他就想起1984年陪宋美龄赴美治病时的场景。 那时的"第一夫人"尚能优雅地用银匙搅动咖啡,而今自己却要靠止痛剂续命,他拒绝孩子们陪床,只让方智怡每晚念《红楼梦》给他听。 当读到"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时,他忽然轻笑,这结局,倒比我们蒋家人体面,1996年深秋,蒋孝勇在荣总病房迎来了人生最后一个生日。 方智怡端来的长寿面里卧着溏心蛋,他刚要调侃这西式做派,喉头突然涌起腥甜,血沫在清水面汤里晕开时,他竟觉得这抹红比任何寿宴都喜庆。 次日凌晨,他在昏迷中反复呢喃"奉化""台北"两个地名,监护仪的警报声惊飞了窗外白鹭,蒋孝勇的葬礼在细雨中举行。 李登辉送来的花圈被放在角落,倒是新党要员们送来的挽联上"孤臣孽子"四字,当灵车驶过中正纪念堂时,她忽然明白,这个一生谨小慎微的男人,用最后的秘密返乡完成了最惊心动魄的政治宣言——在历史洪流面前,再显赫的家族也不过是片随波逐流的落叶。 主要信源:(从蒋家后代上海创业说起——中国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