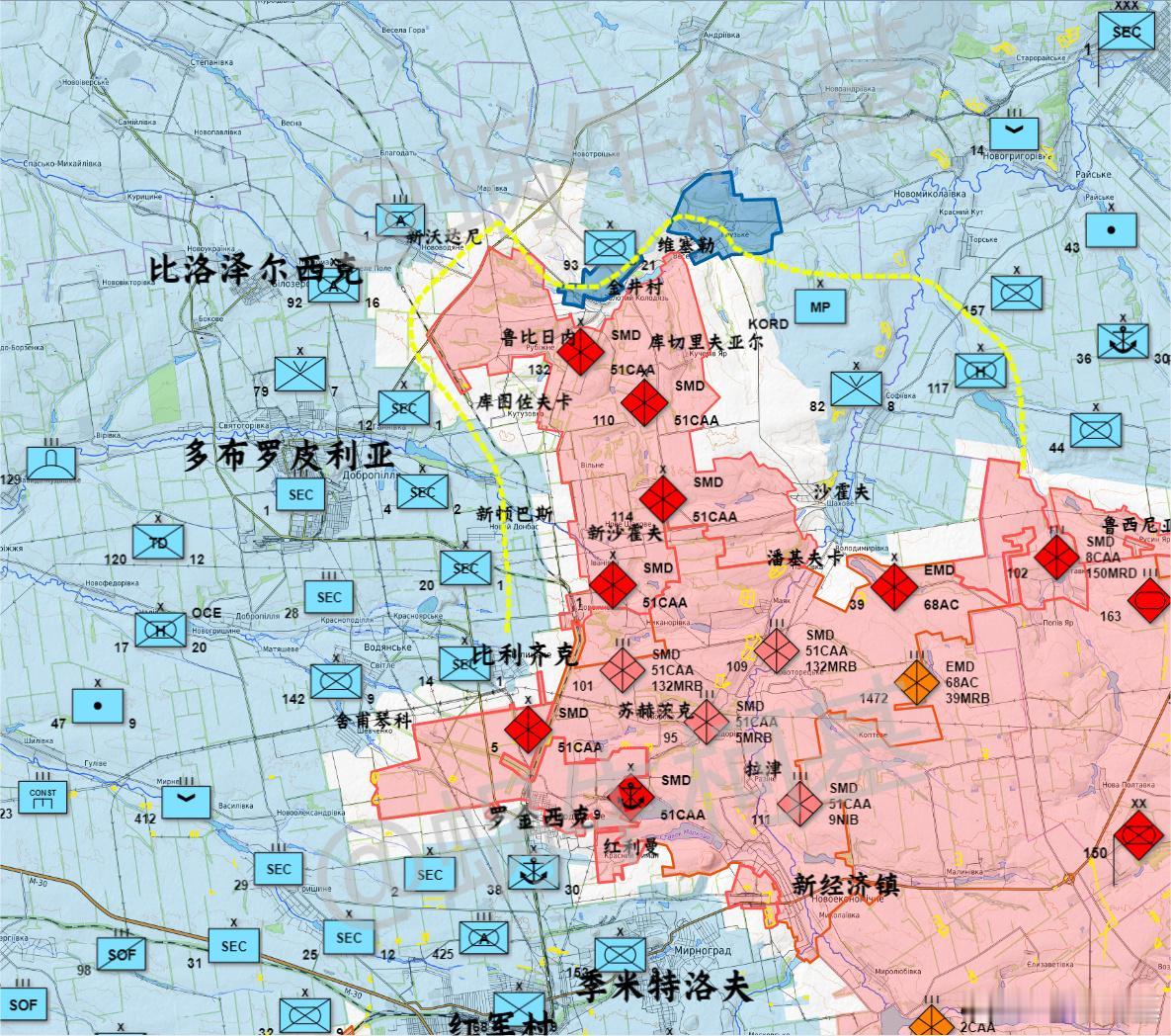1982年女飞行员刘晓莲在驾驶飞机爬升至700米时,突然被一架歼击机撞击,伴随一声巨响,机组人员全部昏迷,飞机失控急速下坠,就在这时刘晓莲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1982年9月20日上午9时32分,河北张家口上空传来沉闷巨响。
一架完成转场任务返航的安-26运输机在爬升阶段遭遇意外。
刚完成训练返航的歼-6战机如同银色闪电般迎面冲来。
两机相距不足300米时,歼击机飞行员虽竭力拉升却为时已晚,金属机翼狠狠撞上运输机头部。
撞击发生刹那,歼-6在火光中翻滚坠落。
为避开地面村落,飞行员放弃跳伞机会,操纵失控战机栽向玉米地。
携带的航弹引发冲天烈焰,年轻的生命融入北中国秋日的田野。
安-26驾驶舱内则是另一番景象。
强震让三十二岁的女机长刘晓莲撞上操纵台,腰椎错位的剧痛尚未袭来,意识便陷入黑暗。
运输机如同断线风筝向左倾斜坠落,七百米高空在三十秒内骤降至四百米。
液压油在机首破洞处喷涌,裹着强风在前窗涂抹出猩红幕布。
机舱内烟雾弥漫,仪表盘仅剩高度表顽强闪烁,七名机组人员横卧在金属舱板上生死未卜。
最先苏醒的是刘晓莲。
腰部的刺痛与失重感让她瞬间清醒,眼前景象令人窒息:操作台液压表指针疯狂跳动,断裂线路冒出刺鼻青烟。
她本能扑向操纵杆,却发现方向舵重若千斤,油门杆卡死在原位。
“抢救飞机!”撕裂般的呼喊震醒了昏迷的战友。
满脸是血的副驾驶常继堂扑到副驾位,与机长合力抗衡沉重的操纵杆。
机械师魏成景拖着伤腿爬行检查,嘶声报告关键信息:“发动机完好!尾翼正常!”
后舱传来金属摩擦的刺耳声,机械员宋春明和特设员张殿义用钢管撬动变形的油门推杆。
当推杆终于松动时,高度表已指向三百米临界线。
四百米高空相撞,三百米恢复操控。
生死一分半钟里,带血的掌印遍布驾驶舱每个操控钮。
前窗被染成暗红,领航主任胡兴元紧盯磁罗盘嘶吼方位修正,飞机在离地二百米处终于改平。
新的危机接踵而至。
机身传出橡木断裂般的呻吟,蒙皮接缝处气流尖啸。
刘晓莲立刻意识到:严重受损的机体随时可能空中解体。
最近的安全降落点正是七分钟前起飞的机场,但无线电早已损毁,前窗视野不足五米。
“盲降!”刘晓莲发出指令。
常继堂展开航图,胡兴元俯身观测地面参照物。
安-26如蒙眼巨兽掠过高压线塔,机腹擦碰树梢带起纷扬枝叶。
当熟悉的跑道轮廓在血色视窗里隐约浮现,新的麻烦出现了,六架结束训练的歼-6正列队降落。
“放下起落架!”指令声中,机械师魏成景扑向起落架手柄。
前轮顺利探出,主起落架却被变形舱壁死死咬住。
铁扳手在剧烈震动中砸出火花,手柄在第四次重击时突然松动。
几乎同时,通信长蔡新成发现致命疏漏:“电源没关!摩擦起火就完了!”
左腿骨折的他推开搀扶,指挥张殿义切断了总电源。
九时三十八分,带伤的战鹰对准草坪跑道。
就在着陆瞬间,机头突向主跑道偏转。
刘晓莲与常继堂同时站直身体,将全身重量压向右舵。
他们心里清楚:此举极可能让双腿在触地时粉碎性骨折,但此刻别无选择。
机腹与草坪接触的刹那,钢铁与大地擦出蓝紫色火花。
前轮在剧烈摩擦中折断,机鼻重重砸向地面。
滑行的安-26如受伤巨鲸犁开草皮,在距主跑道七米处轰然静止。
正在降落的歼-6编队安然掠过天空,六架战机平稳着陆。
硝烟散尽的驾驶舱里,蔡新成昏倒在电路总闸旁,他的左手仍紧握着绝缘胶布。
刘晓莲瘫在座椅上,腰椎剧痛让她无法动弹。
七名幸存者被抬出机舱时,远处的玉米地仍有黑烟升腾。
那位不知名的歼击机飞行员,永远定格在驾驶姿态中。
事后调查揭开悲剧根源:两机在相同压高度层遭遇通讯频率错位。
安-26三分钟后必然解体的结论,令在场的航空专家肃然起敬。
这份用意志书写的航空史奇迹,最终镌刻在七枚军功章上。
刘晓莲、蔡新成荣膺一等功,其余五人分获二、三等功。
二十二载光阴流转,五十五岁的刘晓莲佩戴少将军衔站在阅兵场。
当年血染的驾驶舱细节,化作空军指挥学院教材里的经典案例。
与她共享荣誉墙的还有师弟刘传健。
那位完成史诗级备降的川航机长。
两代蓝天卫士的身影在空军航空大学的校史馆交相辉映,讲述着同样的铁律:精湛技艺在左,钢铁意志在右,方能托起生命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