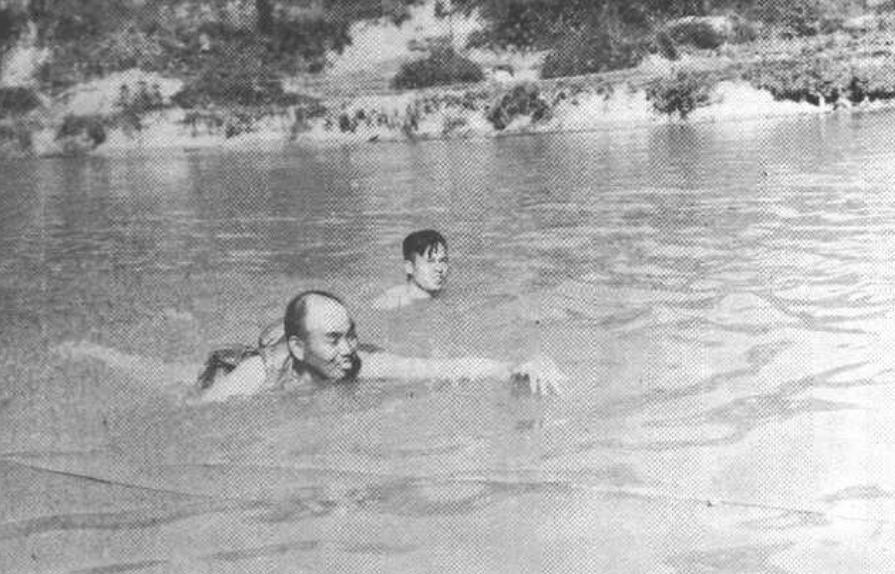许世友陪女护士顾锦萍逛南京路,顾锦萍笑言:成大首长保护小兵了 “1983年4月16日下午三点,你们几个真打算单枪匹马闯上海?”许世友把话说得像在阵前点兵,却夹着关切。对面,二十七岁的顾锦萍愣了愣,随即点头。谁也没料到,这一句略带军味的调侃,竟成了那趟南京路散步的序曲。 距离许世友告别军职已两年,他的住所依旧设在南京军区后勤大院。顾锦萍是院里抽调来的保健护士,毕业于南京卫生学校,英语说得溜,针头下去利落,只是提起要给“许老虎”打针时却心里直发怵。传闻中的许司令脾气犟、嗓门大、喝起茅台惊人,可一接触,顾锦萍发现老人家爱开玩笑,批评是批评,但落点从不伤人。 她原本并不愿意来。那年春节刚过,周德礼参谋长把她叫到办公室:“小顾,许司令年纪大了,得有人贴身照顾。别听外面瞎说,他对年轻人可护着呢。”顾锦萍不好拒绝,咬牙去了。有意思的是,第一次量血压就出了差错,袖带没绑紧,仪器数值蹿得老高。许世友瞅她脸红,哈哈大笑:“别怕,我又不是在前线抓俘虏。” 关系就这样破了冰。之后的日子,顾锦萍常被叫到书房。那间房里摆着一张大字典、一套繁体本《红楼梦》,封皮已卷角。十多年前,毛主席在中南海同几位大将聊天时提到:“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红学也得补一课。”主席还点了名字——“许司令,五遍,少一遍都不行!”任务摆在那儿,许世友礼貌答“是”,心里却犯了难。识字不多,行军打仗靠地图、靠目测,要啃四大名著里的繁体字,真够呛。最开始他想“打缩写”:让秘书把全书压成一万字梗概。后来发现还是似懂非懂,只好央求顾锦萍当“讲书先生”。顾锦萍花一个礼拜连夜通读,随后每天午后挤出半小时,把贾府的起落、宝黛的悲欢娓娓道来。许世友握着茶杯,时而皱眉,时而点头,听到“抄家”情节还拍桌子:“哼,纸糊的富贵,一捅就破!”听得多了,他竟能背出几段脂批。 酒,是老人家的另一爱好。逢客必开茅台,逢喜亦开茅台。他常说那句顺口溜:“冷酒伤肺,热酒伤肝,没酒伤心。”顾锦萍酒量几乎为零,可架不住老人热情,有时也抿一小口。那一小口,把距离陆续拉近。于是当她提到想到“十里洋场”开开眼界时,许世友才冒出那句“我给你当保镖”,并立刻安排车辆和随行司机,外加一支小口径手枪塞进风衣口袋——老习惯,出门要备不时之需。 次日晨七点半,车子从中山门驶出,沿沪宁公路一路向东。车上放着收音机,里头正播《在希望的田野上》。顾锦萍透过车窗看麦田,心里却盘算南京路该从哪头逛起。将近中午,车进上海。那时的南京路,霓虹灯白天也亮着,商贩吆喝夹着几句上海闲话,外地游客三三两两,街面倒比想象中平和。许世友走在最外侧,目光不停扫,步子虽慢却稳。顾锦萍轻声对同伴打趣:“看吧,大首长变成咱们的警卫员了。”老人家听见,朗声回道:“我打了一辈子仗,还护不了你们仨小姑娘?” 他们从西藏中路逛到河南中路,买了几块奶油小方糕,又在百货公司二楼看了最新的二波收录机。顾锦萍想掏钱,被许世友按住手:“别和我客气,这点小东西,算我孝敬下一代。”午饭在黄河路的小馆子解决,几碟冷菜、一壶黄酒,老人家依然把枪压在腿边。服务员偷偷打量,认出这位白眉老人似曾相识,却又不敢上前。 傍晚返程,车刚开出市区,许世友忽然发话:“小顾,你们这些读书人,不光要会看书,还得学几手防身。改天我教你们擒拿。”顾锦萍半开玩笑:“我怕挨摔。”他摆手:“不摔人,先教你们躲。”遗憾的是,这堂课终究没开成。那年秋末,许世友病情加重,转入总医院特护病房。顾锦萍忙前忙后,深夜量体温、清理输液,依然给他读《红楼梦》做消遣。老人醒着时还惦记:“第五遍我得凑够。” 1985年10月22日凌晨,许世友走了。遗体告别那天,军号低沉,雨落梧桐。顾锦萍站在人群最后,兜里塞着一本袖珍版《红楼梦》,书脊被汗水浸得发软。出殡队伍缓缓移向雨花台公墓,她忽然想到南京路的那句玩笑,鼻子一酸:那位愿意给小兵当保镖的大首长,再也不会拉着她过马路了。 几个月后,她调到上海一家机械进出口公司做翻译。每逢下午下班,她都会去南京路口转转,看熙攘人潮,看路对面挂着闪闪霓虹的“茅台”灯牌。有时候,她还能听见老人家大嗓门的回响:“艺不压身,记住!”这句话,顾锦萍记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