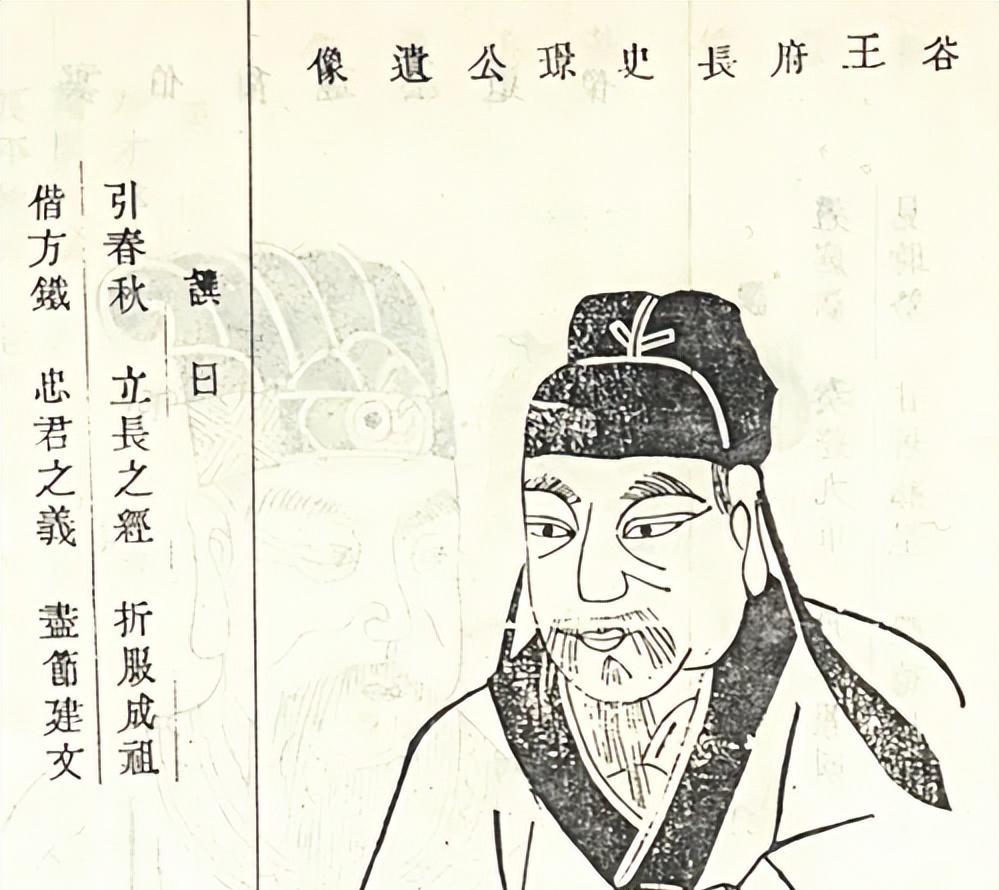1390年,打了胜仗归来的唐胜宗,等来的不是赏赐,而是赐死诏书。唐胜宗满心不甘,问朱元璋:“我究竟犯了什么弥天大罪,竟要落得如此下场? 金銮殿的金砖被日光照得发白,唐胜宗身上的铠甲还沾着漠北的尘土,甲片碰撞的脆响在殿里荡开,显得格外突兀。他盯着龙椅上那个满脸皱纹的男人,眼眶红得像燃着的炭火——这是和他一起从濠州的泥地里滚出来的朱重八啊,当年在郭子兴帐下,两人分过一个麦饼,在死人堆里背过彼此,怎么如今成了说杀就杀的君王? 朱元璋没抬头,手指捻着诏书的边角,黄绸子被捏出几道褶。案几上堆着厚厚的奏折,最上面那本的封皮,印着“胡党余孽案”五个字,墨迹黑得发沉。“你随朕三十年,”他的声音像殿角的铜钟,闷闷的带着回响,“从滁州到应天,你斩过陈友谅的先锋,守过洪都的城门,这些朕都记着。” 唐胜宗的手攥紧了腰间的佩剑,剑柄上的缠绳磨得发亮,那是他打平江时,朱元璋亲手帮他缠的。“记着为何还要杀我?”他往前挪了半步,铠甲摩擦的声响惊得殿外的侍卫握紧了刀,“臣的儿子还在云南戍边,臣的妻小在应天府里守着祖宅,他们做错了什么?” 朱元璋终于抬了眼,眼角的皱纹里藏着说不清的复杂。他忽然笑了,笑声里带着点沙哑:“去年冬天,你儿子托人带回一筐云南的荔枝,你分了半筐给徐达家,这事不假吧?” 唐胜宗一愣。徐达是开国第一功臣,半年前刚病逝,死前还被人举报过与胡惟庸有书信往来。他当时只想着徐达的夫人爱吃荔枝,压根没往别处想。“那是同僚情谊……” “情谊?”朱元璋把诏书往案上一拍,黄绸子“啪”地展开,“胡惟庸当年在府里摆酒,你不也去了?他给你递的那杯酒,你敢说没沾唇?” 唐胜宗的后背“腾”地冒出汗来。胡惟庸是五年前被处死的丞相,牵连了上万人,这案子像根毒藤,这几年总在功臣们的脖子上绕几圈。他确实去过胡府的酒局,可那是奉旨赴宴,席间连句私话都没说过。“陛下,那是公务……” “朕老了。”朱元璋打断他,声音突然软了些,指节敲着自己的膝盖,“夜里总梦见当年打天下的弟兄,有的断了胳膊,有的没了脑袋,都睁着眼看朕。他们说,朱重八,你当了皇帝,就忘了咱们当年说的‘有福同享’了?” 唐胜宗的喉咙哽住了。他想起刚投军时,朱元璋站在高坡上喊:“等天下太平了,咱们回家盖大房子,给爹娘坟前立石碑!”那时的朱重八,眼里的光比天上的星星还亮。如今这宫里的琉璃瓦再亮,也照不进那点光了。 “臣明白了。”唐胜宗慢慢跪下,铠甲砸在金砖上,发出沉重的闷响。他没再辩解,只是磕了三个头,额头抵着冰凉的地面,“臣死不足惜,只求陛下善待臣的家人,让他们回濠州种地,别再沾朝堂的边。” 朱元璋看着他佝偻的背影,案几上的茶杯晃了晃,茶水溅出几滴,落在“胡党余孽案”的奏折上,晕开一小片湿痕。“你儿子在云南立过战功,朕会让他继续戍边,只是改个名字,换个防区。”他顿了顿,又说,“你家祖宅,朕让人照着原样修,留着给后人看看。” 唐胜宗没再说话,起身时腰杆挺得笔直,像当年守洪都城时那样。侍卫上前卸他的佩剑,他抬手拦住,自己解下剑鞘,把剑放在金砖上。剑身在日光下闪了闪,映出他鬓角的白发——才四十出头的人,这几年竟添了这么多白头发。 走出金銮殿时,风从午门吹进来,带着城外麦田的气息。唐胜宗回头望了一眼那片金黄的琉璃瓦,忽然想起二十年前,朱元璋在南京城楼上拍着他的肩膀说:“胜宗啊,这天下是咱们一刀一枪拼出来的,将来得守好,别让百姓再遭罪。” 那天下午,应天府的百姓看见一辆没有帷幔的囚车从皇宫里出来,车里的人穿着旧铠甲,坐得笔直,路过秦淮河时,还朝着河西岸的方向笑了笑——那里住着他的妻小。 后来有人说,唐胜宗死的那天,朱元璋在御书房里坐了一夜,案上摆着当年两人分过的那个麦饼的碎屑,是从旧战袍的夹层里找出来的。 许多年后,唐胜宗的儿子在云南边境打退了来犯的敌人,受赏时没要金银,只求皇帝赐一块“守土安邦”的匾额,挂在濠州老家的祖宅里。那块匾后来存了三百年,直到太平军路过时,还被当地百姓藏在柴房里,没人舍得烧坏它。 (据《明史·唐胜宗传》及《明实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