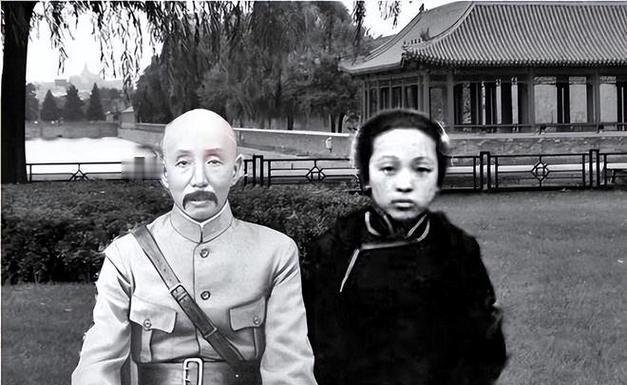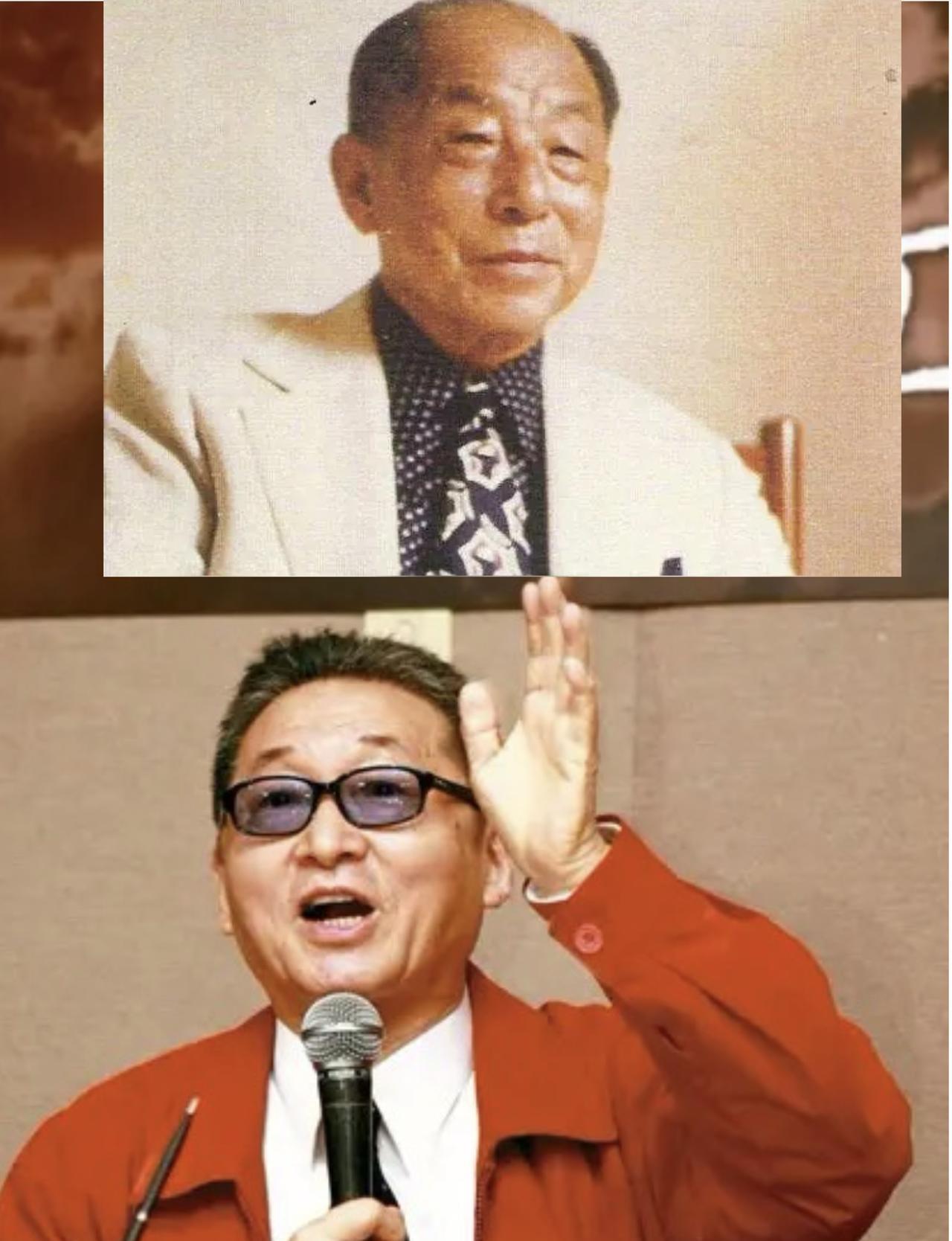1912年,张作霖用马鞭狠抽张学良,夫人们忙跪倒欲求情,张作霖一瞪:“谁敢求情,我崩了他!”然而,张首芳抄着火铲就冲过去怒吼:“张作霖,你再敢打我弟,我砸烂你头!”张作霖见状,悻悻走了。 好家伙,这声“张作霖”喊出来,别说那些姨太太,连张作霖自己都懵了。在那个年代,别说女儿,就是他手下最横的将领,谁敢直呼其名?可张首芳就敢。她小脸涨得通红,眼睛里喷着火,死死地护在张学良身前。 对峙了几秒,让人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威风八面、杀伐决断的张大帅,竟然悻悻地把鞭子往地上一扔,嘟囔了句啥,黑着脸,背着手,走了。 全院子的人都看傻了。 为啥?张作霖怕一个丫头片子手里的火铲?当然不是。他怕的,是这个女儿身上,她亲娘赵春桂的影子。 张首芳这股子冲天的怨气和泼天的胆子,全是她那个早逝的母亲给的。赵春桂是张作霖的原配,陪着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保安团团长,一路摸爬滚打。可以说,张作霖的江山,有赵春桂一半的功劳。可男人嘛,尤其是有本事的男人,总容易在功成名就后,忘了那个陪自己啃窝窝头的女人。 随着张作霖的官越做越大,帅府里的姨太太也越来越多。赵春桂是个烈性子,眼里揉不得沙子。她看不惯那些虚与委蛇,更受不了丈夫的冷落。一气之下,她带着张首芳姐弟三个回了新民老家,算是跟奉天的荣华富贵彻底决裂。 可这一走,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回到老家后,赵春桂积郁成疾,很快就病倒了。弥留之际,她心心念念的,还是那个让她又爱又恨的男人,盼着他能回来看自己最后一眼。 张首芳那时候还小,但她亲眼看着母亲的眼神,从期盼,到失望,最后变成一片死寂。张作霖不是没得到消息,他派了医生,派了卢夫人,甚至连张学良都偷跑回奉天去求他了,可他,就是没回来。他总觉得,这是老婆在跟他赌气,耍性子。 直到赵春桂咽下最后一口气,张作霖才匆匆赶回,办了一场风光大葬。在灵堂上,张首芳看着那个男人脸上一闪而过的哀伤,心里没有半点感动。母亲用命下的赌注,最终只换来了一场迟到的葬礼。这份怨,这份恨,就这么种在了张首芳心里。 从那天起,她就在心里发誓,这辈子,一定要护好母亲留下的这两个弟弟。所以,当她看到张作霖挥舞马鞭抽打张学良时,她看到的不是父亲教训儿子,而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在伤害一个没了娘的可怜孩子。 她抄起的不是火铲,是积压了多年的委屈和愤怒。她吼出的那句“张作霖”,喊的是一个女儿对父亲的失望,和一个姐姐对弟弟最本能的保护。 张作霖退让了,因为在那一刻,他从女儿的眼睛里,看到了亡妻的质问,看到了自己的亏欠。这份愧疚,比任何武器都更有杀伤力。 张首芳的“硬”,贯穿了她的一生。后来,张作霖为了政治联姻,把她嫁给了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的儿子鲍英麟。这位鲍公子,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吃喝嫖赌,五毒俱全,还动不动就搞家暴。张首芳是什么人?她能跟自己爹叫板,还能怕一个二世祖? 据说,鲍英麟在外头受了气回家撒野,张首芳二话不说,抄起桌上的古董花瓶就砸了过去,指着他的鼻子骂:“你再敢动我一下试试?我爹的脾气你不知道,我弟弟的脾气你更不知道!”从那以后,鲍英麟再也不敢对她动手。这段婚姻虽然不幸,但张首芳从未向谁低过头。 皇姑屯一声巨响,张作霖走了。张学良接掌东北,成了少帅。张首芳的日子,也跟着弟弟的命运起起落落。她最担心的,始终是这个从小护到大的弟弟。 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被囚禁。消息传来,张首芳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她一个妇道人家,无权无势,丈夫也靠不住,只能四处托人打探消息。每次听说有东北军元老能去探望张学良,她都拿出自己本就不多的积蓄,买些东北的土特产和滋补品,千叮咛万嘱咐地让人捎过去。 十几年音讯隔绝,直到1947年,她才收到张学良辗转寄来的一封亲笔信。信里说他一切都好,只是眼睛花了,看书费劲。张首芳捧着信,几十年的委屈和思念瞬间决堤,哭得泣不成声。 没过多久,第二封信来了,张学良在信里说,想要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的大字版《明史》。 这对当时的张首芳来说,是个天大的难题。她早就被丈夫赶出家门,生活拮据,靠变卖首饰度日。为了给弟弟买这套书,她跑遍了当时的北平,最后,她一咬牙,卖掉了母亲留给她唯一的遗物——那支金簪。 在那个战火纷飞、音讯不通的年代,为了给远在台湾孤岛的弟弟寄去一套书,一个落魄的姐姐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那套《明史》承载的,哪里是文字,分明是一个姐姐倾其所有的爱和牵挂。 可惜,造化弄人。这套书寄出去后,海峡两岸彻底隔绝。直到1954年张首芳在北京病逝,她也没能再见到自己的“小六子”一面。她走的时候,穷困潦倒,身边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所有认识她的人都知道,这个女人,一辈子都活得有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