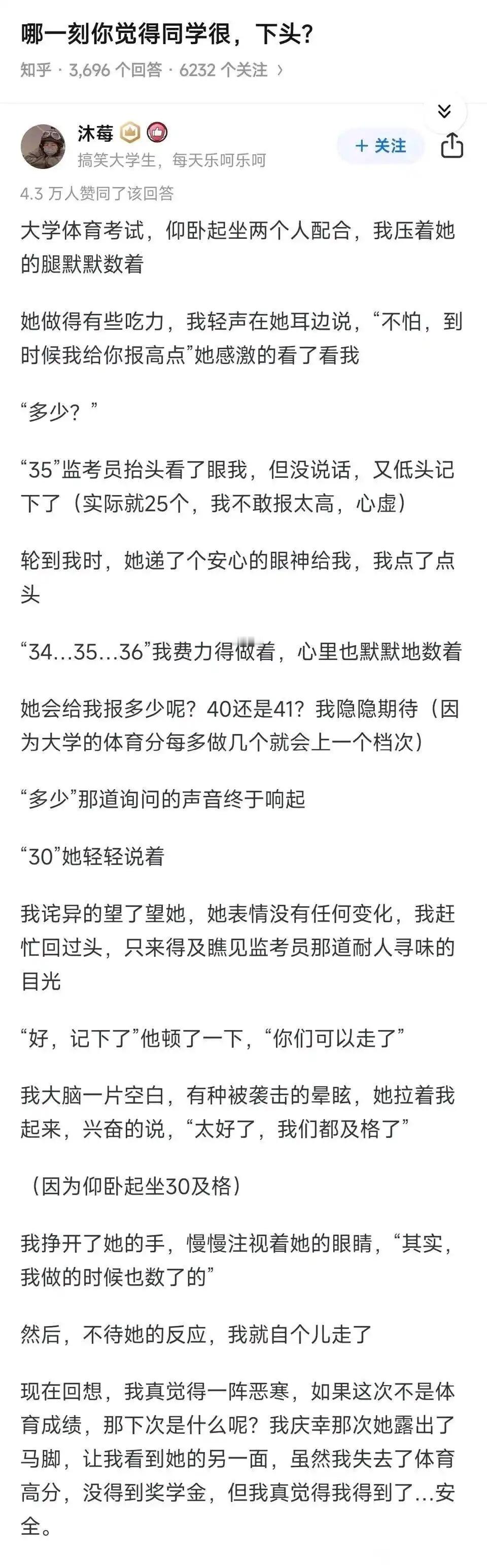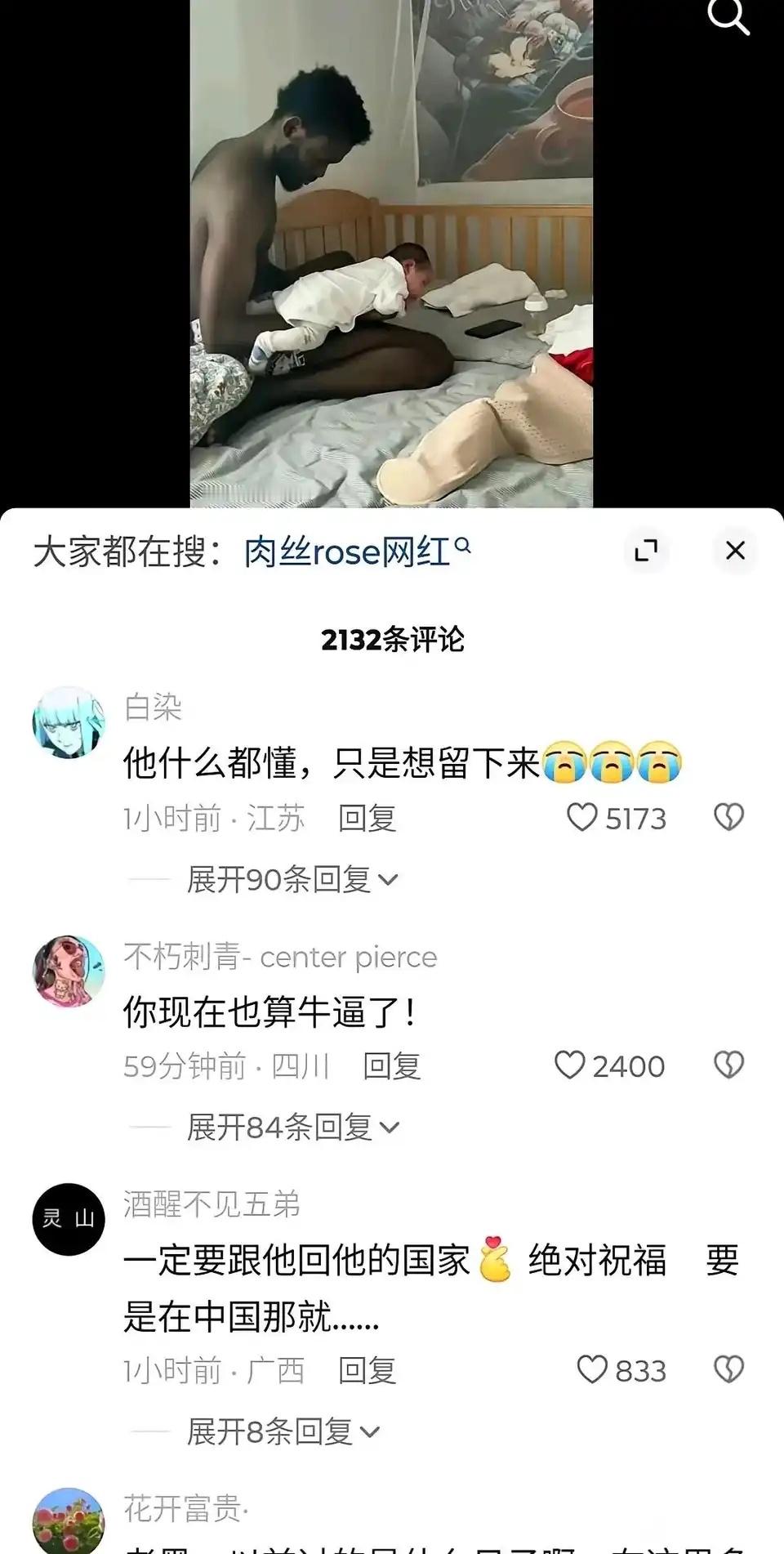1986年,邓稼先弥留之际问妻子:“30年后,还有人记得我吗?”许鹿希瞬间红了眼睛,她把丈夫紧紧地抱在怀里,就像哄着婴儿一样,哄着他入睡。
邓稼先临终前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他吃力地问妻子许鹿希:“三十年后,还有人记得我吗?”许鹿希强忍泪水把他搂进怀里,像哄孩子似的轻轻拍着他的背。
这是1986年夏天,距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已经过去二十二年,可邓稼先的名字直到上个月才出现在报纸上。
二十八年前的那个夏天,三十四岁的邓稼先回家时心事重重。
他告诉三十岁的妻子自己要调动工作,去哪儿不能说,做什么不能说,连通信地址都不能给。
他最后只留下两句话:“往后这个家就靠你了,我的命要交给新工作了。
这事要是干成了,这辈子就值,死了也值。”许鹿希抹着眼泪回答:“我支持你!” 谁也没想到,这句承诺要用二十八年的独自坚守来兑现。
邓稼先像人间蒸发似的扎进了戈壁滩。许鹿希在北京当医生养家,白天在医院教解剖课,晚上回家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
有邻居嚼舌根说老邓怕是死在外头了,她只当没听见。1964年10月,收音机里传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许鹿希激动得手直抖。
后来她父亲在饭桌上嘀咕:“不知道是哪位神仙搞出来的?”许鹿希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这些年不见人影,是在沙漠里放了个“大炮仗”。
核武器研究是刀尖上跳舞。1979年有颗核弹头出了岔子,没按计划炸响。
邓稼先拦住同事,自己冲进现场找哑弹。戈壁滩的风刮得人脸生疼,他抱着摔碎的弹片仔细查验,防护服早被放射性物质浸透了。这事就像埋了颗坏种子,六年后他查出直肠癌晚期。
1985年国庆节,邓稼先偷溜出医院去看天安门。望着广场上飘扬的国旗,他喘着气对警卫员说:“等建国一百年,国家强盛了,你八十四岁再来这儿,替我看一眼……”警卫员别过脸不敢接话。
回到病房,许鹿希日夜守在床边,眼见着丈夫被癌痛折磨得蜷成虾米。
她自己是北大医学院教授,救过无数病人,此刻却救不了相濡以沫的丈夫。
1986年6月,报纸突然登出《两弹元勋邓稼先》的长篇报道。
全国人民这才知道,那个让原子弹炸响、让氢弹腾空的科学家,二十八年隐姓埋名,连老婆孩子都不知他在哪。病床上的邓稼先捏着报纸,手指划过铅印的名字,久久说不出话。
一个月后的7月29日,他躺在妻子怀里留下最后三句话:“别开追悼会,别惊动大伙儿;把我埋母亲旁边;咱们不能被落得太远……”
许鹿希把丈夫的骨灰送回安徽老家,转头就扎进北师大宿舍楼的老房子。
这间六十平米的小屋墙皮都裂了缝,卫生间瓷砖缝里还留着邓稼先用蓝粉笔写的计算公式。
有人劝她搬去条件好的院士楼,她指着墙说:“老邓的魂儿在这儿呢。”
客厅最显眼处挂着丈夫的黑白照,旁边摆着1999年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她每天用绒布擦相框,这个习惯从1986年保持至今。
2015年,儿子邓志平帮母亲整理出《邓稼先传》。老太太戴着老花镜,把丈夫留下的糖纸千纸鹤、旧水壶、半截蜡烛都贴上标签,连木门上的裂缝都原样留着。
她把两百多封家书扫描成电子版捐给国家图书馆。
1958年的信纸上还能看清那句:“希希,戈壁滩的星星亮得像你的眼睛。”
2023年8月,九十五岁的许鹿希坐在轮椅上过生日。
屋里没摆寿宴,只有侄子许进带来的两幅字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年轻人凑钱画的《松鹤延年》,九三学社书法家写了七遍的邓稼先语录:“做科研要像骆驼,忍得住渴,驮得起山。”
老太太让侄子推她到丈夫铜像前,把字画挨个举起来合影。拍完照她忽然想起什么,扯着嗓子喊:“小进,记得微信发我照片啊!”
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如今常来陪老人聊天。有回博士生说起量子纠缠实验,老太太脱口而出最新论文的期刊号,惊得小伙子直咂嘴。
另一个学生悄悄在茶几放了束白菊——他查资料发现邓老当年总采野菊放在妻子实验室。许鹿希颤巍巍从铁盒里取出1968年的糖纸鹤,彩色的“北京”二字依然鲜亮。
当年邓稼先躺在长安街边问“三十年后还有人记得吗”,如今公交车驶过花园路,常有家长指着北师大宿舍楼对孩子说:“瞧见没?‘两弹元勋’家的灯还亮着呢。”
这盏灯从青丝照到白头,照了三十八年,照得比原子弹的光芒更久长。
老话说灯芯不灭魂不散,许鹿希守着这盏灯,就像守着一句无声的回答:骆驼死了留驼峰,人走了留名声,你们两口子的故事,早刻进共和国的年轮里了。
信息来源: 1.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官网《我院为邓稼先夫人许鹿希先生祝寿》、北京卫视《晚间新闻》报道《邓稼先故居里的生日》 2.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微信公众号《许鹿希先生九五华诞记》、人民政协网《“两弹元勋”邓稼先夫人许鹿希平静度过95周岁生日》 3. 新华网《邓稼先夫人许鹿希:稼先去世前一个月,中央军委终于同意对他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