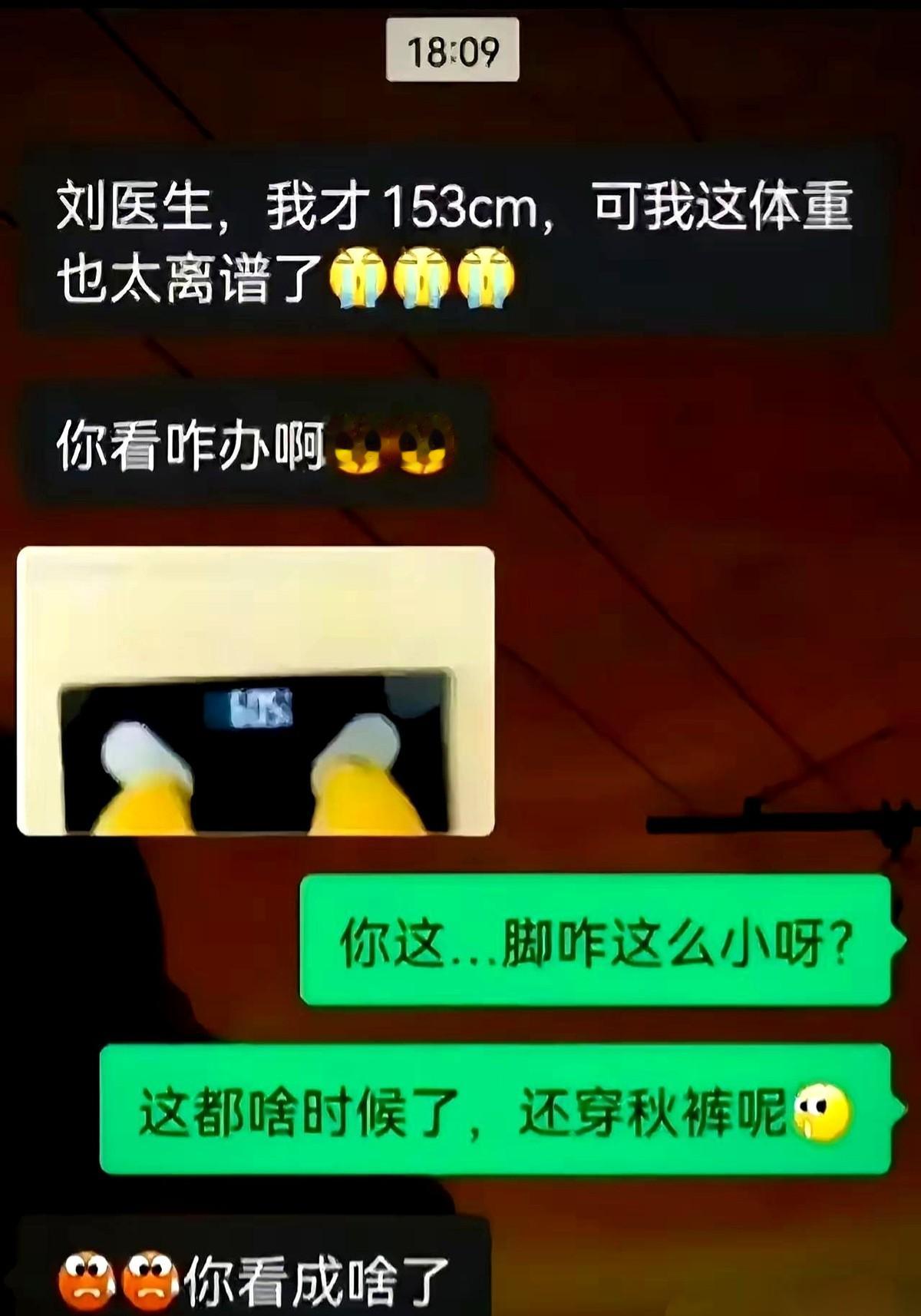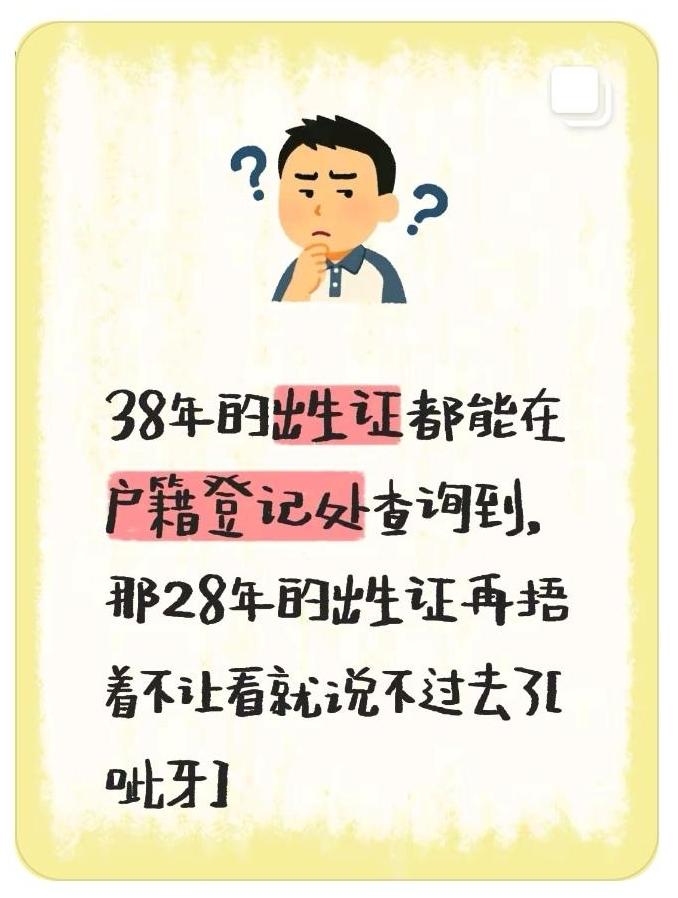[太阳]1910年,上海青帮老大给一个实习医生敬酒,问道:“方大夫一个月挣多少?”方大夫说:“不多,2元2角。”青帮老大眯起了眼睛:“来我这,拜我为师,我资助你开个诊所。”方大夫沉默片刻,随即摇了摇头。 那时候的方慎斋,白天跟着西医院老医生查病房,听诊器在掌心焐得温热;晚上蹲在药房配药,药臼里的当归碎末簌簌落在油纸袋上,指尖总沾着股挥之不去的苦味。 他租的亭子间在法租界边缘,木楼梯踩上去吱呀作响,每月房租要耗去他一半薪水。江苏常熟老家的父亲是私塾先生,寄来的信里总夹着几张写满批注的《论语》,末尾那句“医乃仁术,无分贵贱”被红笔圈了三遍。 青帮老大的邀约不是第一次递到年轻人面前。码头扛大包的老王头说,上个月帮里“先生”刚给一个牙医开了铺面,如今连巡捕房的人看牙都得预约——可那牙医上个月给帮派火并的人治伤,手一抖差点锯错了骨头。 方慎斋见过更糟的。隔壁医院的李医生去年入了帮,如今诊室里总坐着几个“兄弟”喝茶,穷苦病人来了就得等,有钱人来了直接插队。有回一个黄包车夫咳血来晚了,李医生正忙着给帮会“四爷”看“富贵病”,愣是让人家在门口咳到天亮。 他摇着头拒绝时,没说“我怕惹麻烦”,只在心里算了笔账:入帮能换门面,换不来病人咳嗽时眼里的信任;能免房租,免不了深夜被电话叫去给“道上兄弟”处理刀伤时的手抖。 后来他和同学在闸北区开诊所,门脸是刷白的木板,挂着块掉漆的“慎斋诊所”木牌。第一天开张,一个拉黄包车的师傅捂着胳膊进来,伤口还在渗血,兜里只摸出三个铜板。方慎斋没问他跟谁打架,先拿盐水冲洗,再撒上消炎粉——那包粉是他用半个月饭钱换来的进口货。 有人说他傻,放着青帮的“大树”不靠,偏要在泥里刨食。可拉车师傅回去后,三天功夫,附近纱厂的女工、码头的力夫、街角的摊贩,排着队来敲门。他们不识字,说不清自己得的啥病,只知道这个方大夫不问他们是不是“道上的”,也不管钱够不够。 那年冬天流感厉害,诊所挤得转不开身。方慎斋三天没合眼,累得靠在墙上打盹,手里还攥着没写完的药方。有个病好的老太太送来一碗热粥,说:“方先生,你跟那些‘帮里医生’不一样——你眼里有我们。” 他忽然想起1910年那个晚上,青帮老大酒杯里的酒晃出涟漪,像极了后来诊所门前病人踩出的泥坑。只是酒杯里的涟漪会散,泥坑里的脚印,却在时光里越踩越深。 乱世里的安稳,有人靠码头的枪杆子,有人靠租界的铁皮房,方慎斋靠的是药箱里那把用了十年的听诊器——它听过富商的心跳,也听过乞丐的喘息,却从没因为谁的身份变过调子。 如今再看那个摇头的瞬间,哪是什么“错过捷径”?那是一个医生给自己划下的边界:医病,不医江湖;救人,不救利益。这条线划得浅,却比帮会的帮规更有分量。 多年后,慎斋诊所的木牌换成了水泥的,可老病人还记得,当年那个拒绝青帮的年轻人,是怎么在两元二角的月薪里,给“良心”标了价——那价格,比任何帮会的“资助”都贵,也都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