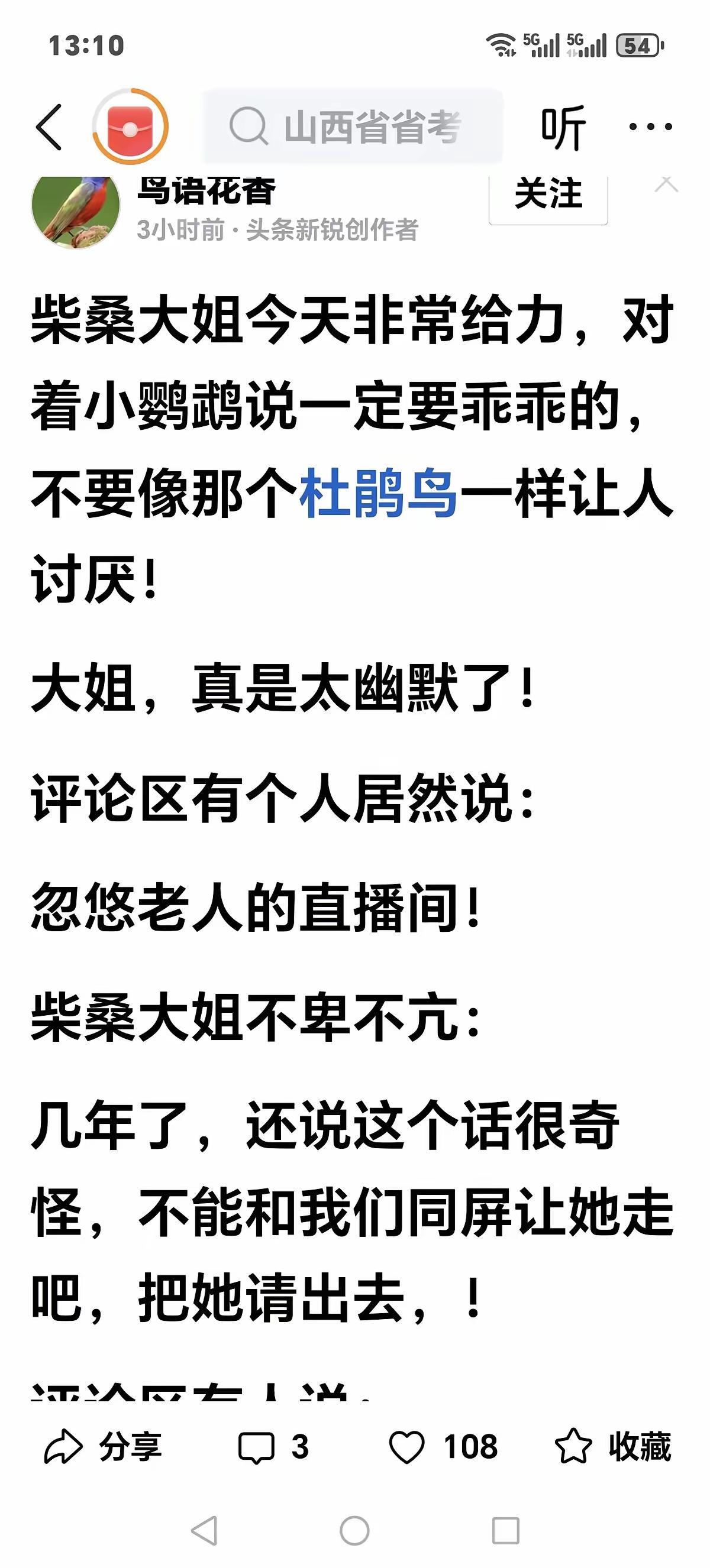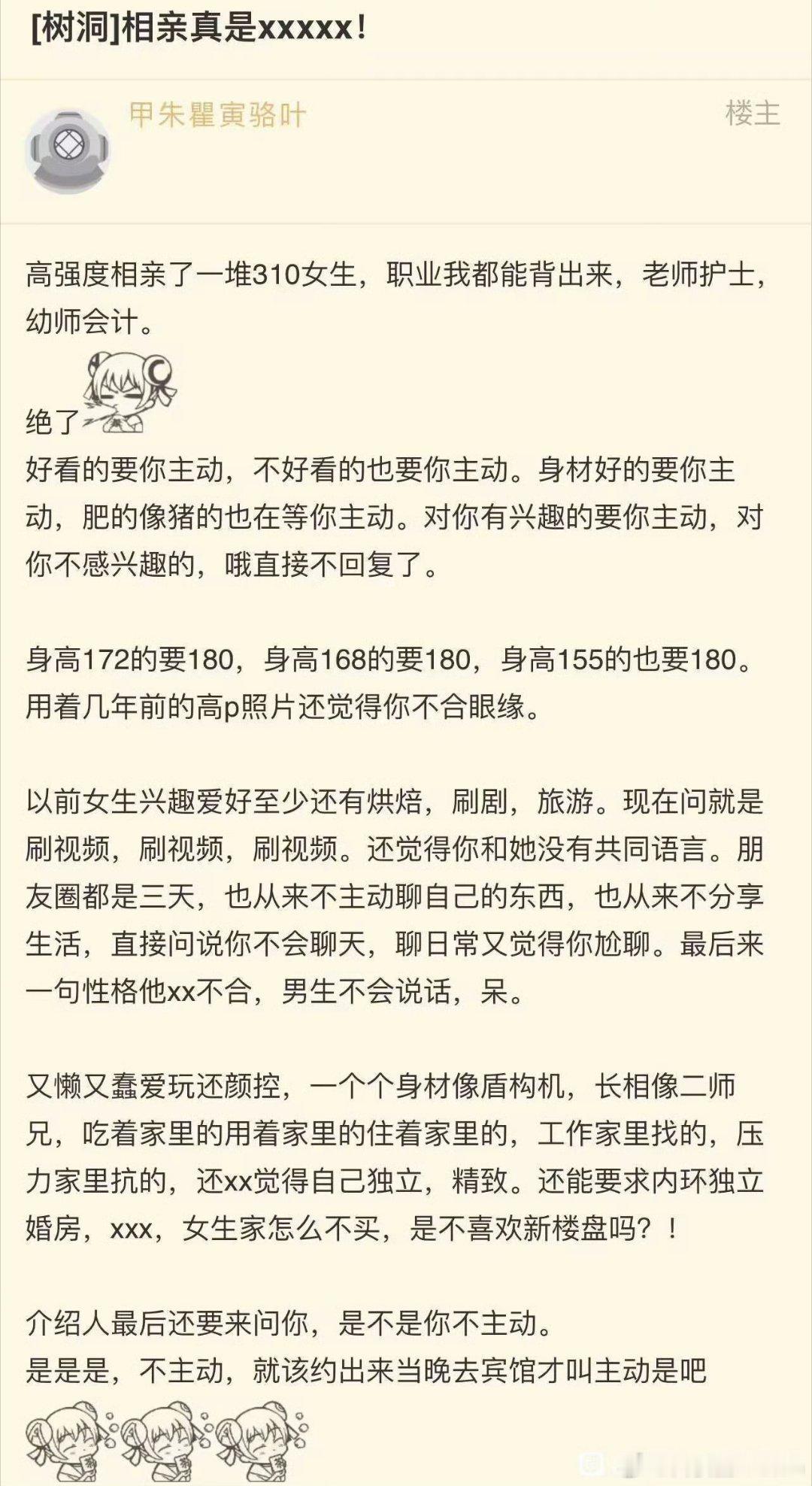男孩今年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向后妈和父亲要钱,后妈说家里没有钱,父亲做不了主不当家,男孩子哭啼着找叔叔借钱,于是叔叔把爱车卖了给他交了学费。 男孩攥着钱,喉咙里像堵了块石头。叔叔的手在旧T恤上擦了擦,转身去给他倒水,客厅那台旧风扇吱呀呀地转着,吹乱了桌上几张零钱。他没多留,怕自己忍不住哭出来。去北京的前一晚,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把录取通知书看了又看。 火车站的月台上,叔叔用力拍拍他的背,“到了就打电话,别舍不得吃饭。”火车开动,他看见叔叔一直站在那儿,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他靠窗坐着,手里紧紧攥着那个装钱的旧信封。 大学的日子,是教室、图书馆和打工地点的三点一线。他给学校送过桶装水,帮快递站分过件,晚上回到宿舍,常常累得倒头就睡。每次给叔叔打电话,他都只说好事,比如老师夸他认真,或者北京秋天有多好看。电话那头,叔叔总是笑呵呵的,但他有次隐约听见邻居问叔叔怎么好久不开车了,叔叔含糊地说车坏了,骑电动车方便。 大三那年暑假,他提前两天回家,想给叔叔个惊喜。快到叔叔家那条巷子时,却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正费力地蹬着三轮车,车上堆着高高的纸板箱。七月的太阳毒辣,那人背心湿透,紧贴在佝偻的背上。是叔叔。他愣在原地,看着叔叔蹬到废品站,抹着汗跟人讨价还价,接过几张皱巴巴的零钱。 他悄悄退到拐角,眼泪唰地流了下来。他才知道,叔叔卖车后,一直在偷偷收废品帮他攒生活费。那天晚上,他像没事人一样去叔叔家吃饭,叔叔炒了几个菜,一直往他碗里夹肉。风扇还在吱呀呀地转,他看着叔叔晒得黝黑的胳膊,低头猛扒了几口饭,没让叔叔看见他红了的眼圈。 回北京前,他把打工攒下的所有钱,偷偷塞进了叔叔的枕头底下。火车再次启动时,他望着窗外,心里比来时多了份沉甸甸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