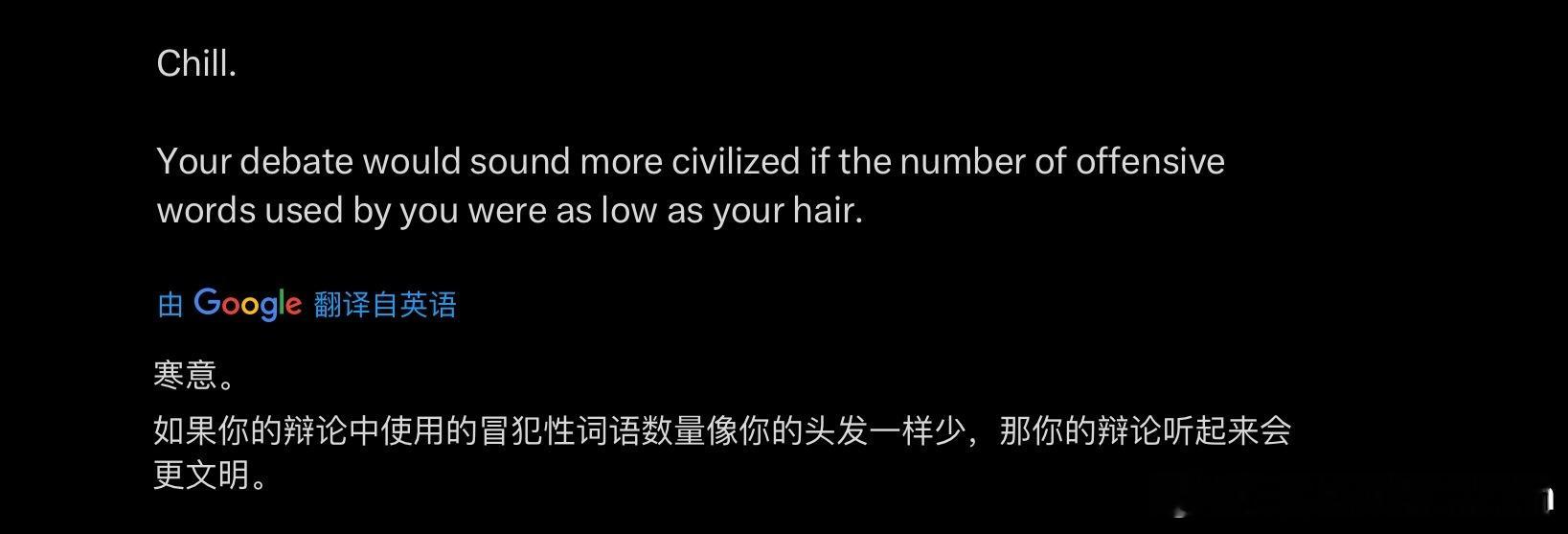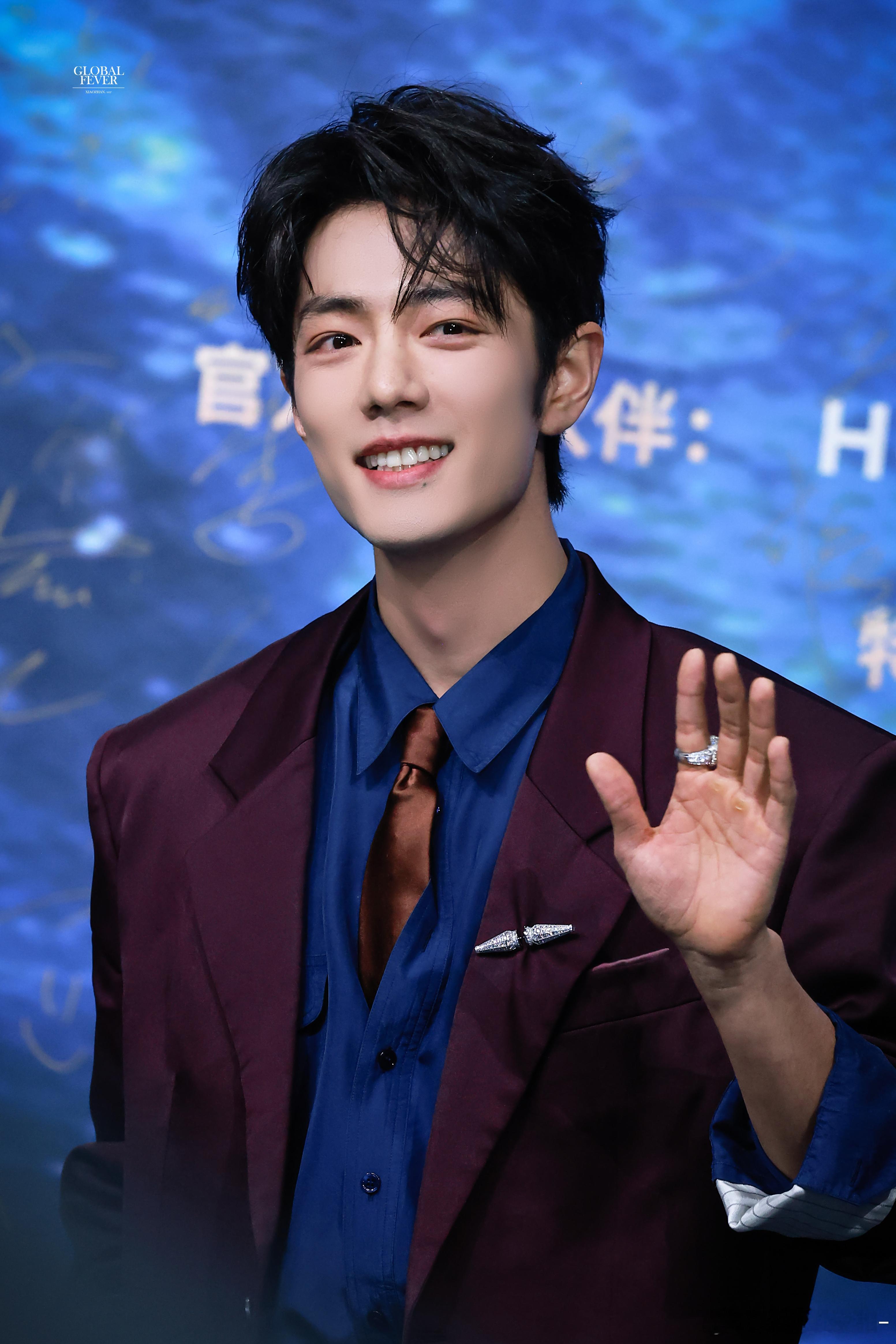噪音致人伤残,为何长期无人问津? “隔壁天天加工木材,我耳朵里像有几万只蝉在叫,耳朵都快聋了!”河南的赵先生最近愁得夜不能寐。他家与木材加工厂仅一墙之隔,相距不过五六米。每天从清晨六点到深夜十一点,电锯、刨床、压板机轮番轰鸣,声音尖锐刺耳,仿佛无数金属碎片在颅骨内摩擦。他试过敲门沟通、找村委调解、拨打12345热线,甚至蹲守在厂门口等老板出来理论,可对方总是敷衍一句“就这几天”,然后照常开工。日子一天天过去,噪音非但没停,反而随着订单增多愈发猖獗。 去年7月,赵先生开始出现持续性耳鸣,起初以为是熬夜上火,没太在意。可耳鸣不仅没消退,反而越来越响,夜里躺在床上,耳边如同塞进了一台永不停歇的电钻。他终于扛不住去了县医院耳鼻喉科。检查结果令人心惊:双耳高频听力严重下降,确诊为噪音性耳聋,听力损失已达中重度水平。医生神情凝重地告诉他:“你必须立刻离开这个高噪音环境!再拖下去,神经性损伤不可逆,到时候就算装助听器也救不回来了。”赵先生攥着诊断书站在医院走廊,手心全是汗——他上有老下有小,房子是祖传的,搬走?谈何容易。 更令人窒息的是,这场灾难并非突发。早在三年前,邻居们就陆续反映过噪音问题。有人投诉后,环保部门曾来检测过一次,结果显示昼间噪音高达82分贝,夜间76分贝,远超《声环境质量标准》中居民区昼间55分贝、夜间45分贝的限值。可检测报告交上去后,便如石沉大海。厂方象征性加装了一层薄铁皮隔音罩,第二天又因“影响散热”拆掉。监管缺位、执法疲软,让违法者有恃无恐,而受害者只能在日复一日的轰鸣中默默失聪。 时间来到2025年12月,赵先生的听力已恶化至无法正常接听电话,连孙子喊“爷爷”都听不清。他不得不申请残疾人证,经专业机构评定,被认定为听力四级残疾。这意味着他的日常生活将永久受限——不能驾驶、难以就业、社交障碍……一个原本健康的中年人,就这样被无形的声波推入残障群体。记者随他前往镇政府反映情况时,镇长坐在办公桌后,语气轻松地说:“年前就不生产了,剩下的板材年后做完就停。”仿佛这只是一桩寻常的邻里纠纷,而非一起因行政不作为导致的身体伤害事件。乡政府工作人员补充道:“大机器都挪走了,现在只剩一个小电锯。”记者实地走访,在赵先生家院中开启那台所谓“小电锯”,声音确实微弱,几乎被风声掩盖。可问题是——当伤害已经造成,迟到的整改还有多少意义? 这不禁让人追问: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究竟体现在哪里?当一位公民因长期暴露于超标噪音而致残,基层治理体系为何反应如此迟钝?是技术手段不足?显然不是。噪声监测设备早已普及,执法依据清晰明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禁止夜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木材加工虽非建筑施工,但其性质类似,且发生在居民区,理应受到更严格约束。那么是人力不足?也不成立。乡镇设有环保办、综治办、网格员,多头管理本应形成合力,却在实际中演变为“谁都管、谁都不管”的推诿困局。 更值得警惕的是背后可能存在的利益链条。这家木材厂规模不大,却能在居民区长期违规作业,是否与地方保护主义有关?是否因能提供少量就业岗位或缴纳税费而被默许“带病运行”?记者试图查询该厂环评手续,当地环保所却以“涉密”为由拒绝提供。这种信息不透明,恰恰为权力寻租留下空间。当公共健康让位于局部经济利益,当个体苦难被系统性忽视,所谓的“发展”便成了对弱势者的二次伤害。 赵先生的遭遇绝非孤例。据中国疾控中心2024年发布的《职业性噪声聋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全国每年新增噪声性听力损伤病例超12万例,其中近三成发生在非职业场景,如城中村作坊、临街商铺、社区施工等。这些“灰色噪音源”游离于监管边缘,受害者维权成本高、举证难、周期长,往往在沉默中承受不可逆损伤。法律虽赋予公民安宁权,但在执行层面,噪声污染仍被视为“软性违法”,处罚力度远低于水、气污染,违法成本低得惊人——多数案例仅处以几百元罚款,与企业收益相比微不足道。 要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就必须把人的健康置于发展的核心位置。这需要制度层面的刚性约束:建立噪声污染快速响应机制,对居民区周边高噪作业实行“零容忍”;推行“首接负责制”,杜绝部门推诿;公开企业环评及处罚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司法救济渠道也需畅通,允许受害者集体诉讼,提高惩罚性赔偿标准,让违法者付出真实代价。噪音污染 致人伤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