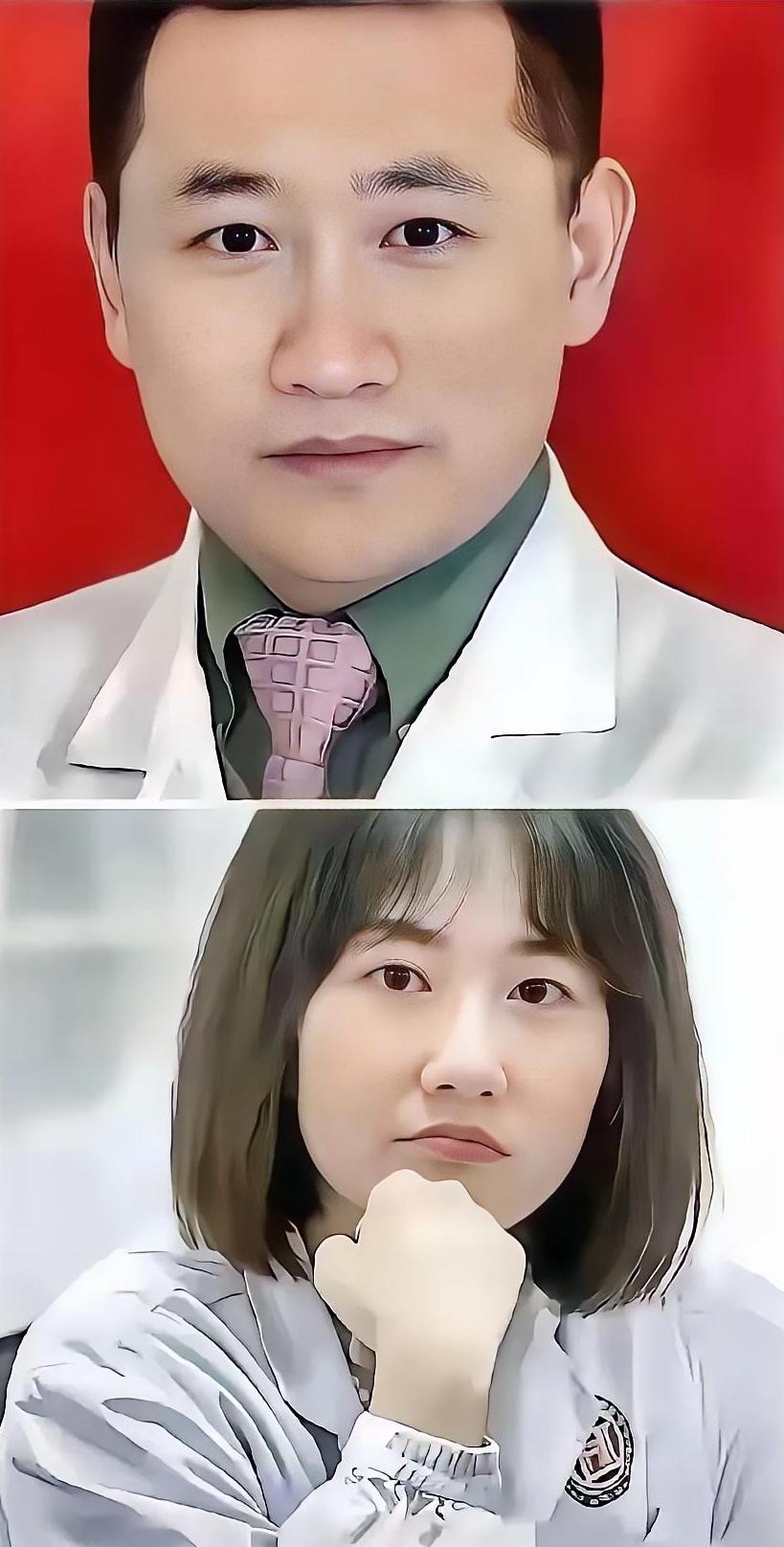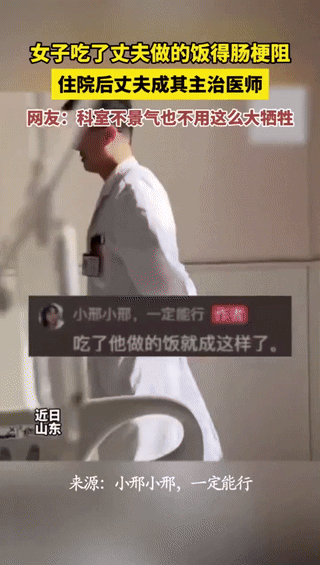2021年,32岁的宋元志是一名血透室医生,工作地点在江苏某三甲医院。平日性格温和严谨,喜欢在下班后独自待在办公室翻阅病例,或到图书馆查阅最新的透析指南。他每天六点四十五起床,站在医院宿舍阳台上,手握一杯黑咖啡,边看着楼下缓缓驶入的第一班救护车,边快速浏览医学公众号的最新推文。午间常因临时会诊错过饭点,宋元志便会带上一盒便当回值班室,在查阅病例的间隙匆匆吃几口。夜班后,他常常靠在电脑前记录透析观察日记,直到凌晨一点才合上病历本。这样高强度、高专注度的生活,他早已习以为常。

住院部后花园里常有野猫出没,其中一只灰黑相间的大猫,眼神凶悍,尾巴少了半截,被医院员工称为“大灰”。这只猫常在垃圾桶旁翻找残羹冷炙,有时蹲在急诊入口的台阶上,冷眼打量着来来往往的病人。宋元志初见它时,正好夜班结束,猫正蹲在手术楼外的长椅下打盹。他随手掰了一块面包扔过去,大灰略微警觉地扫了他一眼,随后懒洋洋地走过去叼走,尾巴微颤。从那天起,他常在值夜班时给它带点吃的,彼此之间也算结下了某种无声的默契。
而意外就发生在2021年7月16日下午,宋元志刚结束一场三小时的血透穿刺培训,拖着一身疲惫准备前往地库取车。医院后门的维修通道一向昏暗狭窄,两侧堆着废旧病床和铁皮柜,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铁锈味。他正低头查看手机里的班表,忽然,耳边传来一阵刺耳的塑料摩擦声。宋元志抬头那一瞬,只见大灰从旧床垫后猛地蹿出,灰黑的身影在光影中一晃,像一道阴影划破沉寂。
大灰的前爪紧紧压住一个污渍斑斑的外卖袋,嘴里叼着腐烂的食物残渣,眼神凶狠发亮,喉咙里传出嘶哑低吼,背脊高高拱起,毛发炸立,像随时要扑向猎物的野兽。宋元志本能地往后退一步,可还未来得及转身,大灰已如离弦之箭般弹起,发出一声尖厉的“咝——”!

下一秒,利爪和尖牙几乎同时袭来——那种速度快得几乎看不清轨迹。宋元志只感觉一阵剧痛猛地炸开,右小腿瞬间传来撕裂般的灼热感。他低头的一刹那,只见裤腿被撕出一道长口,猫的前爪死死钩进肉里,甚至还能清晰地看到两颗獠牙刺入皮肤的瞬间,血珠在毛发之间疯狂迸出。猫的身子死死缠在他的小腿上,前后爪轮番抓挠,像在撕碎一块猎物。
“啊——!”剧痛让宋元志惊叫出声,膝盖一软,整个人几乎跪倒在地。他下意识用手去拨,却被猫尾一扫,掌背也被带出几道血痕。鞋底一滑,宋元志踉跄着撞在一旁铁柜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此时猫才松口,一跃而逃,消失在杂物堆后。
宋元志缓缓低头,鲜血已顺着小腿汩汩而下,渗进袜子,流入鞋内,布料瞬间染透。他愣在原地几秒,才意识到脚下一片刺痛如火烧。四道抓痕交错其间,其中一道咬痕呈半月形,边缘齿印清晰,皮肉翻卷,夹杂着猫毛、灰尘与泥渍,整个伤口触目惊心。
当时值班保安听到动静迅速赶来,一眼看到宋元志满腿是血,脸色惨白,立刻从门岗拿来纱布压住伤口,一边止血一边安抚他不要乱动,同时掏出对讲机,语气紧张地通知院内医务室请求紧急支援,语速快得几乎打结。

院感科主任闻讯赶到,一眼看到宋元志的伤势便眉头紧锁。他迅速蹲下查看创面,小腿内侧四道抓痕交错分布,最深处超过2.6厘米,几乎穿透皮下脂肪,接近筋膜层,且有明显异物残留。红肿灼热,皮肤边缘呈暗红色,创口夹杂猫毛、灰尘和铁锈细屑,典型的污染伤口。主任低声道:“污染严重,必须立刻彻底清创,不能拖延。”
随即,清创程序在感染控制室快速展开。医生戴上双层手套、护目镜与帽套,操作全程无菌。助手打开3%过氧化氢,冲洗液起泡翻滚,发出“滋滋”声。宋元志疼得整条腿发抖,下意识想躲闪,却被护士稳稳按住大腿。“再忍一下,必须彻底冲干净!”主任边说边指挥护士拿来生理盐水与碘伏交替使用,对创面进行十余轮冲洗和擦拭。
随后,医生取镊子仔细探查创口内部,一根根猫毛、一粒粒灰渣都被小心夹出,有些粘附在组织深层,必须轻轻挑开肉口才能看清。宋元志额头青筋绷紧,呼吸粗重,指尖因为剧烈疼痛而泛白,冷汗一滴滴打湿后背。他忍着痛,牙关咬紧不发出声音,但整个肩膀止不住地颤抖。
清创结束后,医生再次确认创口边缘无可见污染物,才进行消毒覆盖。整个过程历时近四十分钟,操作精细到毫米,显示出高度专业性。处理完毕后,主任立即做出决定:伤势严重、动物来源不明,必须尽快转至具备狂犬病暴露处置资质的定点医院,接受后续疫苗与免疫球蛋白注射。

救护车以最高优先级送达市区疾控医院。急诊值班医生早已等候,他迅速带宋元志进入隔离处置区,再次查看伤口并确认暴露等级为III级(深层抓咬伤,伴污染)。流程立即启动:第一步,再次彻底清创,确保组织边缘无病毒残留;第二步,立即进行人用狂犬病疫苗首针接种;第三步,在创口四周进行狂犬病免疫球蛋白的“环绕式”注射。
“这一步很关键。”医生一边操作一边解释,“免疫球蛋白是被动免疫,能在疫苗起效前先帮你挡住病毒扩散。这几毫升药液必须分点分层打进创面周围,注射均匀,不能有死角。”说话间,他用极细的针头将药液缓缓推进皮下,每一次都引发针刺般疼痛,宋元志的脸色一度扭曲,但始终一动不动,像在手术台上的病人一样配合。
注射完成后,医生非常严肃地交代了疫苗的标准程序:“你必须按0、3、7、14、28天注射五针,一天不能错,一针不能漏。哪怕你是医生,这一点也不能有丝毫含糊。”他说着在疫苗接种卡上郑重地写下日期,还用红笔圈出下一次注射时间,并叮嘱宋元志设置闹钟提醒。
医生目光坚定地继续说道:“任何免疫程序,都是建立在完整刺激基础上的。一针缺失,整个免疫屏障就可能崩塌,病毒一旦突破神经系统防线,没有任何药物可以逆转。”临走前,医生还强调了疫苗接种期间的生活禁忌——必须保持良好作息,不熬夜、不饮酒、不剧烈运动、不吃刺激性食物,特别要避免工作中接触透析液、患者血液等高感染风险环境。他建议宋元志在恢复期间尽量调换为门诊轻任务,不再参与夜班和ICU重症管理。

医生补充道:“还有一点很重要,你自己就是医生,知道创面复原不只是靠药物,还要靠机体状态。如果免疫系统疲弱,疫苗也很难起作用。”宋元志点头如捣蒜,他知道对方说得句句在理。
从那一刻起,宋元志将“规范接种”视为头等大事,几乎用执行临床路径的标准来管理自己的恢复期。每天按时接种,准点打卡;每针接种后,他都会在留观区安静坐满三十分钟,留心任何头晕、皮疹、气促等异常反应,从不草率离开。他将伤口包扎得密不透风,用医用透气敷料替代传统纱布,每日早晚坚持用碘伏清洁,定时更换敷料,绝不让伤口沾染一粒尘埃。
宋元志还主动找院办申请调整排班,从高压夜班换成了日间门诊,并婉拒了几场学术演讲,避免过度疲劳。他戒掉了多年难改的夜宵与咖啡,早餐坚持鸡蛋与牛奶,午晚餐优先选择鱼类、豆制品与绿叶蔬菜,几乎将自己的饮食管理到了病人级别。连一向无法割舍的辛辣口味也彻底放弃,转而热衷于水煮清淡。晚上十点半准时洗漱,十一点前关灯入睡,睡前不看手机,不刷病例,听着低频白噪音强迫自己进入深睡状态。
同事们看宋元志如此上心,连带着也更加谨慎,有人主动替他值夜班,有人每天帮他打餐送水。慢慢地,他的状态也明显变好,面色红润,眼底的青黑淡了许多,讲话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带着疲惫的喘息感。主管医生见他状态稳定,甚至批下他一周轮休,让他回家好好调养。

就这样,三周后伤口顺利结痂,局部无红肿、无渗液,精神状态也恢复如初。8月中旬,医院组织中层医生例行体检,宋元志主动申请加做狂犬病IgG抗体滴度检测。他紧张地坐在抽血椅上,手心满是汗。等待的三天里,他始终心悬一线,直到收到结果:抗体滴度1:65,达标,提示保护性免疫已成功建立。宋元志终于松了一口气,医生也告诉他可以安心恢复正常工作。但谁也没想到,几个月后,一场更可怕的风暴,悄然逼近...
2021年12月4日上午八点,宋元志像往常一样在重症监护病房查房。他正带着两名实习医生讲解一名慢性肾衰患者的超滤控制方案,语气沉稳,思路清晰。可就在说到“血流动力学稳定”这几个字时,他突然皱紧眉头,腰背骤然发紧,仿佛有人在他脊柱下段扭了一把。紧接着,一股钝痛自腰椎猛然冲上,沿着背部窜到颈后,像一条灼热的铁丝狠狠抽打过去。他整个人一颤,话音戛然而止。
额头顷刻布满冷汗,胸口发闷得像被石块压住。宋元志下意识后退两步靠在墙上,手中的查房本滑落在地,纸页散开。视野开始旋转,走廊的灯光在他眼中化作重叠的白斑,耳边只剩低沉嗡鸣。他张口想说“我出去一下”,却发现下颌已经僵硬,舌头沉得几乎动不了。胸口强烈的压迫感让他吸不进气,喉头发出短促的“呃——”声,肩膀急促起伏。
宋元志扶着墙想缓过来,可左腿一软,整个人几乎滑坐到地上。汗水顺着鬓角狂涌,湿透了白大褂。实习医生被这一幕吓懵,急忙冲出病房呼叫护士。几人赶来,将宋元志抬到空床上平躺。此时的他已经脸色惨白,唇色发青,呼吸急促而浅短,胸膛剧烈起伏,指尖微颤。护士刚为他解开衣领,宋元志忽然抬手,艰难地比划着要水。

一杯温水送到嘴边,杯口刚触及唇齿,他喉头便剧烈收缩,脸部瞬间扭曲。他像被电击般猛地后仰,双手死死抓住床沿。那种疼痛是撕裂式的,从喉咙深处一直灼到胸口,就像有尖刀在气管中来回搅动。仅仅咽下一小口,宋元志却立刻引发爆发性的剧烈咳嗽——那声音嘶哑、干涩,每一次气流冲出都带着痛楚的喘鸣,胸腔被震得发烫,仿佛被烈焰灼烧。
他用力拍打床板,咳嗽一波接一波,喉间涌出浓痰和唾液,混着血丝溢出嘴角。呼吸声断续,氧气仿佛进不了肺。周围护士纷纷上前协助吸氧,监护仪滴滴报警。宋元志的双手青筋暴起,指甲死死嵌进掌心,脚尖在床上不受控地抽搐。片刻后,咳嗽渐弱,但胸口起伏仍剧烈,他的面色从惨白转为潮红,额头青筋突起,整个人像被耗尽气力般瘫在床上。
急救医生赶到,立即启动应急程序。气囊吸氧无效后,医生迅速决定气管插管。助手固定头部,主刀医生一边压舌,一边迅速插管固定。呼吸机接入后,氧饱和度暂时回升至76%,但血压急速下降,心率不规则跳动。医生立刻静推镇静剂,控制痉挛,又补充升压药以维持循环。
不到三分钟,宋元志突发全身强直性抽搐——四肢僵硬,背部弓起,牙关紧咬,面部肌肉痉挛得变形,口角不断溢出白沫。两名护士合力固定身体,另一名医生紧急吸痰,防止窒息。监护仪上,心率从140次/分骤升到170次/分,血氧再次跌破60%。医生果断加大氧流量,建立双静脉通路,同时快速注入液体维持血压。

抢救过程中,CT及脑脊液穿刺同步进行。半小时后,检验结果回报:脑脊液压力显著升高,白细胞总数12.7×10⁹/L;唾液与脑脊液PCR均检出狂犬病毒RNA;血清抗体IgM阳性,滴度1:120。结合吞咽困难、咽痉挛、恐水、抽搐、意识障碍等症状,明确诊断为狂犬病。
听到结果,抢救团队神情凝重。医生继续全力维持生命体征,使用多巴胺升压,静脉推注肾上腺素,反复进行电除颤。心电监护上的波形一度短暂回升,但随后又逐渐平缓。呼吸机发出持续警报,血压降至70/40mmHg,心率跌至40次/分。医生大声指令:“继续按压!加肾上腺素!准备再除颤一次!”
然而,持续的胸外按压再也没有带来波形的跳动。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经过整整一小时的抢救,宋元志的瞳孔逐渐散大,对光反射消失。监护仪的心电线缓缓停在一条直线上——那是生命的终点。医生摘下口罩,沉声宣布:“抢救无效,患者于十点零一分死亡。”
在抢救室外的长廊尽头,宋元志的父母呆呆站着,一动不动。母亲双手死死攥着那张盖着鲜红印章的死亡通知单,眼神茫然地盯着纸面上的黑字,像是灵魂被掏空了一样,喉咙哽咽,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忽然间,她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冰冷的地砖上,双手颤抖地举着那张纸,声音嘶哑破碎:“不可能……我儿子才三十二岁,是医生啊,每一针疫苗都打了,怎么会走到这一步……”那一声崩溃的哀嚎在安静的走廊里来回回荡,刺得人心一阵阵发紧。
父亲则蜷缩在墙角,额头抵着冰冷瓷砖,手中攥着那份检测报告,指关节泛白,血管鼓起。他牙关咬得咯吱作响,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缓缓抬起拳头,一下一下砸向地板。那闷闷的砸击声,如同沉重哀痛的节奏,在长廊回音中更加沉郁绝望。

过了一会儿,母亲仿佛突然抓住最后一丝希望,跌跌撞撞冲到医生面前,语调几近崩溃:“不可能!你们一定搞错了!猫抓了他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去了医院,清创、打针、每次留观他都按时完成,他一向听话,从来没违背过医嘱,怎么可能出这种事?是不是疫苗出问题了?是不是根本没起效?”
面对眼前几近失控的母亲,医生神色凝重却语气坚定:“疫苗质量绝对没有问题。每一批次都有唯一编号,从生产、运输到接种全流程可追溯,流程公开透明,根本不存在失效或造假。更何况疫苗不是会突然失灵的东西。按常理说,完成全程注射,是足够建立有效免疫屏障的。这起事件的问题,恐怕不在疫苗本身。”为了进一步排查,他又看向父亲:“这几个月内,有没有再接触过动物?哪怕是不小心被抓破、咬伤,或者有哪怕极细小的伤口?”
父亲眼神空洞,嘴唇轻颤,拼命摇头,语气颤抖却坚定:“没有!自从那次后,他连看到流浪猫都躲着走,宠物店都不敢靠近。我们天天叮嘱他,他非常谨慎,绝对没有再接触任何动物!”
在场医护心中都明白:狂犬病毒绝不会凭空复发。如果接种流程无误,唯一可能的解释只能是——某个关键细节被忽略了。为了寻找真相,医生团队调取了宋元志从受伤开始的完整医疗记录,清创过程、疫苗接种时间表、抗体检测报告全部复核,甚至连家属平时记录的生活习惯、饮食作息的小笔记本也一并仔细翻查。他们一页页地翻,一条条地对,连每一个接种登记的时间和批号都不放过。

夜里,值班办公室灯火通明,几位年轻医生神情凝重地比对着资料。疫苗接种的时间、编号、体温监测数据都井然清晰;每次留观时的记录都写得一丝不苟;血清抗体检测也明确显示阳性反应。按理说,所有步骤都严丝合缝,没有漏洞。但病人依旧发病,事实本身就如同一道无法解开的死结,沉沉压在人心头,像被雾团裹着,每呼吸一下都感到沉重。
就在这时,急诊楼另一端传来一阵沉稳而急促的脚步声。老主任带着几名助手快步赶来。他本在会议室参与医院专题讨论,刚准备离开就接到通报,说有一例完成全程免疫仍发病的病例抢救无效。他没有片刻迟疑,立刻赶回医院。进门后他面色冷峻,神情专注,走路稳健,直奔主治医生所在的位置,一边走一边简短询问患者从抓伤到发病之间的所有关键节点。
听完医生们的简要汇报后,老主任缓缓转身,目光落到走廊尽头仍在啜泣的父母身上。母亲眼睛哭得通红,父亲仍攥着那张揉皱的化验单,脸上满是失魂落魄。老主任语气低沉而郑重:“坐下说话吧吗,你们的孩子在抓伤后半小时内就送医,做了彻底清创,也按照国家推荐流程接种了疫苗与免疫球蛋白。我刚刚再次确认过了,接种时间、剂量、批次都无误。同批接种的人我们也已回访过,无一例发病。从流程上看,不存在任何差错,药物也没有问题。”
他稍作停顿,看向那对几乎哭成泪人的父母,语气转为深沉:“既然所有治疗环节都无误,那就很可能是后续的生活细节出了问题。狂犬病的潜伏期和是否发作,往往和伤后护理、免疫期间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话音刚落,宋元志的父母几乎同时站起,带着哭腔争辩:“我们回去后照顾得非常仔细,严格照着医院小册子上的每一条做!一针都没漏,每次消毒都按时进行,从没胡乱用药!”母亲哽咽着说道:“我们从不敢自己处理伤口,每天都带他去药房做专业清创,器械全是一次性的,我们不敢马虎。”父亲声音颤抖着接过话茬:“我们是按你们说的做的,从没少过任何一个步骤,怎么会还出这种事?!”
老主任静静听着他们的陈述,眉头一点点皱紧。最初他怀疑可能是哪步没做到位,但现在听来并非如此。他挥手示意两位家属先坐下,语气缓和下来:“别急,我们慢慢梳理,会找到问题所在的。”于是,他们从宋元志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条回顾:他用的是专属的牙刷和毛巾,饮食清淡,坚决不碰生肉和酒精;每天规律作息,绝少熬夜;用药严格遵循医生医嘱,伤口护理全程使用一次性器具,从未擅自更改处理方式;更未接触过任何动物。
老主任沉思良久,眉头始终紧锁。忽然,他缓缓开口道:“能让我看看他手机里的相册吗?”这一句让宋父宋母一愣,有些不解地对视。老主任耐心解释道:“人的记忆常会遗漏细节,但手机里的照片和视频不会。也许那里能找出些线索。”两人迟疑片刻后,终于点头同意。母亲颤抖着输入密码,把手机交到主任手中,并翻出了几张日常拍摄的照片。
老主任接过手机,开始按时间线逐一翻看,尤其关注近一个月的影像资料。一张张画面迅速滑过,记录着生活的琐碎日常。他看得极为认真,眉头越皱越紧,但始终没说话。正当准备合上手机时,灵光一闪,他又迅速滑动屏幕返回更早几个月的影像,语气突然变急:“不对,得往前再看看……”

果不其然,当一段视频跳出画面时,他的动作戛然而止。老主任连忙反复播放前后的内容,表情由疑惑变得沉重。紧接着,又调出几段相似片段逐帧放大查看。
看完最后一个视频后,他缓缓放下手机,长长吐了一口气。会议室的气氛仿佛凝固,所有人都屏住呼吸。他靠在椅背上,神情沉重,语气却平静下来:“我明白了为什么宋元志在完成全程疫苗、规范清创之后,还是狂犬病发作了。”
说完这句话,老主任摘下眼镜,目光扫过全场,语气中透着深深的遗憾:“这既不是疫苗本身的质量问题,也不是宋元志在伤口处理上疏忽大意,更和饮食、接触动物无关。真正的原因,源自他打完疫苗后日常生活中2个极小、极容易被所有人忽视的细节。这2个小到连他这样谨慎自律的医生都没有意识到,小到在场诸位经验丰富的医生也一度忽略的细节。如果不是我在狂犬病研究上坚持了二十多年,我也绝不会把这个看似毫无关联的习惯,与这场致命的发病联系在一起啊!”

第一个细节,是伤口部位具有极高风险。宋元志是在接诊一位被狗咬的病人时,右手食指外侧被犬齿刮破了一点皮肤,伤口看上去很浅,也没有出血,只是轻微破皮。他立刻用碘伏进行了消毒,并在之后接种了五针疫苗。从流程上来看处理无误,但问题出在伤口位置。手指外侧尤其是靠近桡神经分支的区域,神经末梢极其丰富。
狂犬病毒并不是通过血液传播,而是偏好神经组织,一旦侵入皮肤,就会顺着神经路径一路向中枢蔓延,最终进入脑组织。如果伤口靠近神经通道,病毒在极短时间内就能进入神经系统,绕过身体的免疫防线。相比之下,如果是小腿、背部等神经相对稀疏的位置,病毒传播速度会慢得多,身体也更有时间产生足够的免疫保护力。宋元志看似只是皮肤浅破,实则病毒的突破口正好落在高风险地带。
第二个细节,是暴露源看似“平静”,容易误导判断。当时那只流浪狗虽然已咬伤多人,但表现并不狂躁,既没有流口水,也没有猛烈扑咬,而是状态萎靡,反应迟钝。宋元志依照临床经验,认为这条狗不像处于发病状态,因此评估其传播风险较低。但这种判断恰恰忽略了动物在病程初期的潜在风险。
实际上,狗患狂犬病的早期阶段,常常表现为情绪沉静、活动减少,不一定表现出剧烈的攻击行为。这种低调的状态往往更具危险性,因为此时唾液中已经含有高浓度病毒,但动物本身还未进入完全失控期,极易被人误判为健康。宋元志因此并未主动申请免疫球蛋白的使用,失去了额外一层保护屏障。对风险的低估,让他在判断处理策略上留有缺口。

第三个重要因素,是身体状态影响了疫苗的免疫效率。虽然他严格按五针程序完成了疫苗接种,也未曾漏针,但在这期间,宋元志始终处于严重透支状态。他在暴露后第二天就连夜参与了抢救任务,此后连续夜班,平均睡眠时间不足三小时。人在极度疲劳、长期睡眠剥夺和精神压力高负荷的情况下,免疫系统功能会受到明显抑制。疫苗的作用依赖于免疫系统的反应能力,如果身体状态不佳,即使注射了疫苗,也可能因抗体产生延迟或效力不足,出现所谓的免疫空窗期。在这段时间内,如果病毒已通过神经通路迅速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疫苗来不及发挥保护作用,就会失去防控机会。对于宋元志来说,他暴露后第10天开始出现轻微的后颈放射性酸胀,这或许已是病毒进入神经通道的早期信号。
另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宋元志在接种疫苗后的第三天,出现过低烧、轻微的头晕和胃口不佳。他以为是疫苗反应所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也未向医院报告。事实上,这些反应可能不仅仅是接种副作用,也可能是病毒与免疫系统“角力”过程中的生理反应。如果能在当时结合伤口位置和动物状态重新评估风险,或许还来得及补充免疫球蛋白,但遗憾的是,这个机会错过了。
宋元志的病程发展极快。起初只是感到脖子酸胀,逐渐出现喉部发紧、吞咽困难。随后在值班途中突发意识恍惚、剧烈咳嗽、出冷汗。他在喝水时出现剧烈咽喉痉挛,不自主地将水喷出,这是典型的咽喉肌肉抽搐。接着症状加重为持续高热、意识模糊、四肢抽动,最终进入昏迷状态。整个过程不到72小时,从初期不适到深度昏迷,迅速发展为中枢神经系统的严重破坏,呈现典型的脑炎型狂犬病表现。
即便医院动用了最全力的救治措施,包括呼吸支持、镇静、激素调节和中枢保护,仍无法逆转疾病的进展。狂犬病一旦进入临床发作期,至今尚无特效治疗,病死率接近百分之百。宋元志的病例让医学界再一次面对这样一个几乎无法挽救的疾病,也再次提醒所有人:面对狂犬病,防范永远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哪怕伤口很小、哪怕动物没发疯、哪怕流程已完成,只要存在高风险因素,就必须全程严防死守,不给病毒留下任何机会。
资料来源:
1.李伟,王静.狂犬病暴露后疫苗接种的免疫效果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24,58(04):367-371.
2.赵磊,刘芳.我国狂犬病疫情变化趋势与防控策略研究进展[J].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2024,40(05):452-457.
3.陈凯,张倩,周洋,等.重症狂犬病患者的临床救治经验与病例分析[J].中华感染与免疫杂志,2024,34(06):589-593.
(《纪实:32岁年轻医生被流浪猫抓伤后按时接种5针狂犬疫苗,却在两个月后仍发作身亡,主任痛心警示:这3个常被忽视的细节,影响疫苗药效》一文情节稍有润色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图片均为网图,人名均为化名,配合叙事;原创文章,请勿转载抄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