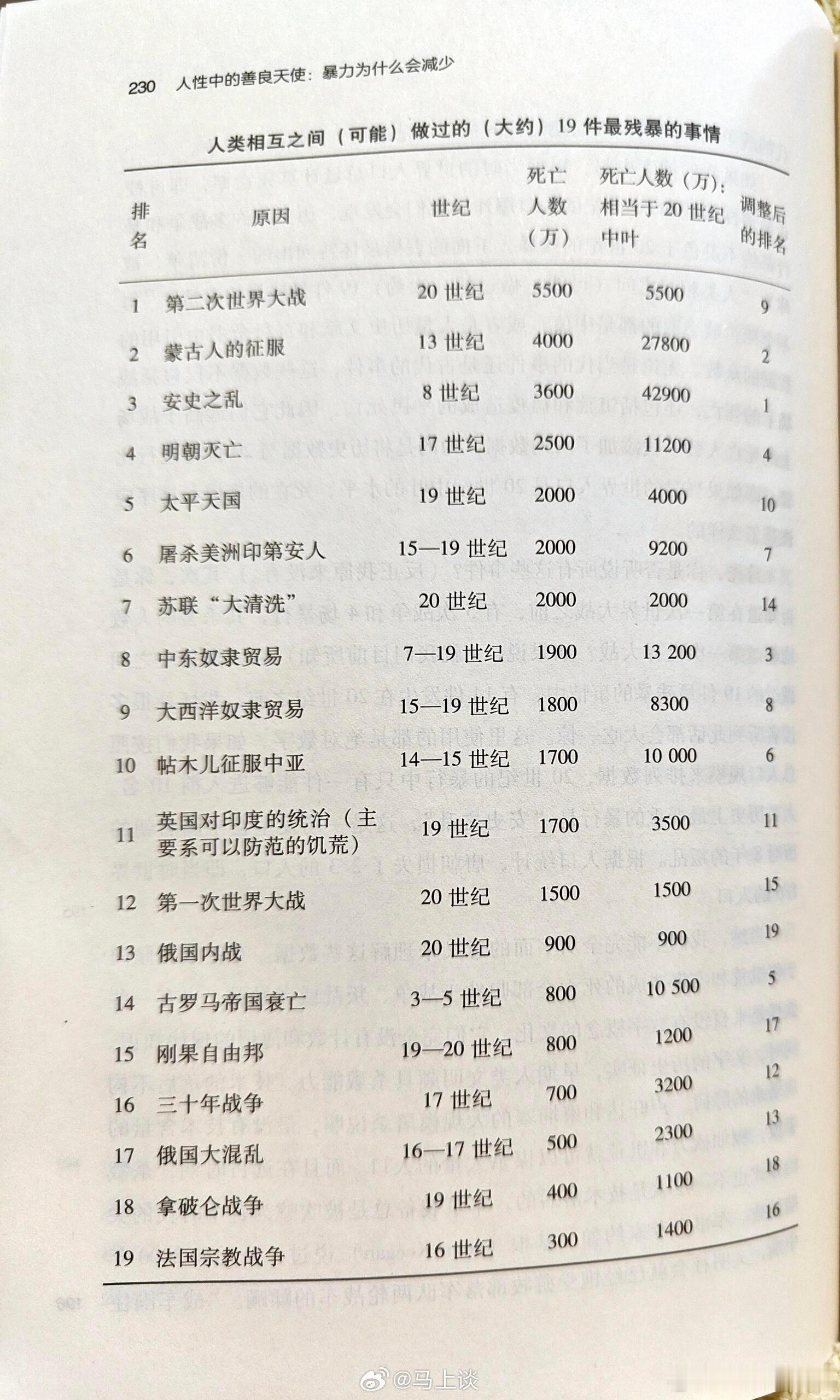《韩愈传》作者:谷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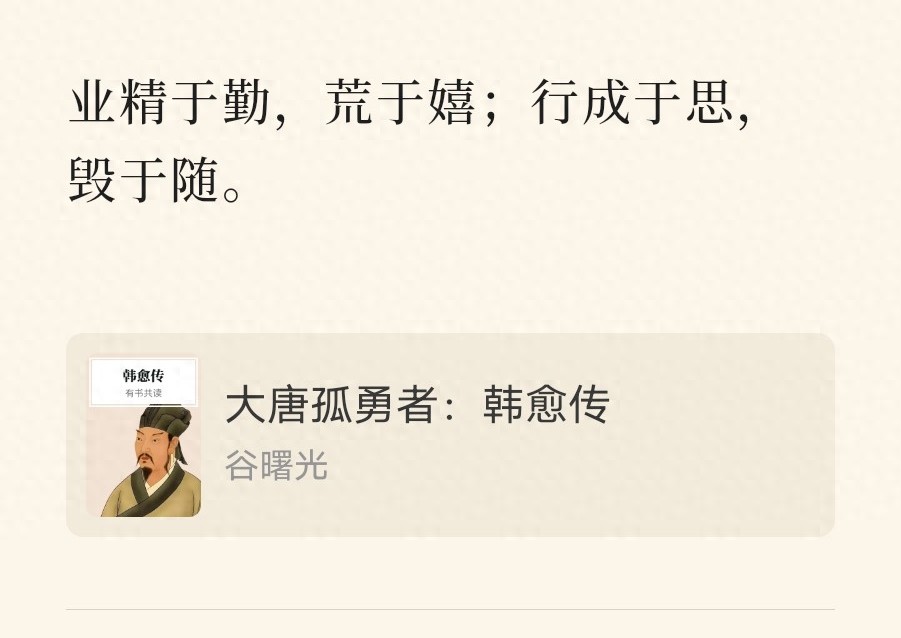
韩愈这个名字大家肯定都听说过。他和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变华丽繁复的骈文为简约直白的散文,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我们读书时语文课本里经常收录他的作品,比如《师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等等。
但如果我们走近这位“一代文宗”,就会发现他可不止这一张面孔。他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诗人,而且是政坛上的“超级网红”,以“杠精”和“㨃上司”而著称天下。他初出茅庐就敢㨃宰相,还㨃过皇帝,还差点因此丢掉性命……
但他的“杠”和“㨃”并非无意义的情绪对抗,而是一种“不平则鸣”,是哪怕不为权贵所容,也要为弱者和真理发声;所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谷曙光老师在他的新书《韩愈传》中,直接把这位大文豪“定性”为“大唐孤勇者”。
2021年底,《孤勇者》这网络神曲爆火出圈。歌词中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来自于蛮荒,一生不借谁的光,你将造你的城邦在废墟之上!”正是韩愈在历史中的模样。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谷曙光老师的笔锋,看看韩愈这位大唐的孤勇者,是如何对峙着绝望、孤身走暗巷,最终在废墟之上造就自己的城邦。
庶出孤童的 “逆袭火种”
我们先从韩愈的身世讲起。公元768年,韩愈出生在今天的河南孟州(另一种说法是出生在长安)。因被后人尊称为韩昌黎,所以很多人以为他出生在河北的昌黎。其实,昌黎类似于郡望,因当地在唐代出过韩姓宰相,于是姓韩的人都往该地“靠”,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
韩愈出生时,“安史之乱”平息未久,原本强盛的大唐仍然未能摆脱政治危机,内有宦官专权之乱,外有藩镇飞扬跋扈。而在文坛之上,王维、李白等巨擘已先后去世,“诗圣”杜甫已经白发苍苍,步入暮年。大唐急需一批新人来重振辉煌。
韩愈的父亲叫韩仲卿,曾官至秘书省秘书郎,又曾任武昌令、鄱阳令;二叔叫韩云卿,官至礼部侍郎。“诗仙”李白对他们两位评价颇高,赞叹哥哥韩仲卿对百姓“惠如春风”,又把弟弟韩云卿比作汉朝的张良,“文章冠世,朝廷呼为子房”。
韩愈就出生于这样一个官宦人家,但和当时的世家大族相比仍是寒门。他排行第四,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大哥韩会比他大近三十岁,以常理推测,他们的生母应该不是同一人。韩愈三岁时,父亲撒手人寰,他是由大哥韩会和嫂子郑氏抚养长大的。
颇为怪异的是,韩愈的现存诗文中无一处提及生母,这是很不正常的。还有,他的弟子和好友写的传记和墓志铭中,也都没有提到他的母亲。因此后世学者推测,韩愈应该是庶出之子,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中矮人一等,所以不愿谈及此事。
值得玩味的是,韩愈不提生母,却为乳母李氏写过一篇情深意切的墓志铭,信息含量颇大。墓志铭里说,他出生没多久,嫡母就过世了,之后父亲也离开了人世,这位李姓乳母见他可怜,不忍离开,于是一直待在韩家照顾,前前后后四十年。
可以说,乳母李氏亲眼见证了韩愈一生中的重要时刻,高中进士,入朝做官,娶妻生子,等等。而韩愈对她也非常尊敬、孝顺,逢年过节,都要带着妻子和孩子,给老人家行礼、贺寿。
此外,这篇墓志铭还写道,李姓乳母去世后韩愈还给她安排了一场盛大的葬礼。这种郑重其事的态度,让后世的学者有理由怀疑,韩愈与这位乳母的关系非同寻常。甚至有学者断言,这位李氏就是韩愈的生母。因为地位卑微,所以她虽然生下了孩子,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名分。韩仲卿去世后,她不好再待在韩家,但也舍不得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只能以乳母的身份留下来,用心地抚育韩愈。
韩愈的父亲去世后,大哥韩会接过了养育幼弟的重任。不管在哪里做官,他都把韩愈带在身边,亲自指导功课。韩愈在读书方面颇有天赋,也知道努力上进。或许庶子的身份让他更为敏感,渴望着能通过读书崭露头角、光耀门庭。
不幸的是,公元779年韩会卷入政党之争,被贬官岭南,一年后就忧愤故去。此时韩愈才13岁,关键时刻是长嫂郑夫人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她把丈夫的灵柩归葬孟州老家,然后又带着一家老三十余口,迁往今天的安徽宣城,就食江南。
大文豪巴尔扎克曾说:“不幸是天才的进升阶梯。”而韩愈正是如此。这位寒门庶子早早就懂得了踔厉奋发,勤奋苦读。晚年时他回忆道:“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也就是说,只要听到有好书就要找来看。
除了酷爱读书,韩愈还早早立下大志。他在诗中写道:“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屠龙破千金,为艺亦云亢。”少年时就立志要学会屠龙术,帮朝廷成就霸王之业。他还想要建立上古圣贤皋陶、后稷那样的功勋,文章要超过曹植、谢灵运。
公元783年,韩愈的堂兄韩弇考中了进士;三年后,韩愈离开家乡,前往长安投奔堂兄。他想要靠这一身才华改变命运,上升到更高更大的平台一展宏图、报效国家。满怀建功立业的热血,他在内心呼喊道:“长安,我来了!”
屡败屡战,愤然上书宰相
在唐朝,寒门学子要想在长安施展抱负,只有四条路径:第一是通过科举考试;第二是从军当幕僚,写出“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高适就是典范;第三是隐居,如李白走的终南捷径;最后是像杜甫一样,献上诗赋文章求官。
韩愈想走的,就是考进士这条路。他的堂兄韩弇考中进士后,此时已经担任殿中侍御史一职。韩愈前去投奔,没想到就在这一年的闰五月,韩弇在执行与吐蕃议和缔盟任务时,不幸罹难,命丧平凉。韩愈失去资助,生计陷入困顿。
山穷水尽之时,韩愈想到了堂兄有位好友,北平王马燧。于是,他在长安街头拦住马燧的车驾,以“故人稚弟”的身份,请对方施加援手。此后的八九年间,他在京城的衣食住行,只能仰仗这位“马王爷”。为了经济自立,他也迫切需要科举高中。
韩愈想办法找到了以前的进士科诗赋策的题目,也就是“往年真题”。看完后他非常自信,觉得“可无学而能”,就是说不用准备,直接去考都行!公元788年,他第一次赴考,以落第告终。韩愈并不是很在乎,他才21岁,来日方长。
之后两次赴考,结果仍然是铩羽而归。直到公元792年,他第四次赶考,这才高中。也就是在这一年,韩愈迎娶了范阳卢贻之女为妻。唐朝有五姓名家,赵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这五家的女孩贵不可言,就连皇室都渴望与之结亲。此时的韩愈“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堪称人生赢家。
不过,在唐朝,即便进士及第仍然不能做官,要么静候三年等朝廷安排,要么就考吏部的博学宏词科,一登第即可授官,可谓仕途捷径。但这场考试难度更大,韩愈中举那年,全国共录取进士23人;但博学宏词科,通常每年只录取3人。
为了考博学宏词科,韩愈又求得“往年真题”。一番研究后,他仍觉得不在话下,但竟然被刷了下来。据说吏部主考官赏识他的文章,已经准备录取,结果宰相更看重华丽的骈体文,直接把写古文的他的名字划掉了。结果这一年,只有两人登科。
之后韩愈又参加了两次考试,还是折戟沉沙。这并非因为他的才华不够,而是文章的观点、风格,入不了当时宰相的法眼,直接说他的文章不合时宜。愤愤不平的韩愈于是策划了一桩“大事件”,一连三次到光范门上书宰相,以情以理抗争。
光范门是长安大明宫西内苑东门,直通宰相办公的中书省,相当于是大唐“国务院”的传达室。在第一封上书中,韩愈低声下气地“卖惨”,说自己“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现在饥寒交迫、无有归属,希望朝廷能赐一个最低等的职位历练,能填饱肚皮就行了。
那这封信起作用了吗?石沉大海,毫无音讯。19天后,韩愈给宰相送来了第二封上书,说自己多年来一直刻苦学习、身体力行,现在却陷入穷困饥饿的水深火热之中,不得不疾呼求助。他问宰相对于这样的学子,您是救助,还是袖手旁观呢?
宰相用置之不理的态度给出了答案:不救。10天后,韩愈把第三封上书送到了光范门。他以质问的口气写道,宰相应该像周公那样吐哺握发、赏识举荐人才,而不是面对我一再的上书,一言不发,没有回音。这不是尸位素餐,又是什么?
平心而论,韩愈之所以一再上书,是因为唐初的确有“上书拜官”的先例,但现在是中唐,靠上书来求官这条路早就被堵上了。而且韩愈的上书等于是将了宰相一军,提拔他吧,说明以前的人才选拔有问题;公开否定吧,三篇文章尽显才华。
那对于韩愈的这种做法,可能有人会觉得他汲汲于名利,且狂妄自大、哗众取宠。但客观地讲,当时韩愈也有自己的苦衷,正所谓“长安居,大不易”,而他七八年来毫无经济来源,只能寄人篱下,如何不焦虑,不痛苦呢?
退一步说,韩愈知道是宰相打压自己,于是坦坦荡荡地上书求官;比起想做而不敢做的人,或者为达目的背后搞小动作的人,更是强上太多。
虽然最后韩愈没有求到官,但他却出名了。整个长安城都知道,落榜生中有个叫韩愈的有才之士。
多年后韩愈在《马说》一文中感叹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只有了解了这位“落榜生”七次考试、三次上书的遭遇,我们才能体会《马说》背后,那种怀才不遇者的悲凉。
那么,这匹“千里马”是怎么等到了第一任伯乐,正式步入职场的呢?作为新人,他又遭遇了哪些机会,哪些挫败呢?下节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