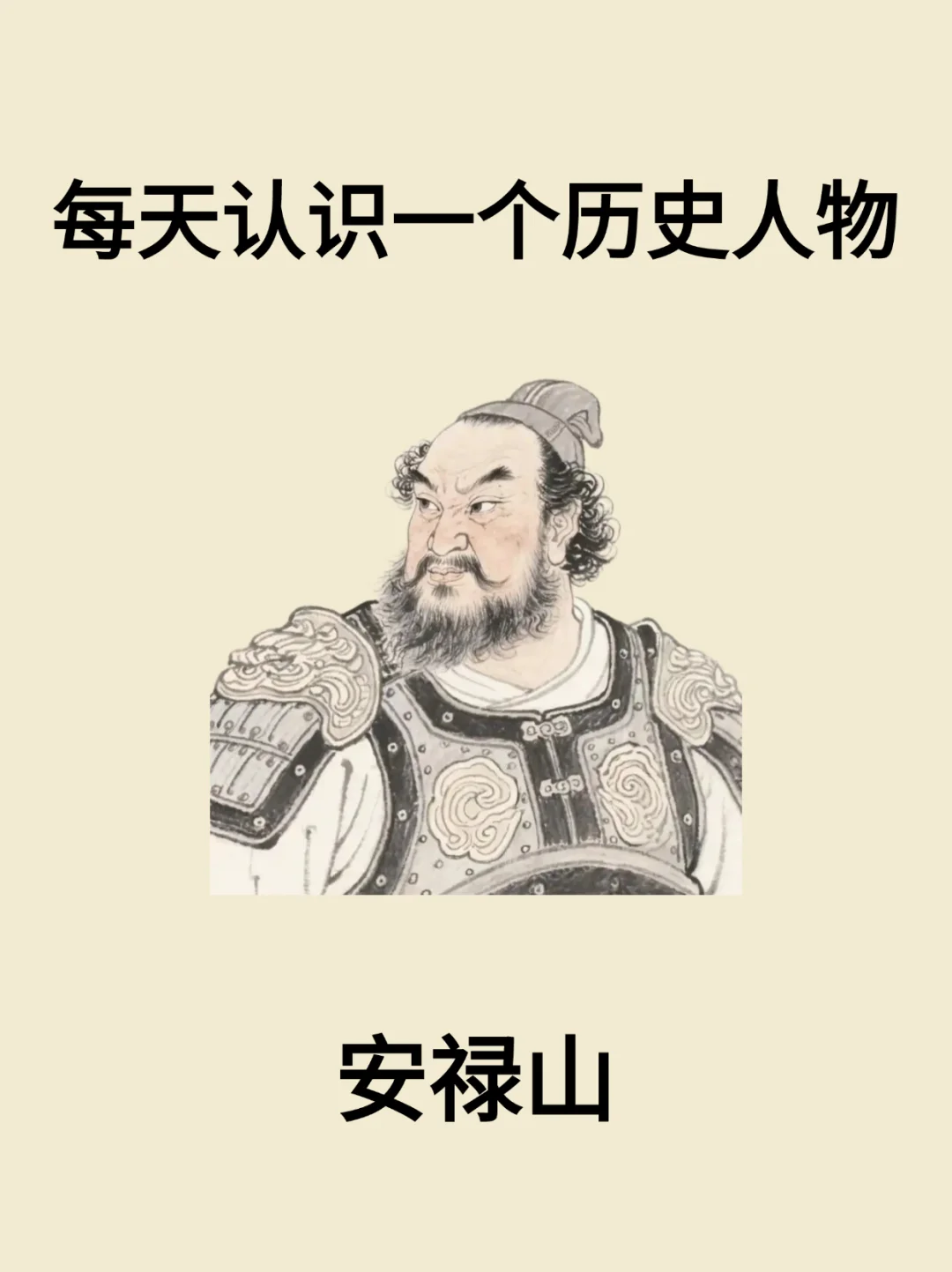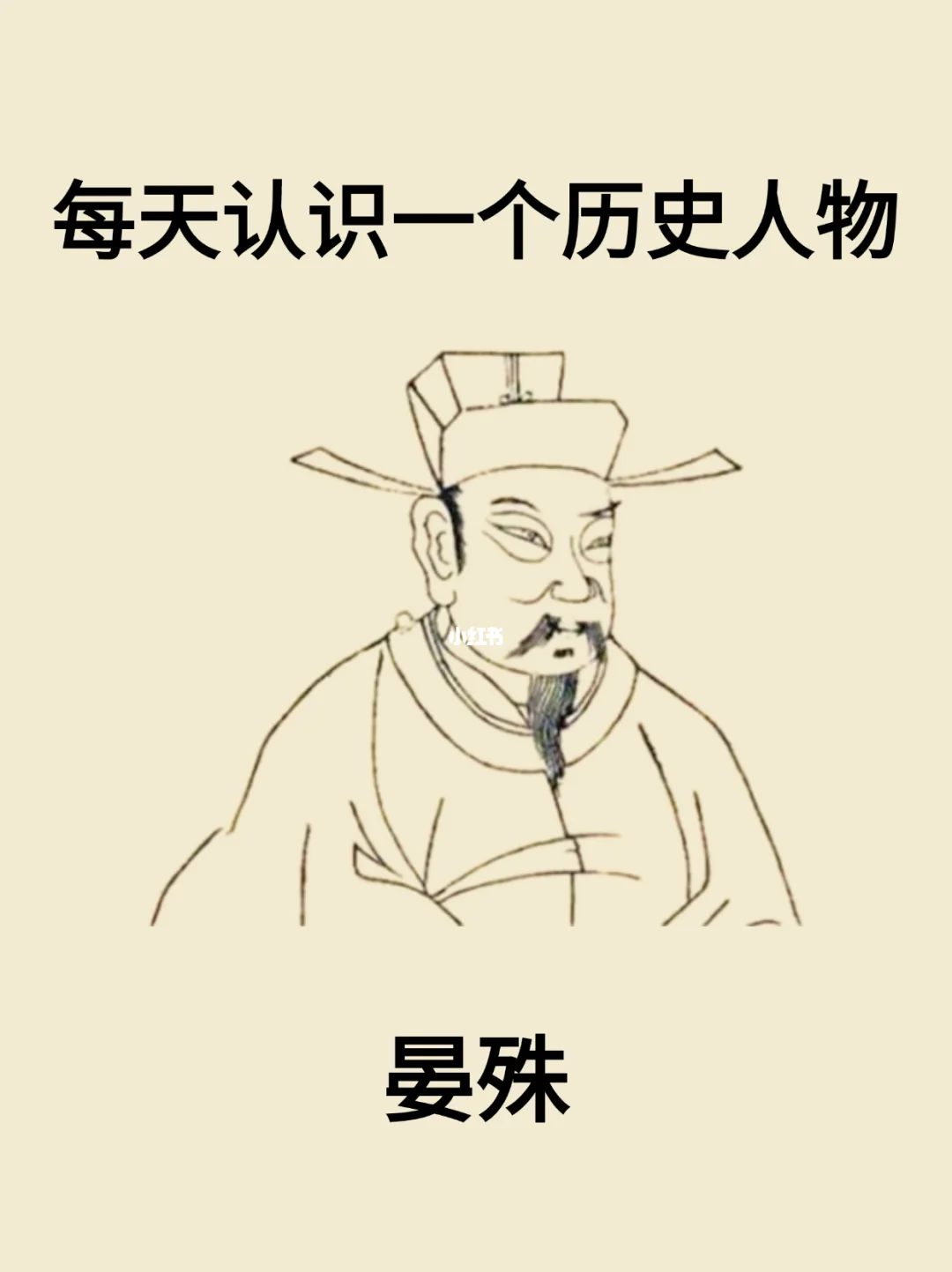“女儿在重症监护室等着救命的钱!你还死抱着那些股票干嘛?”
李刚冲着王芳怒吼着,可王芳却低着头一言不发。
女儿病得那么重,家里欠了一堆债,亲戚朋友都把他们拉黑了,信用卡也早就刷爆了。
大家都觉得她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
就在一切都快要彻底崩溃的那晚,她独自回到家,手抖得厉害,打开了股票交易网站。
三十秒后,她盯着账户余额,整个人像被定住一样,愣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01
2011年深秋的傍晚,上海浦东,天色已经有些暗了,路上车流还是那么堵。
王芳坐在阳台上,手里端着一杯咖啡,眼睛紧紧盯着腿上的笔记本电脑。
王芳今年四十三岁,在一家金融公司做部门主管,职位不算太高但收入还不错,日子看起来过得挺安稳,可最近她迷上了一样东西——股票投资。
电脑屏幕上显示着一个股票交易平台,K线图一闪一闪的,像在跟她较量,她盯着那些数字,眼神专注得让人有点害怕。
她已经研究这只股票好几天了。
“这股票现在每股六百块,还能买,再不入手就没机会了。”她小声自言自语。
她查了很多资料,说这只股票几年前才几块钱一股,现在已经涨了几十倍,网上论坛里一堆人在晒收益,有人三年赚了好几十倍,她越看越觉得,这股票肯定还会大涨。
她开始盘算,手头有差不多350万,是早年投资房产赚来的,现在房价涨得慢了,她动了心思:不如把钱全砸进这只股票,搏一把大的。
“要是买八千股……如果涨到一万块一股,那就是八个亿啊。”她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你在那儿嘀咕什么呢?”丈夫李刚走进阳台,听到她在自言自语,有点好奇地问。
“我在想,要不要把家里的钱都拿去买一只股票。”王芳半开玩笑地说。
“股票?那是什么东西?”李刚一脸疑惑。
“网上很火的一只科技股,国外好多大公司都投了。”她认真起来,“我感觉这股票会大涨,涨得特别快。”
李刚脸色马上沉下来:“你要拿家里全部的钱去买个不靠谱的股票?你是不是疯了?!”
“刚哥,我是认真的。”她放下咖啡杯,“这不是瞎赌,我干金融的,我懂,这股票的涨势不是偶然,是大趋势。”
“你别跟我扯这些,你是懂投资,可你又不是能掐会算的神仙。”李刚声音大了些,“女儿下半年要上更好的学校,房贷还有五年,我爸妈身体也不好……你想拿这些钱去冒险?”
“我不是全压上去,是给自己十年时间。”王芳看着他,“十年不碰这笔钱,输了我们还有工资,赢了我们一家这辈子都不用为钱发愁。”
那天俩人吵得不可开交,谁也没说服谁,之后冷战了好几天。
最后,王芳还是下定了决心,她卖了家里一套闲置的公寓,把基金和理财产品全清了,还跟婆婆借了点钱,凑够了400万。
她分几次把钱转进股票账户,买了八千股那只科技股。
她没把股票留在平台账户,而是转到自己的证券账户,还把账户密码打印出来,存进一台旧笔记本,另一份加密后存进邮箱。
“十年不碰。”她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小心地夹在密码纸旁边。
那晚她坐在书房,看着屏幕上的持仓记录,心里像吃了定心丸。
她觉得自己抓住了未来的机会。
可她不知道,她赌上的不只是钱,还有家庭的和谐、丈夫的信任,甚至自己后半生的路。
02
从2011年买下那只股票后,王芳就像跟自己定了个“十年之约”。
股票被她锁在证券账户里,密码写好,纸质密码藏在旧笔记本里,从那以后她再没动过。
头两年,她几乎每晚都要刷刷行情,股价从六百涨到两千五,又跌回一千二,再跳到四千……她的心跟着起伏,但始终没松手。
她告诉自己:“这是赌十年,不是炒短线。”
可还没等到股票大涨,现实却给了她一记重击。
2015年,公司裁员,她被裁了,拿了点赔偿金后想自己创业,先是跟朋友合伙弄了个跨境电商平台,结果刚上线就没钱了。
后来又投资了一家小咖啡店,半年不到,房租涨得离谱,只好关门。
钱没赚到,家里开销却越来越大。
房贷得还,孩子上学要花钱,婆婆生病住了两次院,家里那点存款眼看着就快没了。
现在全家就靠李刚,他在一家物流公司做主管,工资稳定但不高,那段时间他经常加班,还接了点私活帮人跑业务,晚上还帮朋友修车赚外快。
王芳白天跑项目,晚上回家看到他坐在沙发上整理账单,心里既烦躁又愧疚。
“你能不能去看看那股票现在值多少钱?”李刚终于忍不住问,“你不是说会涨吗?涨了就卖点出来用呗,咱不用这么苦。”
王芳摇头:“现在还不是时候。”
“你到底在等啥?都快2020年了,那钱放那儿有啥用?”李刚急了。
“刚哥,我说了,现在还不到时候。”她语气有点强硬。
“你到底是信它,还是不敢看它?”李刚冷冷地扔下一句。
这句话让王芳愣了几秒,她没接话,转身进了书房。
那晚,他们一句话也没再说。
之后这种争吵三天两头就来一次,有时候是因为女儿学校要交学费,有时候是李刚太累了让她去接孩子,话题总绕回那只股票。
“我们守着座金山却过穷日子。”李刚说。
“你不懂投资。”王芳甩下一句,不再解释。
其实她也慌,股价早不是当年的六百块一股,2017年最高冲到十多万,后来暴跌,又慢慢回涨,她不是没想过卖点,但太清楚这种资产一旦开了口子,就守不住了。
所以她干脆啥也不看,不登录账户,不查行情,电脑密码也不更新,她告诉自己:不动就是胜利。
可她心里也冒出一句:“要是这股票真能翻身,我现在得多轻松。”
她也知道,轻松是有代价的。
那是一把锁,锁住她的执念,也锁住这个家喘不过气的感觉。
她赌的是时间,李刚赌的是耐心。
而耐心,是会被生活一点点磨光的。
2020年5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砸了下来。
那天是周三,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女儿李晓晓放学回家,刚进门就皱着眉说头晕,还说学校空调坏了,下午热得不行。
李刚以为是中暑,没太当回事,煮了碗绿豆汤让她喝了去休息。
“多睡会儿,别玩手机,晚上吃点清淡的就行。”他一边收拾书包,一边叮嘱。
晓晓点点头,窝在沙发里,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
晚饭时,晓晓没吃两口就说想吐,李刚一摸她额头,吓了一跳——烫得厉害。
他赶紧让王芳拿体温计,一量,39.8℃。
“先吃退烧药。”王芳翻开药箱,手忙脚乱,嘴上没说,心里已经慌了。
可药吃下去没两小时,孩子开始吐,脸色白得吓人,眼睛都发直了。
李刚一看不对,抱起孩子就往楼下冲,连外套都顾不上穿。
03
出租车一路狂奔到医院,王芳坐在后座,紧紧搂着晓晓,一手翻手机找病历,嗓子干得发不出声:“她以前没这毛病,身体一直好,感冒都很少……”
医院急诊室人不多,晓晓直接被送进观察室,护士给她挂上点滴,医生做了几项检查,脸色越来越沉。
“建议住院。”医生说,声音很低,“最好尽快转到市儿童医院,这孩子的症状不像普通感染,可能得查查脑部。”
李刚一听腿都软了:“医生,是不是脑炎?会不会是病毒?”
医生没直接答,递来一张住院同意书:“先签字吧,我们马上安排检查。”
接下来的三天像一场没停过的暴风雨,CT、脑电图、血检、基因检测,一项接一项。
王芳和李刚在医院和家之间跑来跑去,每次电话都是“需要补充材料”或“请尽快缴费”。
第四天下午,医生把他们叫进办公室,手里拿着一摞报告,表情不重但也不轻松。
“确诊了,是一种自身免疫引起的神经系统疾病,比较罕见。”医生说,“病因还不清楚,好在发现得早,没扩散,但治疗得马上开始,不能拖。”
“得花多少钱?”李刚问,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前期要用免疫球蛋白和激素治疗,后续可能需要靶向药物,疗程长,保守估计三十五万起步,如果反复,可能得准备一百二十万。”医生说。
李刚脸色刷地白了,身子一晃差点倒下去。
王芳想扶他,还没碰到,他已经顺着墙滑到地上,瘫坐着。
医生想拉他,被他轻轻推开:“没事……我坐会儿。”
他们不是没买保险,可那保单是几年前为贷款买的,保额低,条款多,能报销的几乎没有。
回到家,俩人对着账本坐了半天。
银行卡里不到十万,信用卡三家银行加起来才二十五万额度,平时早透支得差不多了,借呗花呗更别提,连提额都没戏。
李刚拿起手机,翻开通讯录,一页页划,拉下脸开始打电话。
“喂,小张吗?我家孩子生病了,急需点钱,你那儿……”他硬着头皮说。
“哥,我知道你刚买车,可我这边真急……”他又打给一个表哥。
“不好意思。”表哥回了三个字。
李刚没再打,把手机扣在桌上,呆坐了半天。
晚上九点多,晓晓刚睡下,李刚披件薄外套,坐在医院走廊尽头的长椅上。
他一只手攥着衣角,另一只手放在腿上,眼睛红得像熬了夜,盯着地板一动不动。
十点多,王芳刚交完押金回来,手里攥着缴费单。
李刚突然站起来,走到她面前,“扑通”一声跪下了。
“我求你了。”他抬头,眼泪汪汪,“你不是说那股票是咱们的底牌吗?你不是说十年后能救这个家吗?现在我们真撑不下去了,你查查,行不行?”
他声音不大,却像针扎进心窝。
王芳愣了一下,手指攥着单子,指尖发白。
李刚低头,眼泪一滴滴砸在地板上,晕开一片。
她站着没动,几秒后,慢慢点头:“好,我查。”
回家时,天已经蒙蒙亮。
王芳推开书房门,坐到那张用了十年的旧桌子前,拉开抽屉,从最底下摸出一个牛皮纸袋。
里面是当年打印的账户密码,还有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说明纸。
她打开那台七年前的旧笔记本,开机时吱吱响,系统卡得像要喘不过气,屏幕一闪一闪的。
她手心冒汗,捏着那张纸,小心翼翼地铺平,像在摸一件宝贝。
桌面上摊着几张医院的缴费单,每张右上角都印着刺眼的“未付款”。
王芳低头,深吸一口气,屏幕光照在她脸上,显得更苍白——
这一刻,她的人生像是从数字世界,狠狠摔回了现实。
04
等系统启动花的时间比她想的还久,风扇嗡嗡响,像个坏掉的电扇。
屏幕终于亮了,卡得鼠标一顿一顿,她小心打开浏览器,跳出一堆插件报错。
她皱眉关掉提示,转而打开邮箱。
她当年注册了个国外邮箱,专门存那份加密的账户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