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敦煌的女儿”樊锦诗,打算去武汉生孩子,然而领导却不给批假。在敦煌生下孩子后,连衣服都没有。没想到几天后,丈夫给樊锦诗送来了大包小包的衣服和营养品……看到丈夫的那一刻,樊锦诗放声大哭。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麻烦顺手点击一下右上角的「关注」,方便日后随时参与讨论、分享观点,感谢您的支持呀! 那年,30岁的樊锦诗,挺着肚子,已经临近生产,却还在一手握着刷子做着石窟记录,一手翻着堆积如山的档案。 她的丈夫彭金章远在武汉,两口子一年到头见不了几面,只有靠一封封慢得让人捉急的信件来联系。 本来,她打算临产前回武汉,母亲和丈夫都已经在那边准备好床单、孩子的小衣服、月子餐。可没想到,这事却在单位卡了壳。 那天中午,樊锦诗小心翼翼敲开领导的门,轻声说自己临产快到了,想回武汉生孩子。领导头也没抬,嘴里只丢下一句:“生孩子还分哪儿?敦煌不行吗?” 说完便翻下一页纸,不再理会。樊锦诗只能低头退出来,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那一刻,她第一次感到大漠的冷风透进骨头里。 回到宿舍,老旧的土炕上摆着几件褪色的棉衣,都是同事送的。所有给孩子准备的东西早早就寄往武汉——从襁褓、尿布到针线、婴儿奶粉,没有一样在手边。 她只能咬咬牙忍着,想着办法应付眼前的日子。领导还要她去参加农忙,摘棉花。 挺着大肚子弯腰劳作,敦煌的阳光炙烤着她的脸和手臂,脚下满是沙土和干枯的棉秆。 那几天,樊锦诗每晚都睡不安稳,肚子绷得发紧,只能咬着牙坚持。 有时候夜深人静,她一个人缩在小被窝里,摸着隆起的肚子,对着窗外发呆。 风一吹过,窗户咯吱作响,她就想起丈夫彭金章寄来信里说的“等你回来咱们一家人团圆”。 但现实是,她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守着这个冷清的院子,连哭都得等同屋人睡熟了才能抹眼泪。 孩子来得比预产期早些。一天傍晚,樊锦诗腹痛难忍,被同事连夜送到医院。那是一间低矮的平房,简陋得连热水都要现烧。 护士见她孤身一人,忍不住埋怨:“怎么临产了还没人照顾,婴儿的东西都没带吗?” 她哑着嗓子摇头,解释说:“全寄武汉了,原本打算请假回去的。”护士叹了口气,帮她找了些旧布单包孩子。 孩子出生那天,院里下着小雪。樊锦诗看着怀里瘦瘦小小的儿子,心里说不出的酸楚。护士又问她:“你丈夫怎么不在?” 她忍住眼泪,低声说:“他还不知道我生了……”说到这儿,她觉得自己的嗓子像堵着一团棉花。 敦煌当时的物资匮乏得让人难以想象。月子里的饭菜都是稀饭配咸菜,鸡蛋、红糖这些在城市里常见的补品,几乎就是奢侈品。 夜里冷得厉害,孩子没得盖,只能用她自己的棉衣包着,自己则穿着单衣熬夜哄孩子。那几天,她瘦了一大圈,脸色蜡黄,身上没一点力气。 护士心疼她,帮忙拍了电报给武汉的彭金章。电报一出,她就靠在床头,不停地盼着丈夫的消息。 夜里她偷偷掉眼泪,心里头一遍遍地问自己:怎么什么苦都碰上了? 可转念一想,敦煌需要她、莫高窟需要她,自己既然来了,就不能只顾自己。 几天后,医院外传来一阵吵闹,窗外风雪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彭金章披着风尘,扛着一根扁担,两头挂着沉甸甸的包袱,脸冻得发青。 衣服、奶粉、鸡蛋、红糖,还有襁褓小被褥,都是他和母亲早就准备好的。 他一进门,看到妻子瘦得几乎脱了相,孩子裹着棉衣在炕头哼哼,顿时红了眼眶。那一刻,樊锦诗再也忍不住,扑到丈夫怀里放声大哭。 老彭帮着把带来的东西一样样取出来,帮妻子熬了蛋汤,烧了热水,还在墙上钉上钩子,好让樊锦诗挂上婴儿的小衣服。看着丈夫满手冻疮,一路奔波两天两夜赶来,她心疼得直掉眼泪。 在敦煌短短的十几天,彭金章一边照顾妻儿,一边安慰她别太委屈,说:“这孩子小名就叫‘敦敦’吧,咱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段日子。” 孩子满月还没到,彭金章就被单位催着回去。临走时,他叮嘱樊锦诗千万别累着,遇到什么事就写信、拍电报,他一定想办法回来。 那之后的日子里,樊锦诗靠着丈夫带来的温暖,熬过了最难的日子。她有了可以依靠的肩膀,也有了心安的底气。 无论生活怎样艰难,她始终没离开敦煌。多少年后再回忆,她说:“其实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敦煌。但如果没有老彭,我是撑不下去的。” 敦煌的风一吹就是几十年。樊锦诗在大漠里度过了最苦、最孤独的青春,守住了一代代前辈留下的莫高窟,也守住了自己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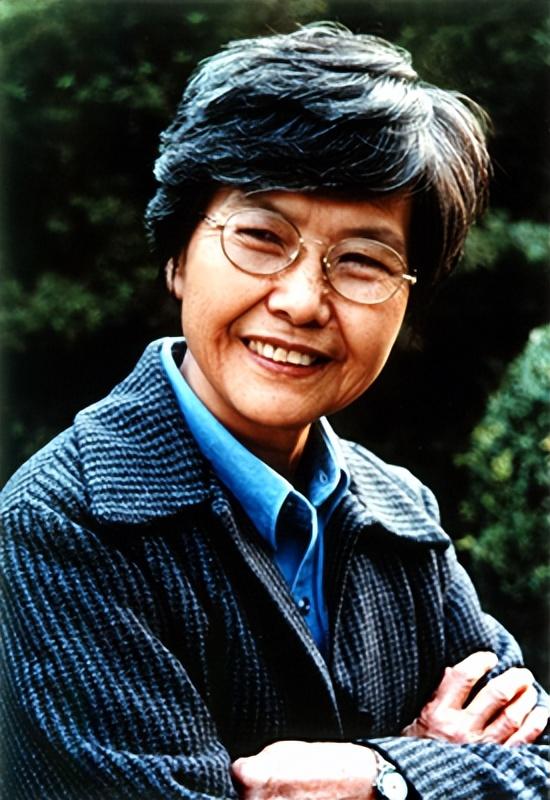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