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新婚六年后,朱惠终于为刘半农生下了一个女儿,刘半农却严肃的说“对外称生了个儿子,让我们的女儿女扮男装。”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16年夏天,江南一个闷热的午后,常州老街的石板路晒得发烫,刘半农坐在书房里,一边擦汗一边修改《新青年》的稿子。 朱惠已经临产,他没有请接生婆,只拜托邻居老太太帮忙,房里静得出奇,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啼哭,老邻居走出来,满头是汗,说:“是个女娃。” 刘半农脸色一下变了,眼神定在窗棂上的光影里,没说一句话,他转过身,对正在忙活洗水的朱惠低声说:“从今天开始,对外说是个男孩。” 朱惠没问为什么,只默默地把准备好的女婴肚兜放进箱子,换上用蓝布缝的小马褂,孩子取名“刘育厚”,“育”是育才,“厚”是做人厚道,不带半点女性痕迹。 六年前的婚礼办得仓促,连请帖都是邻里帮忙写的,刘半农那时刚从杭州回常州,不是为了婚事,而是因为母亲病重,家里说,要“冲喜”,朱惠是做丝绸生意人家的女儿,比他大三岁。 刘半农的父亲刘宝珊不同意,说这门亲事“低了”,可他拗不过病床上的妻子,成亲那天,朱惠穿一身素色长衫,进门时低头不语,跪拜如仪。 婚后头两年,他们住在苏州,日子清贫,朱惠两次流产,第一次是在寒冬打水滑倒,第二次是雨天做饭时晕倒。 这两次都没能保住胎儿,家中来信越发严厉,父亲说香火难续,又提议纳妾,刘半农气得摔了茶盏,他不回信,也不解释,只是辞职离开,带着朱惠搬去上海,靠写文章和做编辑过活。 朱惠身体一直不好,时常头痛失眠,刘半农白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晚上还要下厨熬药,清晨他写白话诗,桌上总放着朱惠做的小针包。 他们在外人眼中总是沉默寡言,一起买菜也少有言语,但邻居说,两人眼神里有东西,像是不肯说破的情意。 朱惠生下“育厚”那天,家里什么都没有,剪脐带的剪刀是在炉上煮过的,襁褓是一块旧布改的,第二天刘半农就出门去邮局,他写信给父亲,只说:“母子平安,”在那个信纸底部,他第一次下意识地写上“厚儿很安静”。 这个秘密从没说出口,却藏在日常的每一个细节里,剪头发只能去男士理发店,朱惠亲手缝的衣服都是对襟,颜色要素,花边不能有。 亲戚来访前,孩子就要提前被送去隔壁邻居家避几天,连最常见的“这是谁家小子啊”这种玩笑话,都必须小心应对。 刘半农知道这套伪装不是长久之计,他曾写下一封信,打算寄给父亲,说清女儿的真实身份,可他终究没寄出去,朱惠什么都没问,只是有一天悄悄把育厚的旧裤子放在窗台上晒,针脚拆了一半,又放下。 1920年,北大通知可以申请出国进修,刘半农立刻报了名,他说是为了学术,其实更多是为了女儿,船到香港转去英国,育厚的护照性别一栏,被划上两条横线。 他们租住在伦敦郊外,每月房租八英镑,屋里潮湿,朱惠常咳得整夜睡不着,刘半农白天在大学教书,晚上翻译《茶花女》,用“她”代替“他”,他说中文不该没有女性的字眼。 有一晚,育厚睡着了,刘半农坐在灯下,看她的额角汗湿,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一句:“教我如何不想她。”那是他第一次用“她”字,第一次写给女儿。 1925年,他们全家回国,住进南京东南大学附近的宿舍,一日家宴,刘半农忽然说:“我来介绍,这是我的女儿,小蕙。” 席间一片寂静,刘宝珊低头不语,半晌放下筷子说:“我老了,耳朵不灵了。”第二天他就回了苏州,寄来一封短信:“此事莫再提。” 那年冬天,小蕙第一次穿上裙子,说冷,朱惠就给她缝了两个暗袋,可以把手放进去,她说这样走路才踏实。 1934年夏天,刘半农因病离世,年仅四十四岁,他的学生说,他去世前握着一本旧笔记,里面夹着一张纸条,上头是当年那句诗:“水面落花慢慢流。”背后写着:“惠卿穿蓝布衫最好看。” 十几年后,“她”字被正式收入《新华字典》,没有人再提那场长达九年的沉默,刘小蕙成了翻译家,讲着几国语言,翻着书页,她常说:“父亲教我读书,也教我活得明白。” 而刘半农给这个国家留下的,不只是一个新字,还有他曾用尽一生试图保护的那个秘密。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刘半农诗歌精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刘半农文集》 央视纪录片《百年巨匠·刘半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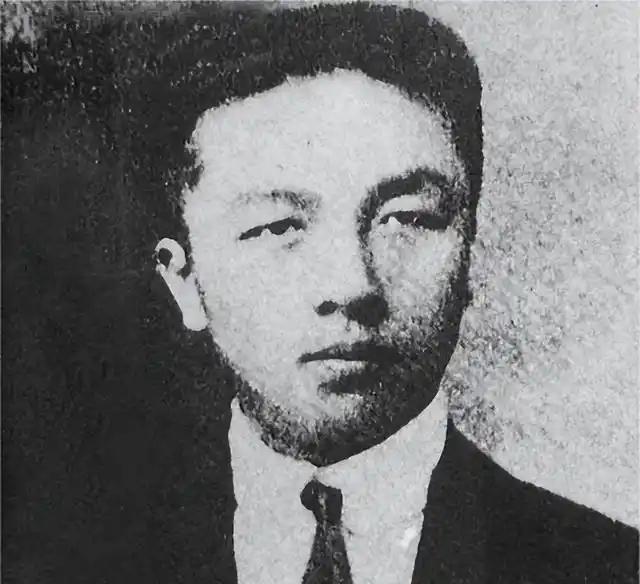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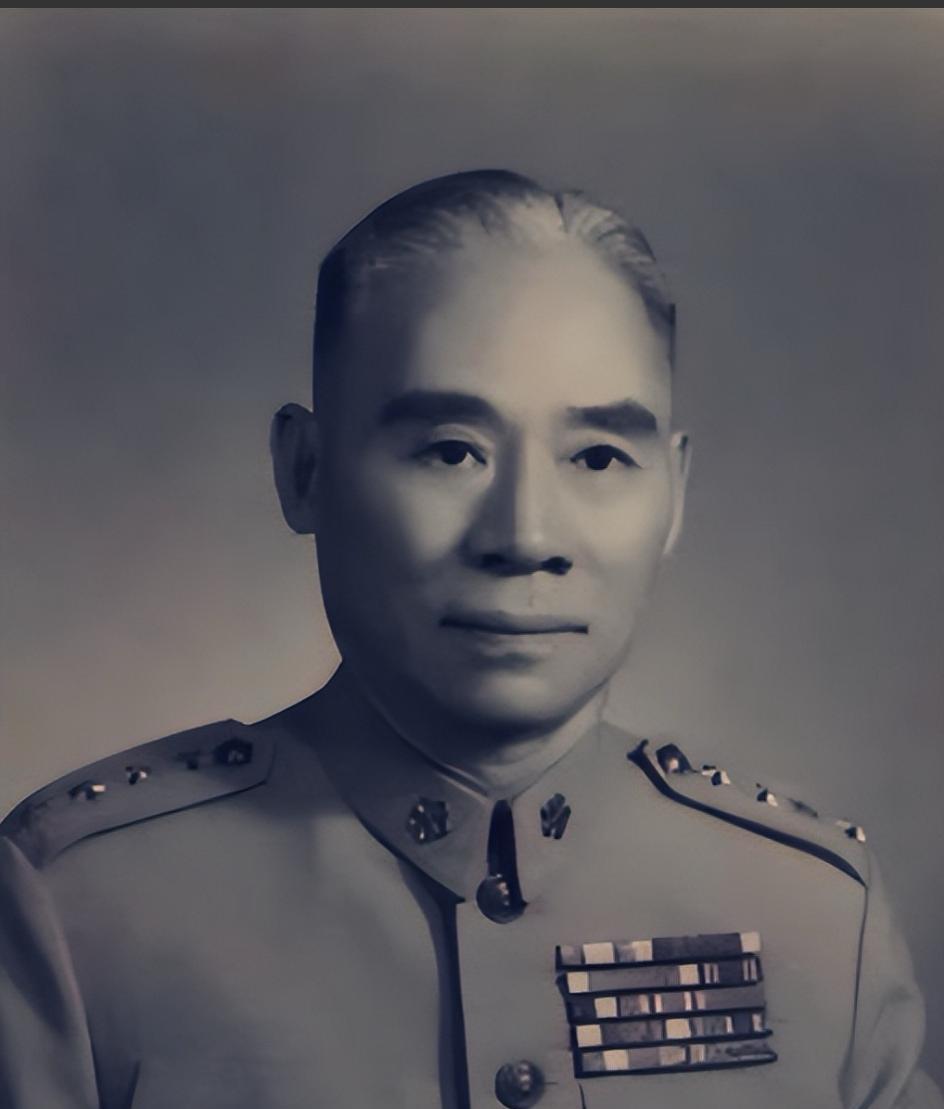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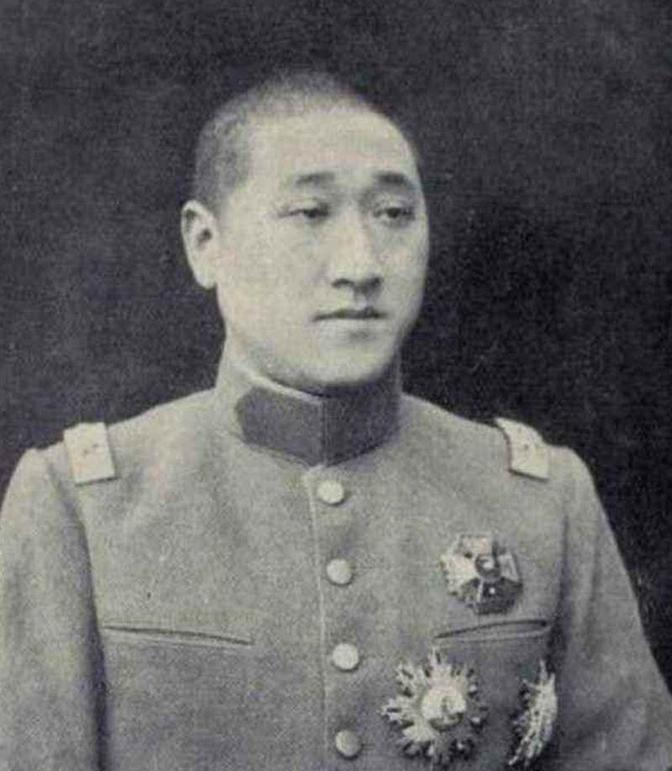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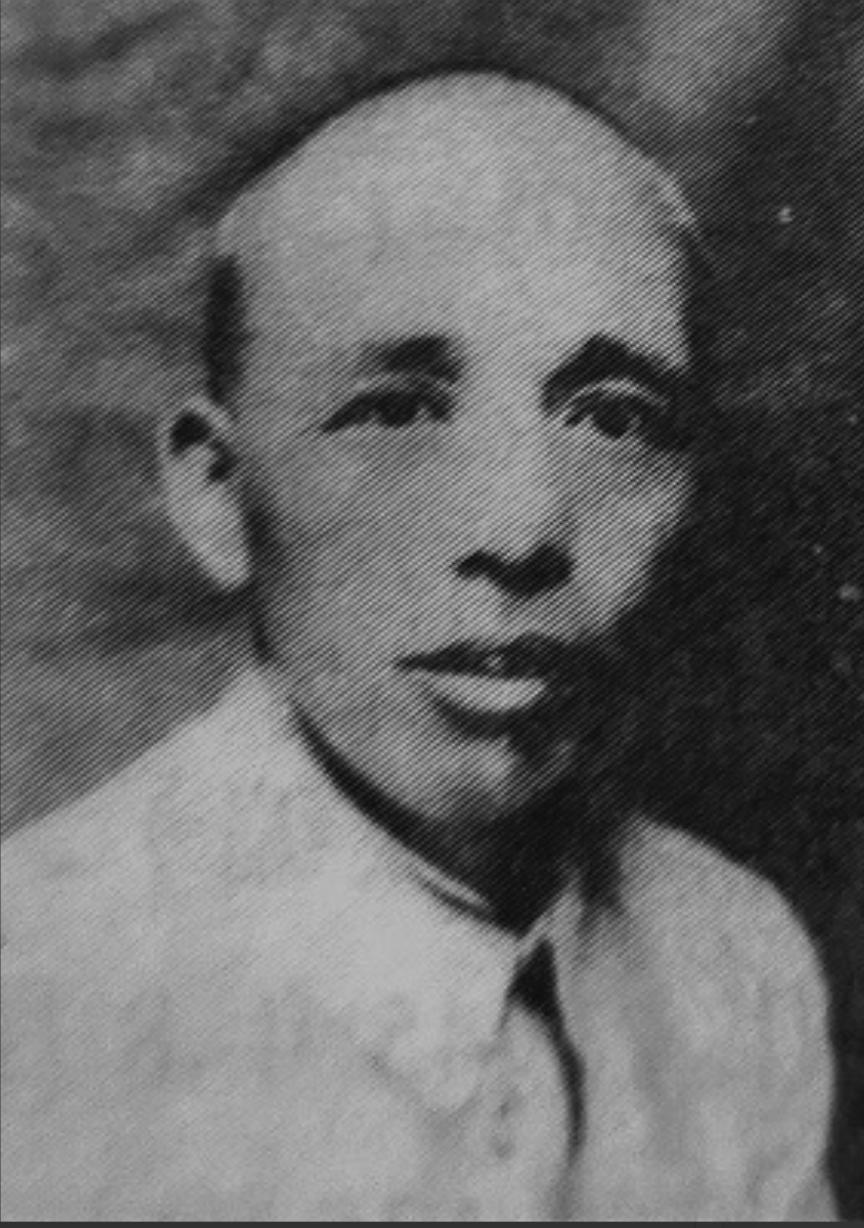


用户10xxx68
为了老父亲的盼孙急切,也为了自己的盼儿之心,更为了保护女儿。❤️🙏🏻
用户10xxx70
怎么不生?生多一、二个肯定有l男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