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盘锦大洼子农场副场长吴成德正带领职工晒粮,突然1辆小车缓缓驶来。1位伟岸的军人快步下车,恭恭敬敬敬礼喊:“老首长,您受苦了。”吴副场长却往外赶人,讲:“你走,你真不该过来啊。”
在那一年,五十六岁的副场长吴成德正握着木锨翻晒麦粒,烈日将他的后背烤得发烫,汗珠顺着晒脱皮的脖颈往下淌。
这位前志愿军团长来农场工作已有七个年头,褪色的劳动布工作服上沾着麦壳,脚上的胶鞋沾满泥巴。
就在这时,农场的东头突然传来汽车引擎声,吴成德眯起眼睛望去,看见辆军绿色吉普车碾过晒场边的土路,车门打开时,他手里的木锨顿住了。
钻出车门的军人肩章上两颗银星晃得人眼晕,正是他十年前带过的兵庞克昌,如今已是正师级干部。
庞克昌迈着标准军步走到晾谷场边缘,冲着弯腰劳作的背影立正敬礼,吴成德没接这个礼,反而抓起草帽扣在头上,转身就要往粮垛后面躲。
庞克昌三步并两步追上去,军靴在麦粒堆里踩出深深的脚印,两个老战友在晃眼的日头底下拉扯,麦场里二十多个职工都停了活计往这边张望。
这事得从更早时候说起,吴成德原是四野老兵,辽沈战役时带着突击队炸过锦州城墙,五四年部队集体转业,他主动报名支援农业建设。
刚到农场那会儿,苏联援助的DT-54拖拉机趴在场院里,全农场没一个人会使,四十多岁的吴成德跟着技术员学挂挡,离合器踩不利索就熄火,折腾半个月终于能开着铁牛犁地。
农忙时节最见真章,三伏天抢收小麦,吴成德带着职工凌晨三点下地,拖拉机大灯劈开夜幕,他坐驾驶座上嚼着冷馒头,车斗里装满捆好的麦子。
有回机器出故障,他钻到车底检修,油污糊了满脸,修好时天边刚泛鱼肚白,场里老会计记得清楚,那季麦子比往年多收了两成。
晾谷场是吴成德最上心的地界,六零年夏天连下七天雨,别的农场麦子都霉了,就大洼子的粮食没事。
吴成德带着人把晒场垫高半米,排水沟挖得四通八达,那天庞克昌找过来时,场上晒的是东北农科所新培育的"辽春一号",麦粒鼓得像小黄豆。
庞克昌这趟来确实冒了风险,当时正值困难时期,部队干部私下看望老同志容易惹闲话,但他听说老首长在农场住的是漏雨土房,每天跟着职工啃窝头,实在坐不住了。
吉普车后备箱里塞着两袋白面,还有条部队特供的"大生产"香烟。
晒场上僵持了足有半根烟工夫,庞克昌硬把白面往吴成德手里塞,老场长急得直跺脚:"快收起来!让大伙瞧见像什么话!"
最后是炊事班长老赵过来打圆场,说场长屋里有新磨的玉米面,非要留庞司令吃饭,那顿饭吃得仓促,吴成德把白面扛回吉普车,只收下包香烟说要分给拖拉机手们提神。
这事后来在场里传成佳话,庞克昌临走前,吴成德从办公室柜底翻出本《农场机械维护手册》,扉页上还留着在部队时的签名。
他把书塞给老部下,说带回去给战士们看看,转业到地方照样能干出个样,吉普车扬起的尘土里,庞克昌攥着那本书,直到后视镜里的人影缩成个小黑点。
转过年来麦收时节,场里突然来了批新农机,庞克昌到底还是变着法帮了老首长——那批联合收割机是军分区淘汰的教练装备,翻修后比手割快三倍。
吴成德没再推辞,带着技术骨干连夜改装机器,秋收时金灿灿的麦浪里,铁家伙轰隆隆开过,惊飞了田埂上成群的麻雀。
往后每年总有那么几回,军绿色吉普车会悄悄停在农场西头的杨树林里,庞克昌再没穿过军装来,倒是常带着农技站的新资料,两个老战友蹲在地头比划庄稼长势,说话声混在拖拉机的轰鸣里,渐渐听不真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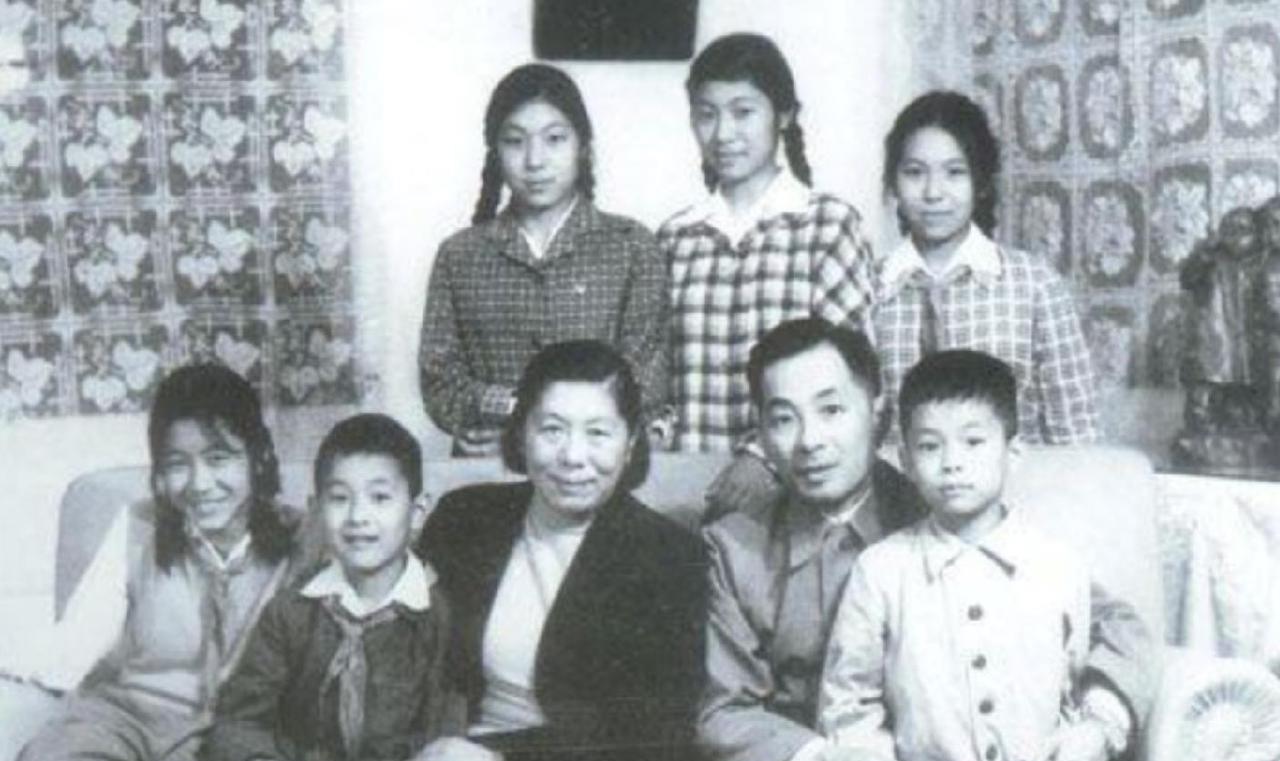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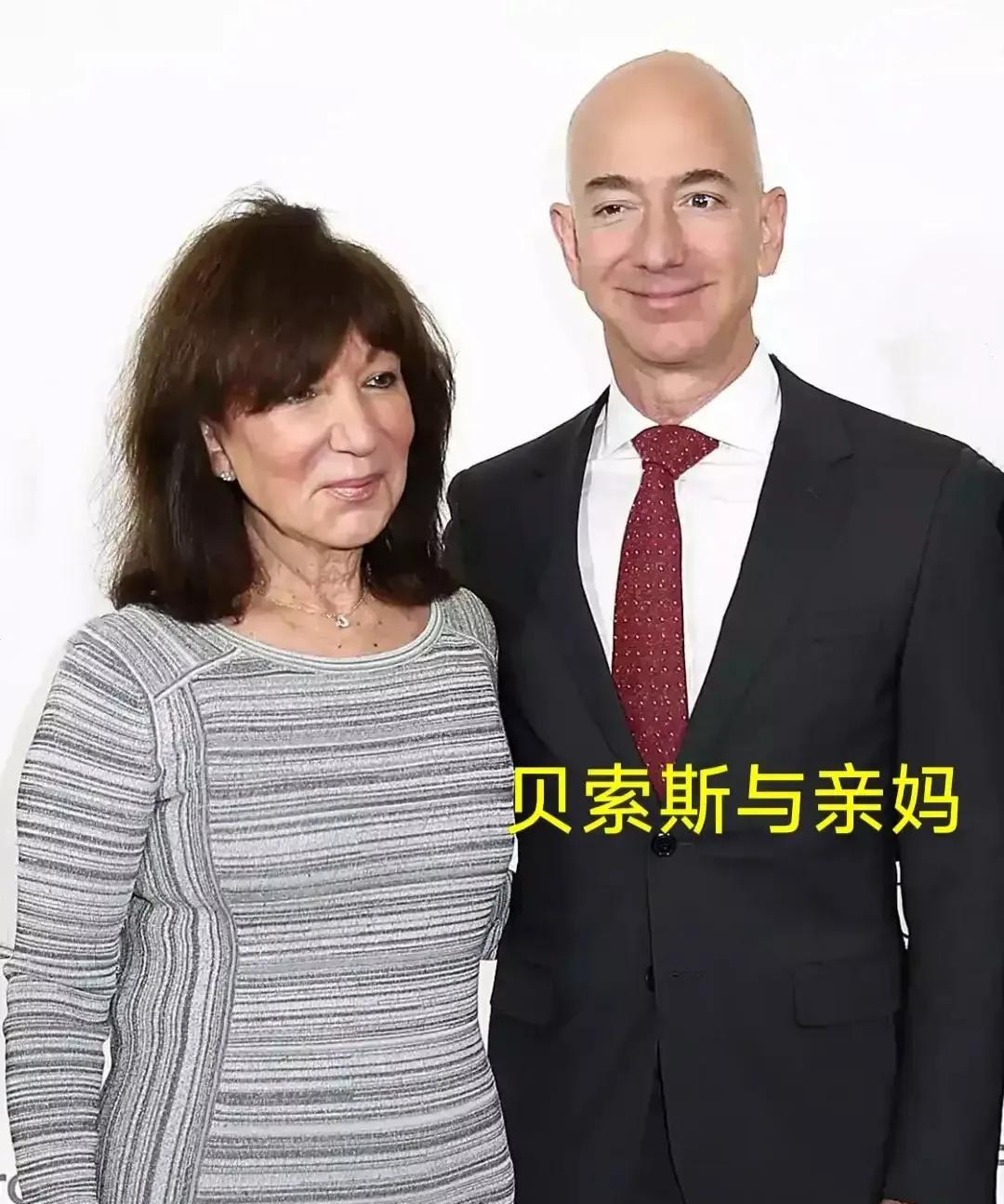







那些浮浮沉沉的往事
共和国脊梁[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