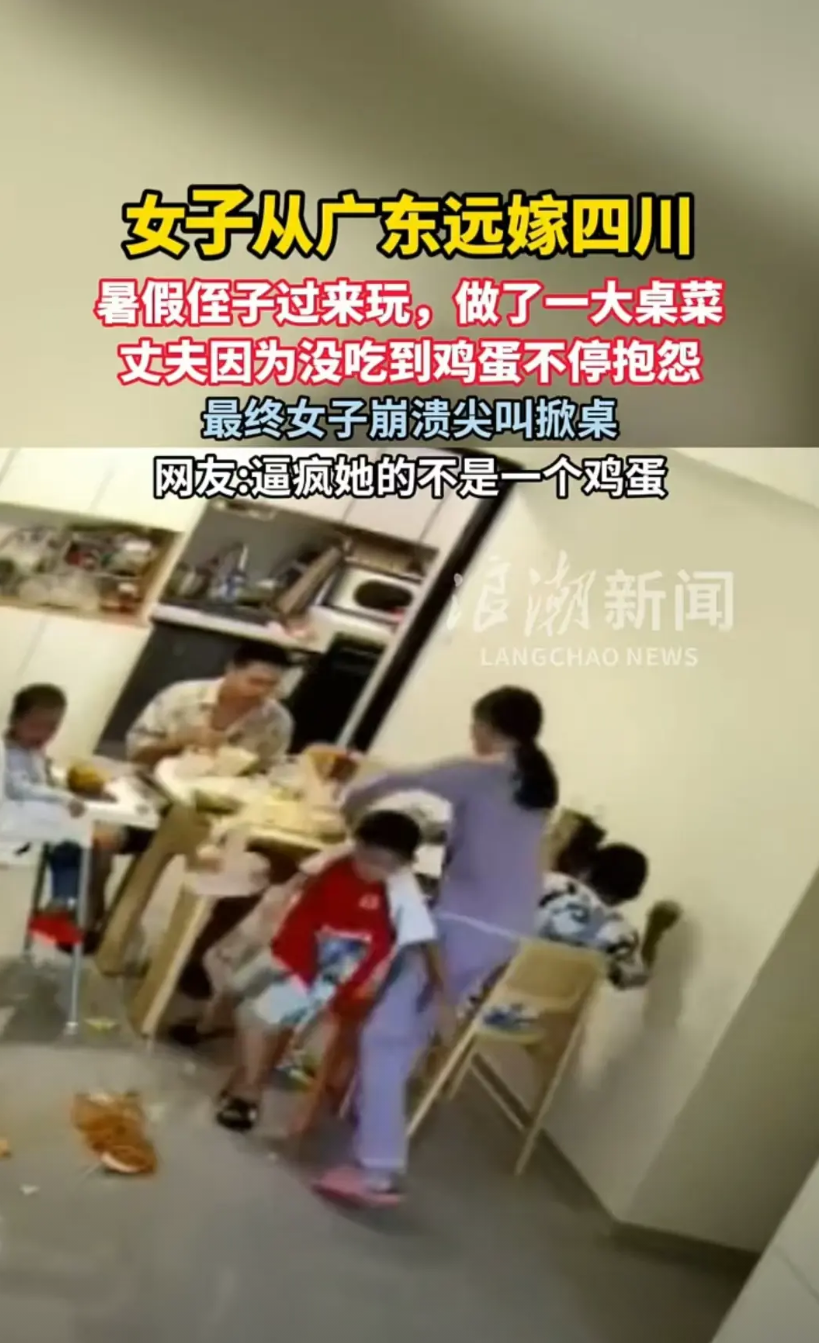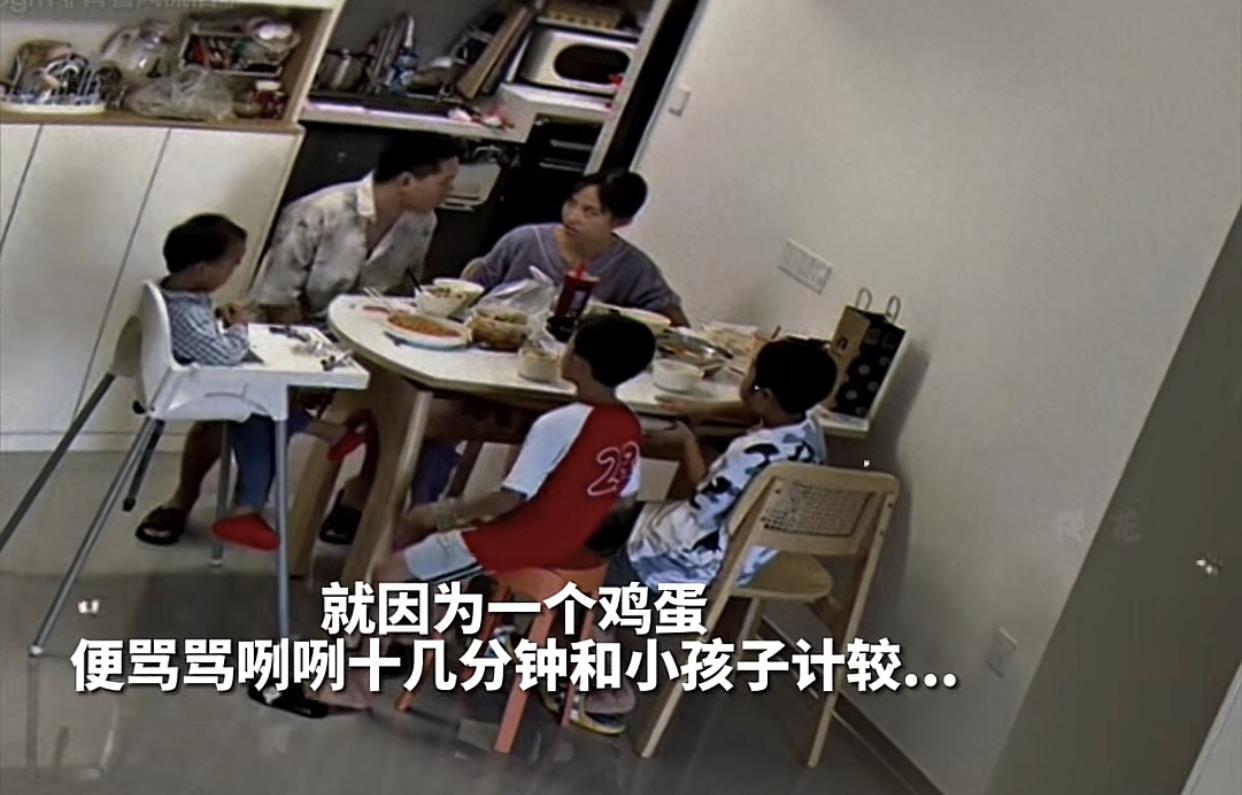我叫杨玉环,老家在四川,爹以前是个小官。小时候日子挺简单,就记得四川那潮湿的风和娘哼的调子,哪想过后来的日子会那么折腾。 开元二十二年,我嫁给了寿王李瑁,成了寿王妃。那段日子挺安稳,王府里春花秋月的,我还以为这辈子就这么过了。谁知道没过几年,皇上让我去当道士,道号“太真”。从王府到道观,像换了个世界,后来才明白,这都是为了进大明宫做铺垫。 进了宫,玄宗对我是真好。给我盖了华清宫,陪着我看遍长安的风景。他知道我喜欢牡丹,就把宫里种满了;知道我爱音乐,就陪我一起弹琴作曲。那会儿我真觉得,这就是最好的日子了。 其实我打小就不是个安分的主儿。在蜀州老家时,总爱跟着爹去赶庙会,看杂耍艺人抛绣球,听茶馆里的先生讲前朝旧事。爹说这丫头“眉梢眼角都是活泛气”,可那会儿我只当是夸我机灵。嫁进寿王府那年,我才十四岁,李瑁比我大五岁,性子温温的,像杯泡开的碧螺春——看着清润,喝到底却没什么滋味。 寿王府的日子确实安稳。每日里除了跟着嬷嬷学女红,就是陪李瑁在花园里赏花。他爱种芙蓉,我偏爱牡丹,两人为这事儿拌过嘴。有回我偷偷在偏院栽了株姚黄,被李瑁发现时正踮脚给花浇水,他站在廊下笑:“环儿,你呀,连种花都要争个高低。”我没理他,末了却把他送的芙蓉枝插在牡丹旁边——倒真成了府里有名的“双绝”。 变故来得突然。开元二十八年,我正在佛堂抄《心经》,小宫女慌慌张张跑进来:“娘娘,皇上身边的高公公来了。”高力士站在廊下,手里捧着道袍,声音像浸了水的棉絮:“贵妃娘娘,皇上请您移驾太真宫。” 那天夜里我在道观里坐了很久。月光透过窗纸洒在蒲团上,我摸着手里的道珠,突然想起李瑁送我的那支珍珠簪子——他总说“环儿戴什么都好看”,可此刻簪子还在妆匣里,人却要换去道袍。后来我才明白,这哪里是修道?不过是给“儿媳变儿媳”的戏码搭个台子。李瑁是寿王,我是寿王妃,若直接入宫,岂不坏了伦理?一道“太真道士”的旨意,便把所有的“不合规矩”都抹得干干净净。 进大明宫那天,玄宗穿着便服在殿门口等我。他比画像里更富态,眼角的皱纹里全是笑:“环儿,可算等到你了。”我低头行礼,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龙涎香,混着点酒气——后来才知道,那是他特意让人配的“百花酿”,就为见我时用。 华清宫的温泉果然名不虚传。我第一次在汤池里泡着,看他让人搬来牡丹,一朵朵插在池边的白玉瓶里。“环儿不是爱牡丹么?”他坐在池边石凳上,剥了颗荔枝递过来,“往后这宫里的牡丹,都随你挑。”荔枝的甜汁沾在我嘴角,他伸手抹去,指腹的温度烫得我心慌——那是我第一次觉得,“不合规矩”原也没什么不好。 我们一起谱过曲子。他爱听我唱蜀地的民歌,我便把在老家学的《竹枝词》改了又改。有回谱到“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他突然握住我的手:“环儿,这词好,像极了我们。”我没敢接话——我们的“青梅竹马”,不过是他五十岁时,我十七岁的开始。 可再浓的情,也熬不过岁月的褶皱。天宝四年,我正式成了贵妃。那天的册封礼极尽奢华,百官跪伏,礼乐喧天。我穿着翟衣,头戴金钗,看着阶下的李瑁——他已经搬去了东宫,见到我时眼神空洞洞的,像在看个陌生人。我突然想起在寿王府栽的那株姚黄,不知被谁移走了,还是枯死了? 玄宗的爱是真的。他会为我去南海捕珍珠,会在我生辰时命工匠造千叶牡丹,会在我咳疾发作时守在床边熬药。可他的爱里,总掺着些别的东西。他爱看我在梨园跳舞,便命人修了长生殿;我爱吃荔枝,他便让人从涪陵快马加鞭送来,“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民谣传遍长安时,他摸着我的头笑:“环儿,你瞧,这天下都是为你闹的。” 可天下哪有白闹的?李林甫死了,杨国忠当了宰相,朝堂上的风气越来越浑。安禄山那胡儿,在范阳招兵买马,玄宗却总说“禄儿是我义子,必不相负”。我劝过他,他摸着我的脸说:“环儿莫忧,朕有的是本事。”那时我只当他自信,后来才懂,他是被多年来的顺境蒙了眼。 天宝十四载冬,渔阳鼙鼓动地来。我在华清宫泡汤时,听见外面的士兵喊杀声。玄宗攥着我的手,指甲几乎掐进肉里:“环儿,随朕去蜀州,我们回当年相遇的地方……”我望着他鬓角的白发,突然想起十七岁那年在寿王府,他蹲在池边给我系鞋带的样子。那时候他的手多暖啊,不像现在,凉得像块玉。 马嵬坡的月亮特别圆。士兵们的刀枪映着血光,陈玄礼跪在地上:“贼本尚在,六军不发!”玄宗颤抖着解下我的香囊,塞进我手里:“环儿,委屈你了。”白绫绕上脖子的那一刻,我闻到了熟悉的龙涎香——原来有些爱,从一开始就带着权力的锈味,像华清宫的温泉,泡得再久,终究是凉的。 后来有人说我是“祸水”,说安史之乱都是我害的。可我知道,那锅太大,我一个人担不起。 注:本文情节参考《旧唐书·后妃传》《资治通鉴·唐纪》《开元天宝遗事》等史料记载,人物心理及部分细节为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