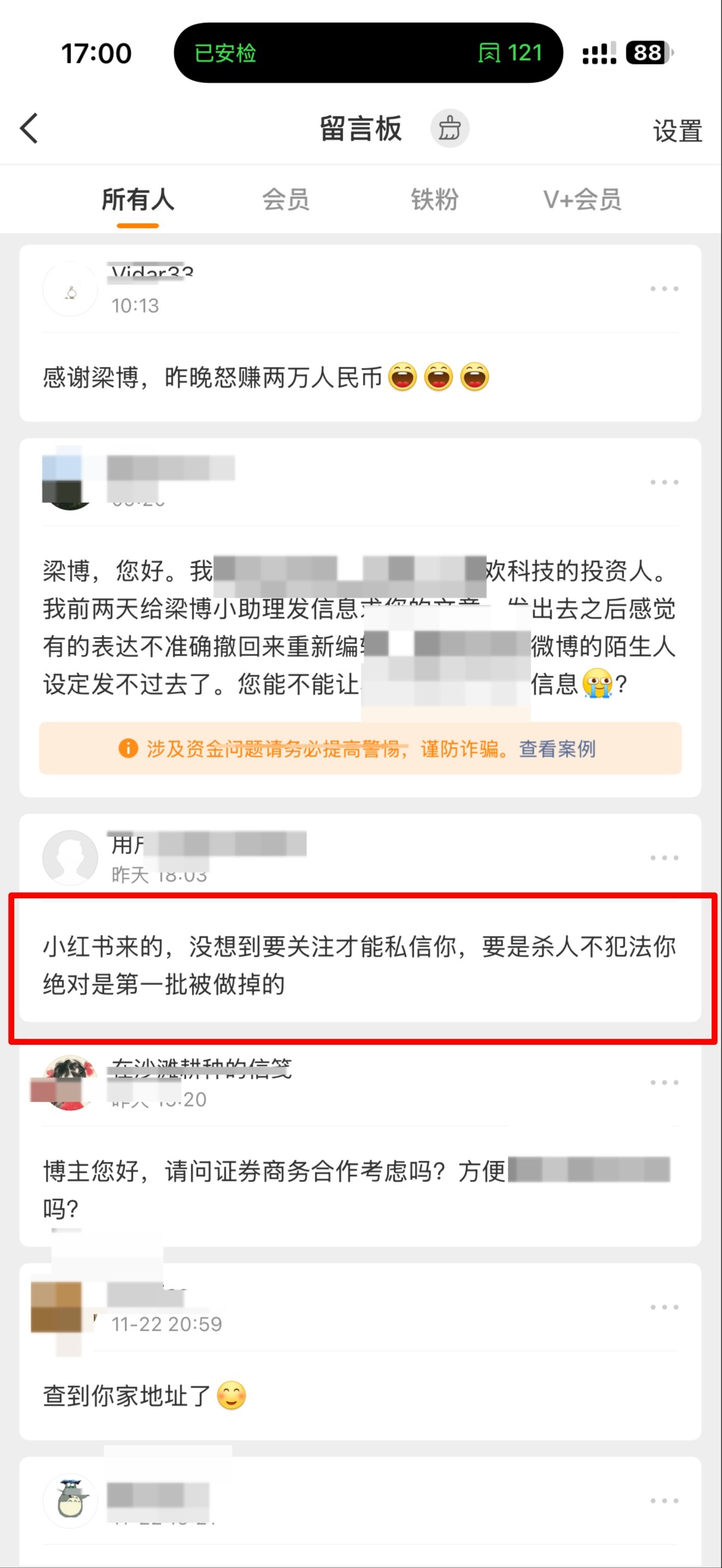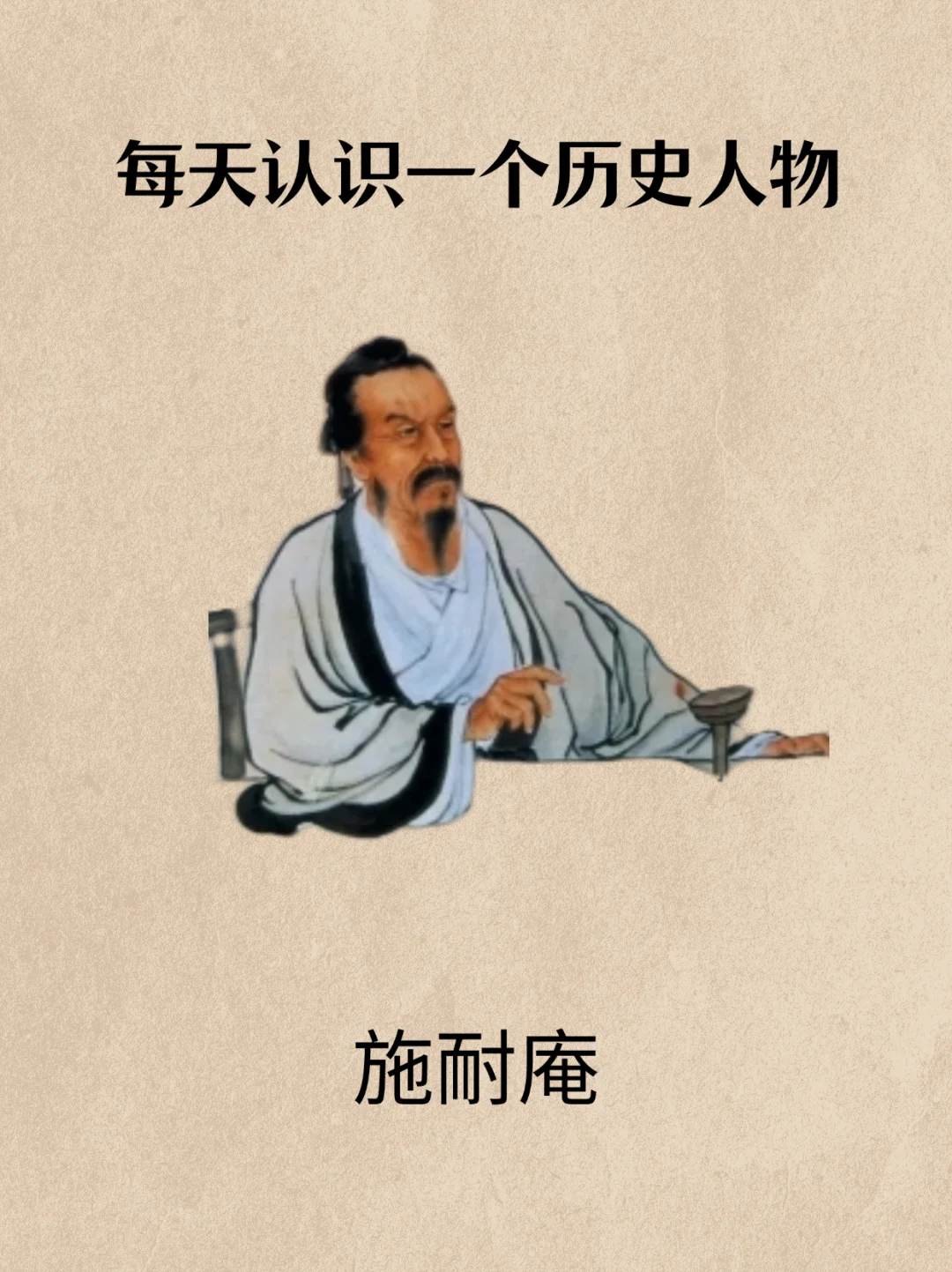78年,我娶了个成分不好的地主女儿,洞房夜,她主动得很,可第二天一早,我就在她枕头底下摸出一双绣花鞋。那鞋塞在枕头芯子里,我铺床时摸到个硬疙瘩,掏出来一看,是双小孩穿的虎头鞋,只有巴掌大,红缎面绣着金线,虎眼睛用黑珠子缀的,鞋底纳得密实,却已经发黄发脆了。我捏着鞋愣了神,里屋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她撩开门帘出来,头发还散着,看见我手里的东西,整个人僵在门槛上。 那年头“成分”是道坎,媒人说她前头嫁过,男人没了,村里人嚼舌根说她“克夫”,我当时只当是闲话——直到看见她攥着裤腿下跪时,手背上裂开的冻疮正往下滴黄水。 “孩子刚满周岁,发疹子烧得小脸通红。”她指甲掐进我胳膊,声音抖得像筛糠,“破庙里没药,我抱着他走了三里地,赶到公社卫生院时,小身子已经凉透了——这鞋,是他头回学走路时,他爹连夜纳的。” 炕桌上的小米粥熬得黏糊,热气熏得人眼睛发酸。我摸了摸虎头鞋底那圈模糊的小脚印,突然想起她昨晚给我铺床时,手指在我胳膊上打滑——原是冻僵了。 谁说地主家的闺女就该金贵?她连夜给虎头鞋缝匣子时,针脚歪歪扭扭,扎得指腹冒血珠,倒像是怕碰碎了啥宝贝。村里老人说她命硬,克死男人和娃,可我瞅着她咳得直不起腰时,还攥着虎头鞋不撒手,倒像是攥着活下去的念想。 开春前她犯了回咳病,夜里总抱着我棉袄不撒手。后来才发现,她把虎头鞋拆了线头,缝在棉袄左襟夹层里,针脚密得能数出三十多下,“这样,孩子就跟着爹暖和。” 入夏时她显怀了,夜里坐在炕沿给孩子做鞋,金线在煤油灯底下晃,她说要绣双鸳鸯的,“这回得让娃踩着爹娘的福气长大。”我蹲在灶台边添柴,听她哼着不成调的曲子,灶膛里的火星子噼啪响,倒比啥都热闹。 如今棉袄还压在箱底,虎头鞋的红缎面褪成了粉白,可那小脚印总在我眼前晃。当年觉得“地主女儿”四个字像块石头压着,如今倒觉得,她和咱庄稼人一样,心里头揣着的,不过是个暖乎乎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