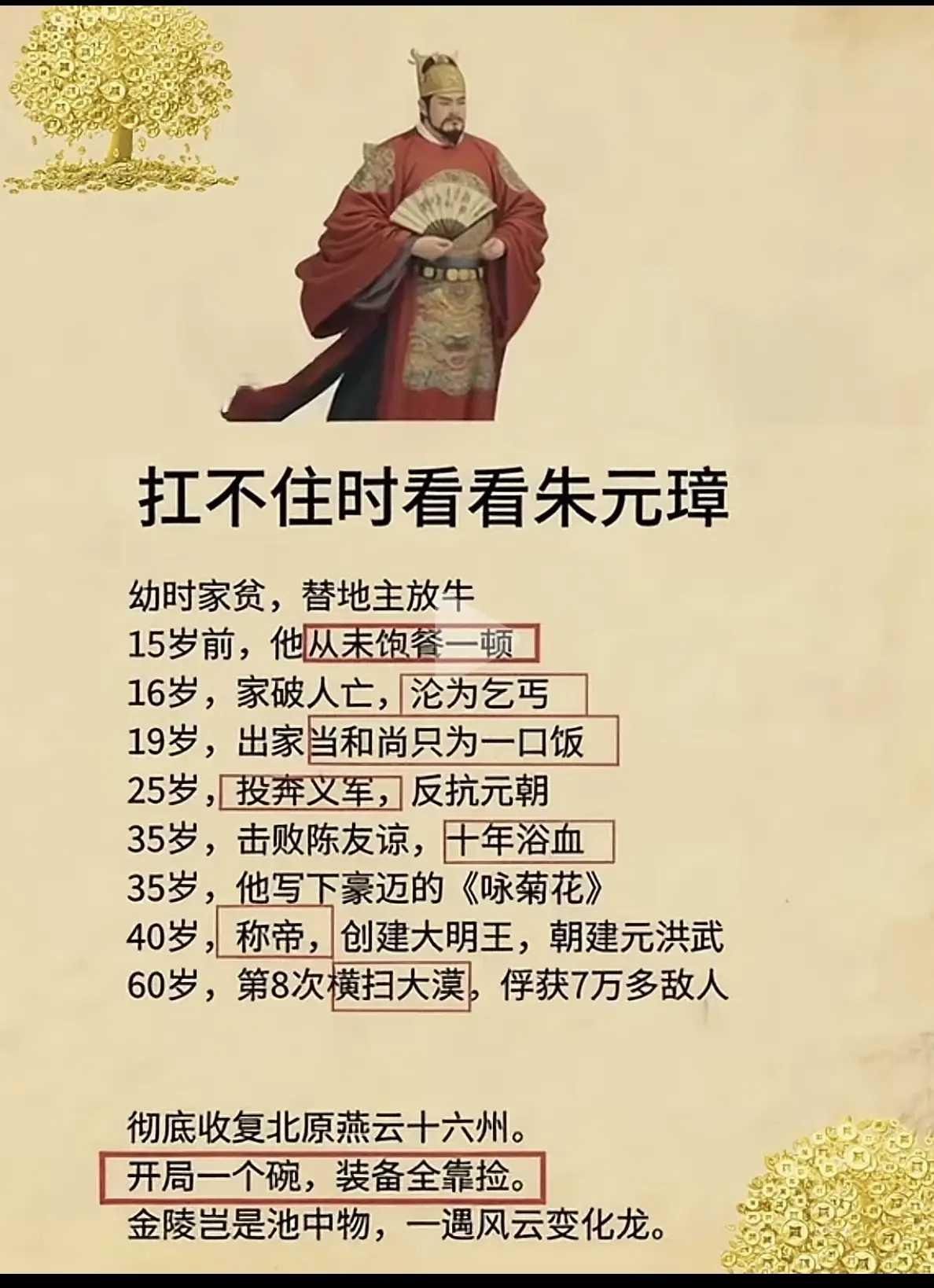宝应元年四月甲寅日的夜里,七十八岁的太上皇李隆基在太极宫的神龙殿内,已整整七日水米未进。
宫人们说,这位曾经将大唐推向开元盛世的老人,是在“辟谷修行”。
这话大约连说的人自己也不信,可在这长安城里,不信的话若说得多了,便也成了真理。
当晚,李隆基被活活饿死。
十三天后,他的儿子,当今皇帝李亨,在华清宫的长生殿内,受惊而薨。
父子二人,一个饿死,一个吓死,竟像是约好了似的,要去阴曹地府继续那场未完的棋局。

这棋局的开局,得从开元末年的血色说起。
那年李亨二十七岁,刚被立为太子,站在东宫的廊下,望着远处大明宫的方向。他忽然懂得了一个道理:在这座长安城里,父子之情是有价的,而那价码,便是龙椅。
他的父亲,那位被天下人歌功颂德的明君李隆基,曾在一年前,赐死了三个儿子——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
罪名是“谋反”,可长安的百姓私底下都在传,不过是武惠妃想要自己的儿子李瑁做太子,枕边风吹得狠了些,那位圣明的天子便提笔一挥,三条性命就此了结。
李亨的生母元献皇后杨氏,出自弘农望族,却在他年幼时便已撒手人寰。
他自幼被王皇后养在膝下,那是个温柔的女人,却也是个可怜的女人。她无子,便将所有心血都倾注在这孩子身上,教他读书识字,教他明白宫墙里的生存法则。
可那法则,原就是吃人的,连王皇后自己都难以幸免。
开元十二年,她因“符厌之事”被废,关在冷宫里,三个月后,无声无息地死了。
李亨那年十三岁,站在冷宫的门外,听着里面传来的阵阵咳嗽声,他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做“帝王无情”。那养育他多年的妇人,临死前连他的面都不得见。
他忽然懂了,这皇宫里,所有的温情都是暂时的,唯有权力是永恒的。父亲可以杀儿子,丈夫可以杀妻子,这世上最亲近的人,转眼间便能成为刀下鬼。
他看着那些宫人麻木的脸,看着他们在废后门前匆匆而过,连头都不曾回一下,他便知道,自己这一生,注定要在刀尖上行走。

他原来叫李嗣升,后来改名李浚,再后来又叫李绍,最后才叫李亨。这名字的屡次更改,仿佛预兆着他身份的飘忽不定。
他本不是嫡子,母亲又早逝,按说这太子之位,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
可天意弄人,武惠妃费尽心机除掉李瑛后,她的儿子李瑁却没能如愿入主东宫。
李隆基或许是杀子杀得累了,或许是在夜里曾被噩梦惊醒,竟将太子之位给了这个向来不起眼的儿子。
李亨接到诏书的那天,没有喜色,只有恐惧。他跪在大明宫的丹墀之下,额头触着冰冷的地面,他听得见自己的心跳,也听得见远处传来的丧乐——那是给他三位兄长的。他成了太子,却也成了靶子。
东宫的日子,比冷宫好不了多少。他每日如履薄冰,不敢信任任何人,连枕边人都不敢。
他的第一位太子妃韦氏,原也是个温婉的女子,与他育有一子。可天宝五年,韦坚案发。韦坚是韦妃的兄长,时任刑部尚书,因与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交好,被李林甫构陷,说是要拥立太子逼宫。
这罪名,原就是莫须有的。可李隆基震怒之下,李亨为求自保,被迫上表,称与韦妃“情义不睦”,请求离婚以绝牵连。
韦妃为保太子,亦劝其割爱,削发为尼,青灯古佛,了此残生。李亨站在东宫的角楼上,望着她远去的背影,那双曾经温柔的眼睛,从此结了一层冰。
他很快又有了第二位良娣,杜氏。这也是个可怜的女子,父亲杜有邻,官不过小小赞善大夫。可李林甫的手,终究还是伸了过来。
天宝六年,杜有邻被诬告“妄称图谶,交构东宫”,下狱拷问,杖杀于公堂。杜良娣被迁出东宫,不久便忧愤而殁。李亨再次承受这割爱之痛,却连哀戚之色都不敢流露分毫。
两次被迫弃妻,李亨终于懂得,自己这个太子,原就不是什么储君,而是一个人质,一个随时可以被替换、被牺牲的人质。他的父亲,要用这种方式告诉他:你的命运,在我手里;你身边的人,也全在我手里。
那些年,长安城的天,总是灰的。李亨走在路上,连宫人太监的咳嗽声,都能让他惊出一身冷汗。
他不敢结交朝臣,不敢联络武将,甚至连自己的东宫属官,都要刻意疏远。
他每日里只读书,读那些圣人教诲,读得越多,心里越凉。
圣人教人父慈子孝,可他的父亲,却在一日之内杀了三个儿子;圣人教人仁义礼智,可宰相李林甫,却在朝堂上构陷忠良,无人敢言。
他又懂了,这圣人书,原就是写给外人看的,真正的皇宫里,只有弱肉强食。

他看着镜中的自己,不过三十来岁,却已两鬓斑白。长安的百姓都在传,太子因忠孝而白头,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白色,是恐惧的颜色,是绝望的颜色。
转机来得猝不及防。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起兵反唐,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了霓裳羽衣曲。
曾经在唐隆政变中杀伐果敢的李隆基,如今却也不过是一个沉迷女色的老皇帝,他慌了手脚,仓皇西逃,带着贵妃,带着杨国忠,带着满朝文武,也带着太子李亨。
然而行至马嵬驿,禁军哗变,杨国忠伏诛,杨贵妃被缢死,父子二人之间最后那层温情的面纱,也被撕得粉碎。
李亨站在变乱的废墟之中,听着远处传来的军士呐喊,忽然笑了。那笑声凄厉,比哭还难听。
这个做了十八年囚徒的太子,在这一刻,终于生出了决断的勇气。
他没有随父皇南入蜀地,而是分道扬镳,北上灵武,在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支持下,干脆利落地登基称帝,遥尊他的父亲为太上皇。
这是他四十年来,第一次对父亲说“不”。
那声“不”,喊得并不响亮,甚至有些颤抖,可它终究是被喊了出来,响彻了那个乱世。
那位太上皇,初闻消息,虽感意外,却也未敢公然发作。
他在蜀中下旨令永王李璘领兵东巡,其用意,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不过是要牵制灵武的新帝,甚至在适当时机,废了这不听话的儿子。
可李亨,此时已有了自己的力量。
他迅速平定永王之乱,将父亲最后的反扑,扼杀在摇篮里。
至德二年,长安收复,他派使者去蜀中,恭恭敬敬请太上皇还京。那姿态,做得十足十的孝顺,可骨子里的意思,谁都明白:您老了,该回来养老了。

玄宗回了长安,住进了兴庆宫,原是他在位时的旧居。高力士、陈玄礼等旧臣陪在身边,倒也还算体面。可这样的体面,在李亨看来,终究是根刺。
兴庆宫离市井太近,太上皇每日在楼上观望,百姓见了,还要跪拜,还要山呼万岁。那呼声,听在李亨耳中,比叛军的战鼓还要惊心。
他做了十八年太子,深知权力的味道,一旦尝过,便再也放不下了。
他的父亲,虽然现在老了,可只要有一口气在,便是一面旗帜,那些不臣之心的人,随时可以打着这面旗帜作乱。李亨不能冒这个险,他冒了十八年的险,已经冒够了。
于是,便有了那出迁居的闹剧。宦官李辅国,那个在灵武有功的阉人,揣度着皇帝的心思,上奏说:“太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等日夜谋划,恐有复辟之危。”
李亨闻言,泣曰:“圣皇慈仁,岂容有此!”
可李辅国早已看透皇帝未尽之言。他矫称上命,先以敕书取兴庆宫厩马三百匹,止留十匹;七月,更带兵将玄宗从兴庆宫“请”到了太极宫。说是“请”,却有数百骑执刃夹道,如临大敌。
玄宗坐在步辇上,望着自己住了两年的兴庆宫越来越远,他忽然问李辅国:“朕为太上皇,何至于此?”
李辅国面无表情地回答:“陛下为天子父,自当居太极宫,以全陛下清修之心。”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可玄宗明白,自己从此便是笼中鸟、池中鱼了。
太极宫比兴庆宫更加辉宏,却远离街市。他的旧人高力士被流放巫州、陈玄礼被勒令致仕。他身边的,都是些新面孔,个个木然,个个沉默。
他懂,自己的儿子,那个曾经跪在自己面前叩头出血的太子,如今用着他当年用过的手段,将权力收得滴水不漏。
李亨自然是知道这一切的。他住在遥远的大明宫里,听着李辅国的汇报,听着太上皇的近况,他沉默着,不置一词。
他不是不想管,而是不能管。他太了解自己这个父亲了,也太了解权力了。他用了十八年的时间,才从太子熬成皇帝,他不能再冒任何风险。
他记得韦妃被逐时的眼泪,记得杜良娣被迁时的绝望,记得自己白头时的恐惧。
那些记忆,像一把把刀,夜夜割着他的心。他告诉自己,这不是狠心,这是自保,是为大唐的江山社稷。
可夜深人静时,他也会问自己:这江山,这社稷,是不是一定要用父亲的血来祭奠?

太上皇的身体,便是在这样的孤寂中,一日日垮下来的。他不再说话,不再走动,每日里只坐在窗前,望着那十匹老马在院子里吃草。他不再进食,宫人送来的御膳,原封不动地端回去。
起初,宫人们还劝他,说是“龙体要紧”,可他不理,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后来,宫人们也懒得劝了,只是将膳食放在门口,过几个时辰再端走。
李亨听闻此事,对群臣说:“太上皇年高,欲效仿先贤辟谷修行,以求长生。朕虽不忍,亦不敢违逆父皇心意。”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可殿下的臣子们,个个低头不语。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见过当年玄宗如何一日杀三子的,也见过李亨如何白头度日的。他们明白,这父子之间的债,终究是要用血来还的。
辟谷到第七日,太上皇已说不出话来。他躺在床上,眼前浮现的,却是被自己赐死的三个儿子。
他也懂了,自己这一生,杀子、废后、失国,到头来,竟是被自己的儿子,用同样的方法,关在这座黄金的牢笼里。
甲寅日,太上皇驾崩。
消息传到李亨耳中,他正病着,听到报信,只是点了点头,说:“知道了,按礼制安葬罢。”
他脸上没有悲伤,也没有释然,只有一片麻木。
十三天后,张皇后政变,李亨本就病着,这一惊,便直接一命呜呼。
这个做了十八年惊弓之鸟的太子,终究也没能逃脱“惊”这个字!
这便是李唐皇室的父子。不是他们生来无情,而是那龙椅,那玉玺,那九鼎,原就是用血肉浇筑的。
唐玄宗李隆基,一日杀三子,做得绝;唐肃宗李亨,默许父亲饿死,做得狠。
可他们若不那般绝、那般狠,死的便是自己。这便是历史的悲剧,也是人性的悲剧。
我们站在千年之后,看那太极宫的秋霜,看那大明宫的夜雨,或许可以轻飘飘地说一句:何至于此?
可若将我们放在那龙椅之上,放在那东宫之中,我们便能保证自己,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
皇权这物,最是无情。它不许你有亲情,不许你有软弱,不许你有半点人的温度。你要坐稳了,便得将自己磨成一把刀,磨得锋锐,磨得冰冷。
李隆基磨成了刀,杀了儿子;李亨磨成了刀,逼死了父亲。他们本是血肉之躯,却被那龙椅榨干了最后一滴人味儿。
可我们又能怪谁?怪制度吗?那制度原就是人制定的。
怪人性吗?人性在权力面前,原就是不堪一击的。
这便是个死局,千百年来的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