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7年秋,李世民大婚,名相袁天罡受邀赴宴。
瞥见红盖头下的长孙氏侧影,他猛然警觉,急告李渊:
“此女母仪天下,非后不可。”
稍顿,声更低涩:“秦王…亦具真龙天命,非帝不可。”
李渊望向正与宾客谈笑的次子,又瞥见帷后新妇隐约的身形。
曾引以为傲的麒麟儿,此刻竟成了心头最尖锐的刺。
01
公元617年的秋天,晋阳宫内张灯结彩,鼓乐声穿透了动荡的时局。
唐王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在这一天迎娶长孙氏,满堂宾客的祝贺声中弥漫着乱世里难得的喜庆。
李渊坐在主位频频举杯,目光扫过英气勃发的儿子和端庄秀丽的新妇,心底满是家族兴旺的骄傲。
酒宴正酣时,相师袁天罡的青布身影出现在殿门外,李渊大笑着亲自起身迎接这位以相术闻名的奇人。
袁天罡微笑着回礼,视线却在不经意间落到披着红盖头的长孙氏身上。
他的笑容突然凝固,仿佛被无形的力量击中般微微一颤,眼底翻涌起震惊的骇然。
“天纲先生为何这般神情?”李渊敏锐地察觉到异样,脸上的笑容淡了几分。
袁天罡深吸一口气,压低声音请求借一步说话,两人便一前一后走进了安静的偏殿。
“唐王恕我直言。”袁天罡的脸色依然苍白,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方才观秦王妃面相,乃是坤载万物母仪天下之相,此女将来非皇后不可。”
李渊先是一愣,随即开怀大笑起来,仿佛听到了最吉利的祝福。
然而袁天罡接下来的话让他的笑声戛然而止。
“秦王妃为后,那秦王……”袁天罡艰涩地吐出字句,“秦王殿下龙睛凤颈,日角龙颜,是真龙天子之相,他也非皇帝不可。”
李渊踉跄着扶住身旁的立柱,脑海中仿佛有惊雷炸响。
他的儿子会是皇帝?那他自己又该置身何处?
偏殿陷入死寂,李渊的胸膛剧烈起伏,眼神从惊骇逐渐转为阴沉的猜忌。
他想起了李世民在军中的赫赫战功,想起了将领们对儿子的狂热拥戴,这些曾让他骄傲的资本此刻都变成了扎心的刺。
“先生此话可有破解之法?”李渊沙哑的声音里透出毫不掩饰的杀意。
袁天罡吓得跪倒在地连连叩首,颤抖着说天命非人力所能更改。
李渊没有再看他,只是冷冷地拂袖而去,扔下一句“我只信我手中的刀”。
当他重回宴会时,脸上又挂起了热情的笑容,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
只有李世民隐约察觉到父亲眼底多了一缕陌生的冰冷。
02
夜色渐深,秦王府新房里的红烛将温暖的光晕洒满房间。
李世民轻轻揭开长孙氏的红盖头,烛光下新娘姣好的容颜染着羞涩的红晕。
两人起初都有些拘谨,毕竟这婚事更多是家族联姻的安排。
“殿下今日辛苦了。”长孙氏轻柔的声音打破了静谧。
“往后唤我二郎便好。”李世民露出温和的笑容,递过一杯热茶。
长孙氏轻声应了句“二郎”,低头时耳垂微微发红,她自幼便听过这位少年英雄的传奇,此刻心中既有新婚的羞怯也有隐约的欣喜。
他们从诗词聊到时局,李世民惊讶地发现这位新妇不仅温婉,对天下大势更有独到的见解。
原本的陌生感在交谈中渐渐消融,李世民心底涌起娶得贤内助的欣慰。
“如今父亲起兵,前路坎坷,嫁与我恐怕要让你受苦了。”李世民握着她的手说道。
长孙氏抬起清澈的眼眸,认真地看向他:“大丈夫当建功立业,我既嫁与你,无论坦途荆棘都愿一同分担。”
她的话语像暖流淌过李世民的心田,他郑重地点头承诺。
然而他们都不知道,此刻唐王府书房里的气氛压抑得如同暴风雨前的死寂。
李渊独自在房中踱步,袁天罡的预言像毒刺反复搅动他的心神。
他无法接受自己打下的江山将来要拱手让给儿子,更无法容忍身边睡着如此可怕的威胁。
“玄真,你说这世上真有天命吗?”李渊对着进来的谋士裴寂突然发问。
裴寂谨慎地回答天命不过是人心所向,李渊冷笑着将袁天罡的预言和盘托出。
裴寂听完脸色大变,立刻跪地劝道此事万万不可轻信。
“我不能拿李家的未来去赌。”李渊的眼神变得决绝,“世民才能太盛威望太高,如今又有这预言,我不能再等了。”
裴寂看着主公眼中不容更改的杀意,知道再劝无益,只能沉默地低下头。
李渊望向窗外秦王府的方向,声音在夜色里显得格外阴森:“既然天要亡我,那我就先逆了这天。”
03
第二日天未亮,秦王府就接到李渊的紧急传召。
长孙氏为李世民整理朝服时柔声叮嘱要小心行事,李世民笑着宽慰她,心底却隐隐觉得不安。
议事厅里除了李渊,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也在场,所有人的表情都异常凝重。
“世民,你可知罪?”李渊面无表情地抛出质问。
李世民惊愕地跪倒在地,不明白自己何罪之有。
李渊将竹简扔到他面前,厉声呵斥刘武周南下连克数城,而负责留守的李世民却安坐家中完婚。
“这是玩忽职守,是天大的罪过!”李渊的声音陡然拔高。
李世民百口莫辩,防区失守确是他的责任,但他更清晰地看见父亲眼中没有愤怒只有冰冷的算计。
李建成立刻痛心疾首地附和,李元吉更是直接指责二哥居功自傲。
这唱和分明是要置他于死地,李世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
“儿臣愿领责罚,请父王给儿臣将功补过的机会!”李世民咬牙请战。
李渊等的就是这句话,他起身拍着儿子的肩膀,命其即刻率三千兵马北上迎敌。
“三千?”李世民不敢置信地抬头。
用三千人对阵五万敌军,这分明是十死无生的催命符。
李建成和李元吉眼中闪过幸灾乐祸,裴寂等人低下头不忍再看。
李世民看着父亲熟悉又陌生的脸,只觉得寒气从脚底直冲头顶,他终于明白父亲真的要他死。
与此同时,秦王府里的长孙氏也察觉到了异常。
府中护卫一夜之间全被更换,新来的守卫眼神冷漠行动肃杀,名为保护实为监视。
侍女们都变得战战兢兢,看她的眼神充满同情与畏惧。
她派人打探消息却发现王府如同铁桶,任何风声都传不进来。
巨大的不安笼罩心头,她焦急地等待,直到李世民失魂落魄地回来。
看到他苍白如纸的脸色,长孙氏的心猛地揪紧,快步上前扶住他。
李世民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紧紧将她拥入怀中,手臂微微颤抖。
长孙氏没有再问,只是静静地抱着他,知道颠覆命运的风暴已经来了。
04
夜幕再次降临时,秦王府的书房里烛火黯淡。
李世民坐在军事地图前目光涣散,脑海中反复回响着父亲冰冷的话语。
“三千兵马收复失地”这道命令不仅锁住他的手脚,更试图将他的生命与尊严一同碾碎。
长孙氏端着参汤悄无声息地走进来,从背后轻轻环住他的肩膀。
“二郎是不是觉得我做错了什么?”李世民沙哑地问。
长孙氏摇摇头,手指轻抚过他紧蹙的眉头:“错的是权欲人心。”
她顿了顿,压低声音说起今早打探到的消息。
有人隐约听见昨日袁天罡与李渊密谈时提及“皇后”“皇帝”之言。
李世民如遭雷击,瞬间将一切串联起来。
原来症结在这里,不是他做错了什么,而是他的存在本身就成了“错”。
那个荒诞的预言像毒种子在父亲心中生根发芽,长成了猜忌与杀意。
“荒谬!我何曾有过不臣之心!”李世民一拳砸在桌案上,虎目中燃起愤怒的火焰。
长孙氏紧紧握住他的手,眼神异常坚定:“现在不是追究的时候,我们必须走出一条生路。”
她的冷静让李世民慢慢平静下来,他深吸一口气问妻子有什么办法。
长孙氏沉吟道父王给三千兵马看似送死,其中或许也有试探之意。
“这一仗你不仅要赢,还要赢得恰到好处。”她清晰分析着,“不能大胜功高震主,也不能惨胜元气大伤,要打一场让所有人觉得是侥幸的巧胜。”
李世民的思路被彻底打开,他盯着地图脑中飞速运转。
长孙氏为他拨开了迷雾,指明唯一可能的生路。
然而他们不知道,此刻一匹快马正从唐王府疾驰而出。
马背上的信使怀揣李渊的亲笔密信,信上只有一句话:“若秦王有幸得胜,务必令其‘为国捐躯’于乱军之中。”
李渊要的从来不是试探,而是万无一失。
无论李世民是胜是败,结局都只有一个。
05
三日后晋阳城外秋风萧瑟,三千兵马在风中显得单薄而悲壮。
李世民身披玄甲骑在战马上,身后站着尉迟恭秦叔宝等心腹大将。
众将都看出此次出征的凶险,尉迟恭忍不住压低声音问殿下此行分明是刀山火海。
“既然信我就休要多言,此战我们未必会输!”李世民的话语充满自信,暂时安抚住众人。
大军即将开拔时,长孙氏的马车缓缓驶来。
她一身素衣走到李世民马前,递上一个沉重的木盒。
“此去万事小心。”她的声音温柔却带着不舍。
木盒里是满满的金银珠宝和几封盖着长孙家印信的书信。
“这是我全部的嫁妆,钱财可打点关节犒赏三军,书信能在危急时联络父亲旧部。”长孙氏轻声解释,“二郎,我等你回来。”
李世民热泪盈眶,翻身下马紧紧抱住妻子。
不远处城楼上,李建成和李元吉正并肩而立冷笑着看着这一幕。
“二弟和弟妹情深意重,只可惜快成亡命鸳鸯了。”李元吉幸灾乐祸地说。
李建成嘴角勾起残忍的弧度:“父王计策天衣无缝,无论胜败他都必死无疑。”
大军渐渐远去,长孙氏站在原地凝望直到背影消失。
回到府中她立刻启动长孙家所有情报网络,要查清李渊是否还有其他后手。
深夜一份加急密报送抵她手中,当看完内容时长孙氏全身血液都凝固了。
密报正是李渊那道“若秦王有幸得胜,务必令其为国捐躯”的绝杀令。
原来这根本是无法逃脱的必死之局,她的丈夫正一步步走向坟墓。
她必须把消息传出去,可大军已远如何追上?
正当她焦急如焚时,书房门“砰”地被人踹开。
唐王府卫队如狼似虎冲进来,为首的卫队长目光冰冷地锁定她。
“奉唐王令,秦王妃长孙氏涉嫌勾结外敌意图谋反,即刻拿下打入死牢!”
06
李世民率领着三千兵马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前行,秋雨绵绵不绝地打在士兵们的铠甲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尉迟恭策马靠近主帅身边,压低声音汇报说粮草只够维持五日,而距离前线还有三天的路程。
秦叔宝也从后方赶上来,面色凝重地告诉李世民士兵中已经开始流传秦王失宠将被抛弃的谣言。
李世民望着雨中疲惫不堪的队伍,心中清楚这不仅是军事上的考验更是父亲对自己的终极试探。
他召集所有将领在临时搭建的营帐中开会,摊开地图指着峡谷地带说出自己的计划。
“刘武周麾下宋金刚贪功冒进,我们可以在黑风峡设伏,用火攻破其先锋部队。”
程咬金挠着头说即便击败先锋,后面还有数万主力部队等着,三千人根本不够消耗。
李世民眼中闪过锐利的光芒,说真正要对付的从来不是刘武周,而是长安城里那位高高在上的父亲。
众将闻言都愣住了,帐中陷入令人窒息的沉默,只有雨点敲打篷布的声音单调地重复着。
“殿下是说……”尉迟恭的声音有些发颤,不敢说出那个可怕的猜测。

![这不就是现代版狸猫换太子[吃瓜]](http://image.uczzd.cn/16251508858676695559.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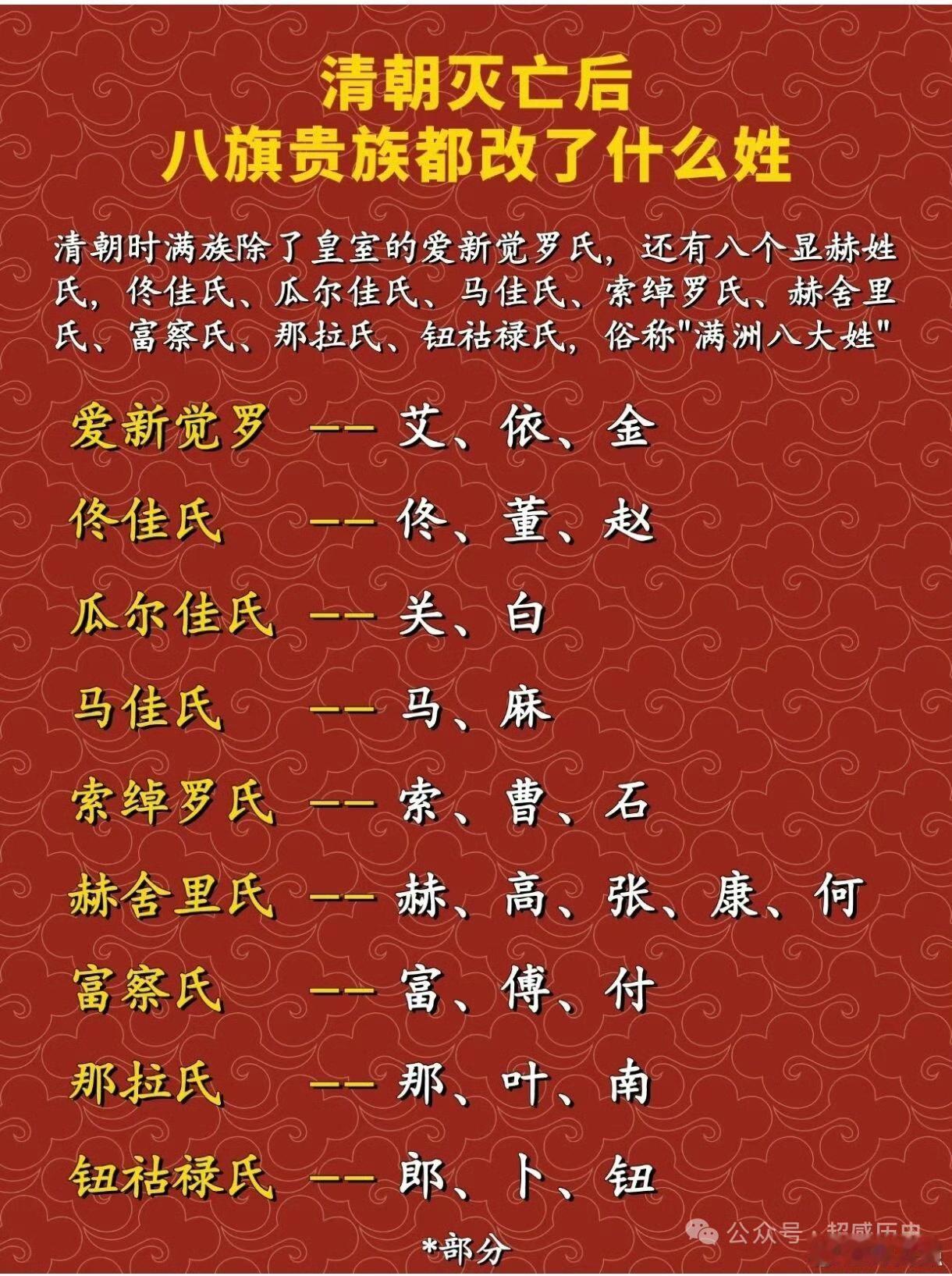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