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自古以来都是游牧民族竞技的胜地,乌孙人、匈奴人、波斯人、突厥人、柔然人、阿拉伯人、契丹人、蒙古人都曾在这片土地上纵横驰骋,开创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王朝,这些强大的游牧部落也在中亚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痕迹。而最后一个鲸吞中亚的大帝国,当然是沙皇俄国。
1865年夏季的塔什干城笼罩在战云之下。这座丝绸之路上的千年古城,此刻正面临着自帖木儿时代以来最严峻的考验。浩罕汗国的守军在城墙上日夜警戒,而城外,俄国远征军的炮口已经对准了这座中亚最后的自由堡垒。当俄军的重炮在6月15日黎明发出第一声怒吼时,没有人能预料到,这场持续仅三周的攻城战,将彻底改变中亚的地缘政治版图,并开启一个持续至今的大国博弈时代。
塔什干的陷落撕开了沙俄鲸吞中亚的裂口,此后 40 年间,400 万平方公里土地、2000 万人口被纳入沙俄版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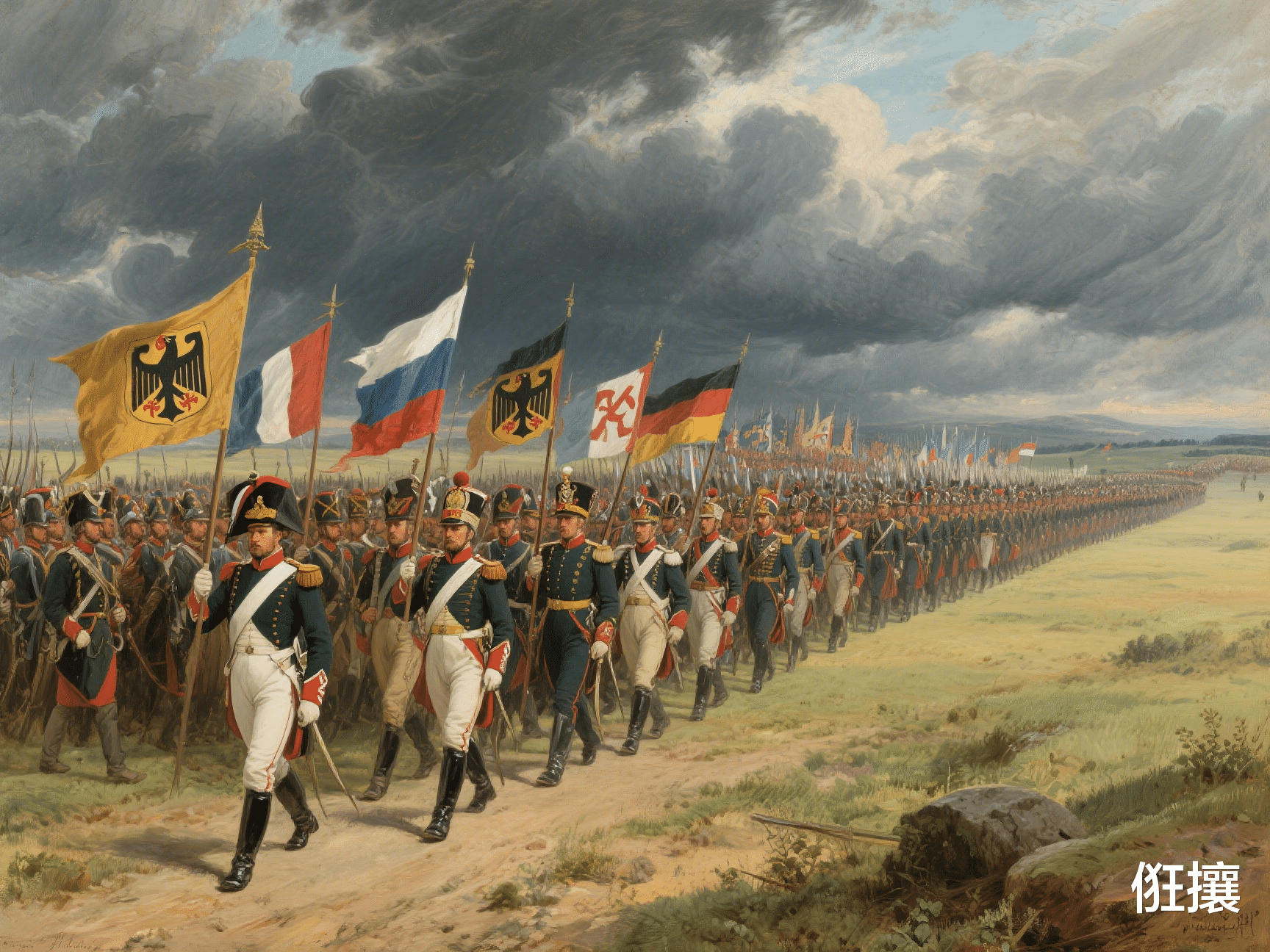
沙俄征服中亚草原
一、战前的中亚棋局
19世纪中叶的中亚正处于权力真空状态。曾经辉煌的帖木儿帝国早已解体,其继承者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陷入无休止的内斗。英国驻印度总督劳伦斯爵士在1864年的秘密报告中写道:"这些汗国就像沙漠中的蝎子,互相撕咬却无力抵御外敌。"与此同时,俄罗斯帝国在完成对高加索的征服后,正以每年70公里的速度向南推进。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授命突厥斯坦总督切尔尼亚耶夫采取"刺刀先行,条约跟进"的策略,而富庶的塔什干绿洲正是其首要目标。
浩罕汗国统治者毛拉·阿利姆·库里深知危机迫近。他紧急加固了塔什干的双层城墙(外城周长24公里,内城8公里),并囤积了足够支撑半年的粮草。英国探险员肖在战前记录道:"城墙上的铜炮擦得锃亮,但使用的还是帖木儿时代的火药配方。"更致命的是,浩罕军队内部分裂严重,三万守军中,真正效忠汗王的不足半数,其余都是被强征的塔吉克农民和不满的哈萨克部落民。

塔什干之陷
二、钢铁与意志的较量
切尔尼亚耶夫率领的俄军仅有1500名正规军,却配备了最新式的克虏伯后膛炮和伯丹步枪。这位被称为"中亚白狼"的将领采取心理战与火力压制并重的策略:白天用炮火摧毁城防工事,夜晚派哥萨克骑兵切断补给线。现藏于圣彼得堡军事博物馆的切尔尼亚耶夫日记记载:"6月20日,我们的炮弹打穿了西北角的礼拜寺穹顶,那些缠着头巾的士兵像受惊的蚂蚁般四散奔逃。"
决定性的转折发生在7月1日深夜。一队吉尔吉斯雇佣兵叛变,为俄军打开了萨马尔罕门。俄军工程兵中尉科瓦列夫斯基的回忆录描述:"我们踩着齐膝的血水冲进内城,月光照在弯刀上泛着蓝光。"巷战持续了三天,浩罕守军依托民居和巴扎巷道殊死抵抗。最终在7月4日拂晓,毛拉·阿利姆·库里带着残部从东南角突围,留下2000具尸体和浓烟笼罩的城市。

沙俄征服塔什干
三、地缘政治的多米诺骨牌
塔什干的陷落引发了连锁反应。1866年1月,俄国在占领区设立突厥斯坦总督区,首任总督考夫曼将总督府设在塔什干旧皇宫。英国《泰晤士报》惊呼:"俄罗斯人把刺刀插进了印度的大门!"为应对危机,英国加速控制了阿富汗并扶持布哈拉汗国作为缓冲带。1873年英俄签署的《中亚协定》将阿姆河划为势力分界线,这个人为划定的边界至今仍是中亚国家纠纷的根源。
军事占领伴随着文化征服。俄国人在塔什干老城旁建设了欧洲风格的新城,宽阔的林荫道取代了蜿蜒的巷弄,东正教堂的尖顶与清真寺的穹顶比肩而立。1885年通车的跨里海铁路更将中亚纳入俄国经济体系,塔什干成为棉花和石油的转运中心。当地史学家卡里莫夫指出:"我们失去了政治独立,却获得了融入现代世界的机会。"
同时,塔什干之陷终结中亚 “多汗国分立”,开启殖民统治体系,在塔什干陷落前,中亚(河中地区、费尔干纳盆地等核心区域)长期处于分散的汗国自治状态:以塔什干为核心的 “浩罕汗国” 是当时中亚最具活力的政治实体之一,与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三足鼎立,同时还有大量部落联盟维持局部自治。而塔什干作为浩罕的经济与军事重镇,其陷落直接摧毁了中亚抵抗沙俄的核心力量。
塔什干失守后,浩罕汗国失去了最重要的税收来源和军事屏障,内部部落贵族纷纷倒向沙俄,汗国迅速沦为沙俄的 “保护国”,并在 1876 年被正式吞并,成为沙俄 “费尔干纳州” 的一部分;殖民行政体系的确立:1867 年,沙俄以塔什干为首都,设立 “土耳其斯坦总督区”,将布哈拉、希瓦等汗国变为 “附属国”,通过 “直接统治(核心城市)+ 间接控制(附属汗国)” 的模式,彻底取代了中亚原有的政治秩序,终结了其数百年的独立政治史。

俄罗斯主导中亚农业
四、经济从 “区域自主贸易” 沦为 “沙俄原料附庸”
塔什干此前是中亚的交通枢纽(连接波斯、印度、中国的丝绸之路要道)和手工业中心(以丝绸、棉纺织、金属加工闻名),经济结构相对独立。沙俄征服后,通过强制政策重构了中亚经济。
强制 “单一作物化”:沙俄为满足本国纺织业需求,强迫中亚农民放弃粮食种植,大规模种植棉花,使中亚从 “粮食自给区” 变为 “棉花原料基地”,19 世纪末中亚棉花产量占沙俄总产量的 80% 以上,而粮食需依赖沙俄本土进口,经济主权完全丧失。
摧毁本土手工业:沙俄通过关税壁垒,将本国廉价工业品(如棉布、铁器)倾销到中亚,挤压本土手工业生存空间,塔什干的传统丝绸作坊从 1865 年的 200 余家锐减至 1900 年的不足 30 家,中亚从 “手工业出口区” 沦为 “工业品消费市场”;交通网络的殖民化:19 世纪 80 年代,沙俄修建 “中亚铁路”(从奥伦堡到塔什干),铁路并非为促进中亚内部联系,而是为了更快地将棉花运出、将军队和商品运入,进一步巩固了中亚对沙俄的经济依附。

中亚地缘
五、“人为划界” 埋下民族矛盾隐患,导致社会矛盾加剧
中亚原本是多民族(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等)交错杂居的区域,民族分布以 “部落游牧范围” 或 “绿洲聚居区” 为自然边界,并无严格的行政分割。沙俄为削弱中亚民族的凝聚力,采取 “分而治之” 的划界策略。
打破自然民族聚居:将同一民族分割到不同行政单元(如哈萨克人被划入 “草原总督区” 和 “土耳其斯坦总督区”,塔吉克人部分归属布哈拉附属国、部分归属撒马尔罕州),同时将不同民族强行划入同一区域(如费尔干纳盆地聚集了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等多个民族)。
强化 “民族身份” 而非 “地域认同”:沙俄通过人口普查、语言登记等方式,首次在中亚明确 “民族标签”,取代了传统的 “部落认同” 或 “汗国认同”,虽客观上推动了中亚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但也为 20 世纪中亚各国独立后的 “跨界民族问题”(如乌兹别克与塔吉克的领土争议、吉尔吉斯与乌兹别克的民族冲突)埋下了根源。

塔什干东正教堂
六、宗教遭受俄化渗透、传统伊斯兰文化受冲击
塔什干是中亚伊斯兰文化的重要中心,拥有大量清真寺、经学院(如 “哈兹拉提伊玛目清真寺”),伊斯兰教法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准则。沙俄征服后,虽未彻底禁止伊斯兰教,但通过一系列政策削弱其影响力:
世俗化改革与俄化教育:沙俄在塔什干设立俄语学校,强制推广俄语教学,限制伊斯兰经学院的招生规模;同时颁布《草原条例》《土耳其斯坦条例》,以沙俄法律取代伊斯兰教法,规范婚姻、继承等社会事务,传统伊斯兰文化的社会功能被大幅压缩。
文化符号的改造:塔什干的城市布局被重构,沙俄风格的政府大楼、东正教堂取代传统的伊斯兰集市(巴扎)和清真寺,成为城市核心地标;俄式服饰、礼仪、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逐渐在精英阶层传播,形成 “上层俄化、下层伊斯兰化” 的文化分裂格局。

中亚受俄罗松影响程度
七、大国博弈加剧,长远的战略阴影
英国此前通过控制印度,将势力范围延伸至阿富汗,原本视中亚为 “缓冲地带”;而沙俄占领塔什干后,继续向南推进(1881 年征服土库曼斯坦,1885 年与英国在阿富汗边境爆发 “潘杰德危机”),直接威胁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
为对抗沙俄,英国加强对阿富汗的控制,扶持阿富汗王国作为 “缓冲国”,同时试图与中国(清朝)合作牵制沙俄(如 1881 年《中俄伊犁条约》前后的外交互动)。这场博弈使 “中亚” 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变为全球地缘政治的 “焦点之一”,并深刻影响了此后阿富汗、中国新疆的历史走向。
这场战役的影响持续发酵。苏联时期,塔什干成为中亚军区总部所在地,1966年大地震后重建为样板城市。1991年乌兹别克斯坦独立时,前克格勃军官卡里莫夫能顺利掌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俄国留下的行政体系。今天,塔什干地铁站里仍保留着列宁像与卫星浮雕,而俄罗斯201军事基地就驻扎在当年攻城战的突破口附近。

塔什干之战
八、总结
总体而言,塔什干之陷并非孤立的军事事件,本质是工业文明(沙俄)对农业 - 游牧文明(中亚传统社会)的碾压性冲击。站在宏观角度上看,中亚历史从 “传统部落 - 汗国自治时代” 转向 “沙俄殖民统治时代” 的核心转折点,其影响贯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深刻重塑了中亚的历史走向。它不仅终结了中亚的独立历史,更从经济结构、民族边界、文化认同等底层逻辑上,重塑了中亚的 “现代性” 基础,其影响延续至今。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