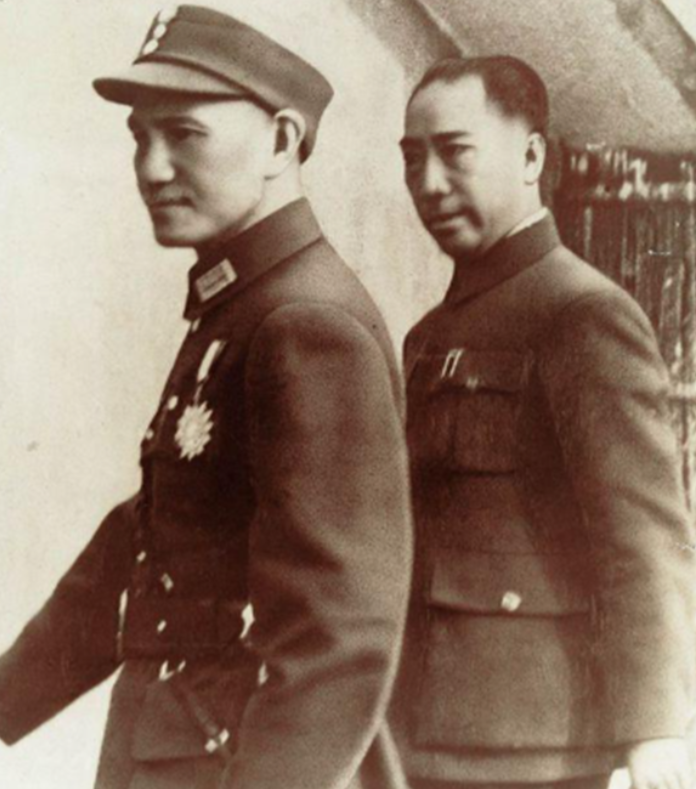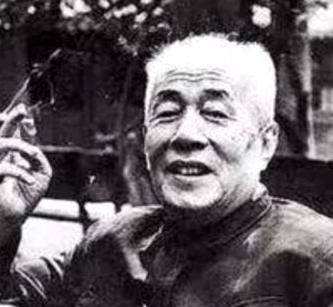1933年腊月二十三,小年之夜,暗杀大王王亚樵约好与母亲见面,但母亲没等来,却等来了戴笠,但等到军统特务破门而入后,一摸床,戴笠差点没气死。 时间地点安排在,赵主教路刘志路公馆。约定的暗号是敲门“三下、两下、三下”,一旦顺序不对,立刻中止见面。 弟弟到了,敲门声却变了调——“梆、梆、梆”,平了节奏。 屋里瞬间安静,王亚瑛眉头紧锁,身子微微一震。 敌情未动,心战已起,这一声错乱的敲门,背后站着戴笠,布控早已完成,外围几道岗,里面布哨、尾随、暗桩一应俱全。 可王亚樵不是等闲之辈,公馆大门上方悬着纸包,纸包细线系着门梁。 一旦强行破门,细线一断,纸包落地,远处一盏煤油灯下,纸影坠地,像是敲了战鼓。 机关触发,只一瞬间,风起云涌。 王亚樵早有准备。屋后阳台贴着排水管,他腰间拴着根“软杆子”,用钢丝编成,头部三爪钩,松紧可控。 他蜷身跃出窗台,一脚挂住阳台角,一手甩杆钩住排水管,脚下发力,身子像条蛇,滑墙而下。 雪地无声,他人已远,戴笠不在现场,人却早在布阵前做足功夫。 十万悬赏、港口巡查、车夫眼线,连杜月笙府上,做饭的厨子都已入账。 可每次包围,每次落空,王亚樵像水流,堵东边就绕西边,赵主教路一役,不光没捉到人,连棉线机关都成了笑柄。 江湖对上体制,戴笠碰上刺王,输得窝囊。 王亚樵不是简单反抗者,是斧头帮出身,十年江湖练就逃生术一整套。 进屋先摸地形,开窗先记出口,茶壶能藏枪,地砖下有洞口。 刺张秋白那年,他在安徽布三条退路,一路水、一条林、一道桥,最后从送饭小贩的饭桶里钻出来,没人想得到。 小年夜那场逃脱是整个“猫鼠游戏”的缩影。 一边是戴笠背后的庞大系统——军统档案、密探网络、法租界警局通气; 一边是王亚樵的草根防线——木匠店、旗袍铺、混江湖的亲戚邻里。 对手太熟,套路太多,谁也没法真正踩死对方。 戴笠急了,转而盯紧王亚樵身边的“情感缺口”,盯上的是余婉君,王亚樵兄弟余立奎的妻。 1936年,王亚樵前往梧州,本为营救被俘兄弟。余婉君递出信,说余立奎要转狱,只差一趟面谈。 王亚樵按约出门,雪夜转街,未曾想,等来的不是兄弟消息,而是满街围捕。 石灰扑眼,刚开口,枪已响,死时身中五弹,身边不见一人,软杆子还在腰间,没来得及解。 戴笠那边,虽传出“全歼”喜讯,但内部都知,这一局花了三年,动用百人,只杀一人,实则损耗惊人。 王亚樵死后,其旧部多人北上,技法传入八路军情报系统。 南京、长沙、武汉,均见其老部下身影,戴笠终胜,胜得发虚。 王亚樵的布防思维,后来被总结成一整套教程。 “不住长宅,不走熟巷,不信常友,不开正门”,华克之就是靠这套规矩,在香港靠送报纸维生,却能传十年情报无失误。 江湖系统虽散,却灵,灵得过于难缠。 王亚樵之死像道分水岭,之前戴笠靠体制压人,之后开始模仿民间特工系统:临时联络、不挂职务、密码口令、备份通道。 再后来的中统、军统分裂,其实都能看见这一套“江湖打法”的影子。 暗杀未成者多,逃脱成功的少,像王亚樵这样连戴笠都形容为“蛛网”,一次次断线又再接的,更是罕见。 体制要围死的,不一定能杀掉;但江湖要保住的,哪怕只剩半口气,也能把人送出去。 公馆一役没留下影像,只有当晚雪地的脚印、墙边断线的棉纸,还有戴笠留下的一句话:“他的老巢剪不断,像野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