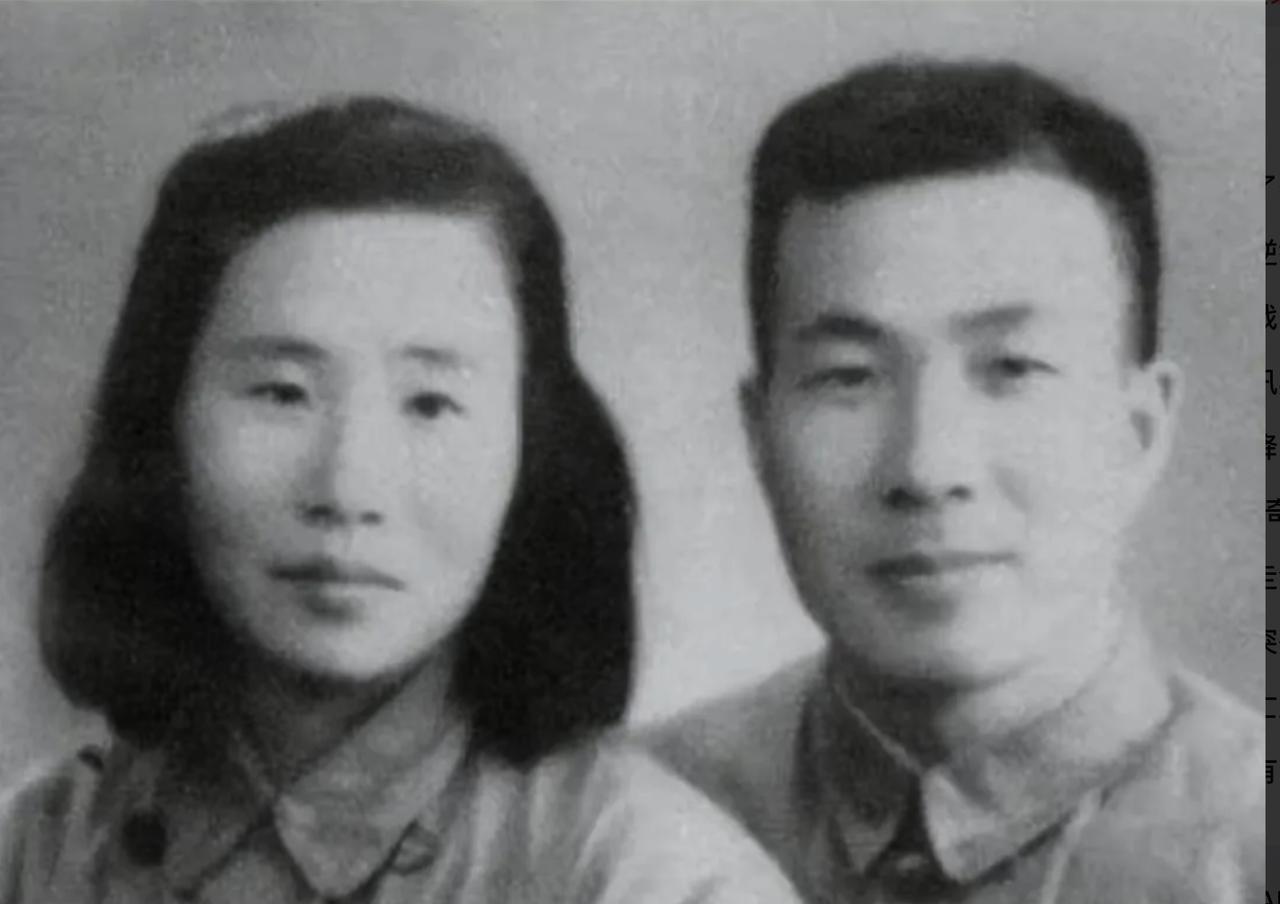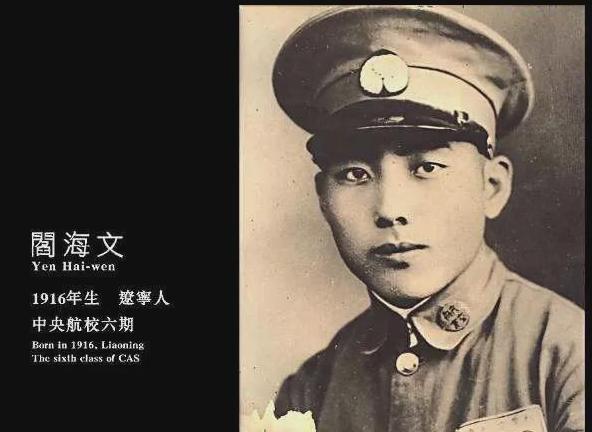1942年一名新四军战士外出时,突然看到对面偷偷摸上来一大片日军,自己的后方就是新四军大本营,眼看日军就要渡河,这名战士下定了某种决心,拿着自己的枪就朝日军冲了过去,准备以一己之力阻击日军渡河,为大部队争取时间。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淮宝县野战医院门口,有一挺沉重的九二式重机枪,静静地立在台座上,枪身被战士们擦得锃亮,仿佛从未开过火,但它不是展品,也不是纪念碑,而是一位幸存者——它曾是敌人的武器,后来成为医院的守护神,这挺枪的归属背后,藏着一场冰河上的血战,还有一个叫吴剑的年轻战士。 1942年冬季,正值敌人对苏北地区发动大规模“扫荡”,新四军四师主力部队已提前转移,唯独野战医院因为伤员太多,实在无法迅速撤离,医院所在位置在一条冰封河流的西岸,河对岸则是敌军可能进攻的方向,为了掩护医院转移,保卫科派出一支小队前往河堤防线,其中包括保卫科长吴剑。 那天傍晚,吴剑原本正在审讯几名被俘的伪军,试图从中获取情报,但战局突变,敌人提前发动了进攻,驻地枪声大作,他当机立断,押着犯人向北突围,前方是一条结冰的大河,河面看似宁静,实则危机四伏,吴剑带着警卫员和俘虏藏身于河堤一带的一条干涸沟渠中,利用地形观察敌情。 此时河对岸的堤坝上,黄色制服密集出现,敌军正在准备渡河,企图从正面强攻医院后方,敌军人数不少,至少一个中队,装备精良,带有机枪和迫击炮,行动快速而有秩序,他们似乎并未察觉吴剑等人已潜伏在对岸堤岸上,正密切注视着他们的每一步。 吴剑所携带的武器并不先进:一支破旧的小马枪和一把左轮手枪,子弹加起来不过二十几发,他清楚,这不是一场能靠火力取胜的战斗,他必须用精准与冷静,去换取时间,但这时间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三百多名还躺在病床上的伤员。 第一批敌军工兵开始试图架设渡河绳索,试图搭建简易浮桥,吴剑选择了最前方那名测距兵作为目标,扣动扳机,子弹准确命中眉心,随着这名士兵仰面倒下,冰面上的敌人顿时陷入混乱,紧接着,吴剑连续射击,又有两人栽倒在冰面上,血迹在晶莹冰层上迅速扩散。 敌军反应迅速,立即调动三挺重机枪开火,河堤上的土石被打得飞溅不断,但吴剑早已熟练地转移阵地,每次射击后快速变换位置,他在弹坑之间匍匐移动,利用地势掩护自己,躲避子弹与炮火的同时,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他的目标始终明确——只打指挥官、机枪手和工兵,每次扣动扳机,河对岸就会倒下一名关键人物。 战斗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敌军始终无法成功架桥,他们开始改变策略,分出一支小部队,试图从下游绕过来包抄吴剑所在位置,这支包抄部队有五十多人,配备有轻重机枪,正快速穿越侧翼林地,吴剑已精疲力尽,腿部被弹片击中,鲜血在雪地上拖出一道道长痕,他只能靠双臂爬行,想要转移到下一个掩体。 当敌人的刺刀寒光已逼近到二十步之内,吴剑仅剩一发子弹,他手握枪栓,准备做最后一击,就在此刻,下游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那是他熟悉的捷克式轻机枪的节奏,援军赶到了。 特务连连长彭修强带着一个班的兵力,从下游杀出,他们的机枪在雪地中怒吼,形成一道密集的交叉火力网,敌军的包抄队伍被这突如其来的火力压制在河岸边,纷纷倒下,枪声如雷,鲜血染红了雪地,吴剑趴在冰冷的地面上,终于松了口气。 彭修强和他的战士迅速与吴剑会合,利用火力优势稳住局势,他和吴剑分别掩护左右两翼,一人压制重火力点,一人专打敌军指挥官与机枪手,这两个并肩多年的老战友,用最默契的配合,将敌军一步步逼回河岸。 当新四军主力团从背后合围而至时,敌军已无退路,整场战斗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最终以日军败退告终,吴剑被战友们抬下战场时,棉衣早已被血水与雪水冻成硬壳,手中那支小马枪已经打光,枪管还在冒着白烟。 战后清点,敌军在这场交战中损失百余人,而野战医院的三百多名伤员则全部安全转移,吴剑一个人击毙十五人,其中包括一名敌军小队长和多名关键岗位士兵,他用自己微薄的火力,在敌人面前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防线。 三天后,吴剑在野战医院苏醒,他高烧不退,神志不清,反复低声喊着“别让他们过河”,直到这时,警卫员才真正明白,这场他死守河堤的战斗,并不是为了任务,而是为了那三百多名还在病床上的兄弟。 那挺被缴获下来的九二式重机枪,战后被永久安放在野战医院门口,上面刻着三个字——“护院枪”,它不再开火,也不再移动,但它的存在,时刻提醒着后来的人:在那场最寒冷的冬天里,有人曾用血肉之躯,为战友们守住了一线生机。 信息来源:日军《第17师团作战日志》(防卫省公开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