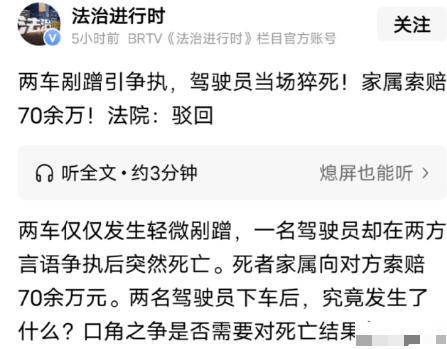令人心酸的一段话: “老人的前途是病和死。我还得熬过一场病苦,熬过一场死亡的苦,再熬过一场炼狱里烧炼的苦。老天爷是慈悲的。但是我没有洗炼干净之前,带着一身尘浊世界的垢污,不好‘回家’……” 医生说我脑中的血栓像悬在屋檐下的冰凌,不知何时会落。我摸着床头柜上那本翻烂的《金刚经》,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情景。 那也是这样一个午后,阳光把病房切成明暗两半。他瘦成一把枯柴,却坚持要自己刷牙。牙刷在嘴里机械地动着,血水顺着嘴角流下来。 “爸,别刷了。” 他不理,继续刷,直到吐出满口血沫。 “脏。”他看着我说,“不能这样回去。” 那时我不懂。现在,当我也走到生命的隘口,才明白他说的“回去”是回哪里去。 一 我的第一场病苦来得悄无声息。 是去年桂花开的时节。我照常去公园遛弯,走到第三圈时,左腿突然不听使唤。不是麻木,是它突然成了别人的腿。我扶着长椅慢慢坐下,看那些年轻人从我身边跑过,他们喘着气,汗珠在晨光里闪闪发亮。 多奢侈啊,能自由地喘气。 住院那天晚上,护士来抽血。针头扎进青紫色的血管时,我忽然想起七岁那年,母亲在井边给我洗澡。她用皂角搓我的脖子,搓出一层灰泥。 “看你这身泥猴样。”她笑着拍我的背。 现在,我成了真正的泥猴,血管里流淌着药水,皮肤上贴着电极片。这副皮囊,比七岁那年脏多了。 二 死亡的苦,我在父亲身上预习过很多次。 他最后的日子里,总盯着窗外那棵老槐树看。树上有个鸟窝,春天时会有燕子飞来。 “它们认得路。”有一天他突然说,“不管飞多远,都认得回家的路。” 他说话时,手指一直捻着被角。那床白色被单被他捻出一个旋涡,像时光的隧道。 他走的那天特别清醒,让我给他刮胡子。我的手抖得厉害,刀片在他松弛的脖子上游走。他闭着眼,忽然说:“轻点,别吵醒你妈。” 母亲已经去世十年了。 最后一口气呼出来时,声音像一片叶子轻轻落地。我看着他脸上那些老年斑,想起母亲生前总笑他:“你这人,连老了都不肯老老实实地老。” 现在轮到我了。镜子里的脸,越来越像父亲。 三 最难的,是炼狱里烧炼的苦。 不是疼痛,是那些翻江倒海的记忆。深夜,当止痛药的效力退去,往事就像默片一样在眼前播放。 我看见三十岁那年,为了升职,把同事的方案据为己有; 看见四十岁那年,母亲病重,我却因为一个重要会议错过了最后一面; 看见五十岁那年,女儿高考前夜,我和她大吵一架,只因她不肯报我选的学校…… 这些记忆像锈迹,深深蚀在灵魂上。 前天,女儿来看我。她给我剪指甲,剪得很慢,很仔细。 “爸,”她突然说,“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 我问她原谅什么。 “所有。”她说,“所有的事。” 那一刻,窗外的云正好散开,阳光涌进来,照在她也有了皱纹的脸上。我突然明白,老天爷给我的慈悲,就是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让我在彻底“回家”之前,把这一身尘浊世界的垢污,一点点洗刷干净。 四 今早,护工小陈推我去花园。雨后,月季开得正好。 “李爷爷,您看这花,昨天还被雨打得抬不起头呢。” 我让他在一株白色月季前停下。花瓣上还挂着水珠,在阳光下像一颗颗钻石。 “真干净。”我说。 小陈笑了:“刚下过雨嘛。” 他不知道,我说的是另一种干净。 回病房时,经过儿科病房。一个光头的小女孩在走廊里画画,她看见我,举起画纸:“爷爷你看,我画的家。” 画上有大大的太阳,小小的房子,房顶的烟囱冒着炊烟。门是开着的,像在等谁回去。 “真好。”我说,“门开着。” “当然要开着呀,”女孩眨着大眼睛,“不然家里人怎么进去呢?” 我愣在那里,忽然泪流满面。 五 昨晚,我梦见了父亲。 他不在病床上,而是在我们老家的院子里劈柴。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动作利落有力。 “爸,”我在梦里问他,“你不病了吗?” 他直起腰,用袖子抹了把汗:“病完了。” “死亡呢?” “也死完了。”他笑起来,牙齿很白,“现在该你病了,该你死了。别怕,都是回家的路。” 醒来时,枕巾湿了一片。但心里是前所未有的清明。 我拿起床头的《金刚经》,翻到最喜欢的那一页:“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窗外的天渐渐亮了。第一缕阳光照进来,落在我的手上。这双布满老年斑的手,曾经捧过初恋的脸,打过叛逆的儿子,也扶过临终的父亲。现在,它正学着松开,松开一切紧握的东西。 护士来送药时,我说谢谢。 医生来查房时,我配合地伸出胳膊。 女儿打电话来,我说一切都好。 这就是我现在的功课,在病苦中学会承受,在死亡的阴影里学会放手,在炼狱的烧炼中,把这一生的爱恨情仇,慢慢熬成可以带回家的样子。 我知道,当最后一点尘垢洗净,那扇门会为我敞开。就像父亲说的,就像画上画的。 而我要做的,就是在这场漫长的归途里,走完最后的洗炼。 犹如《圣经》中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尘世是逆旅,而老去是归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