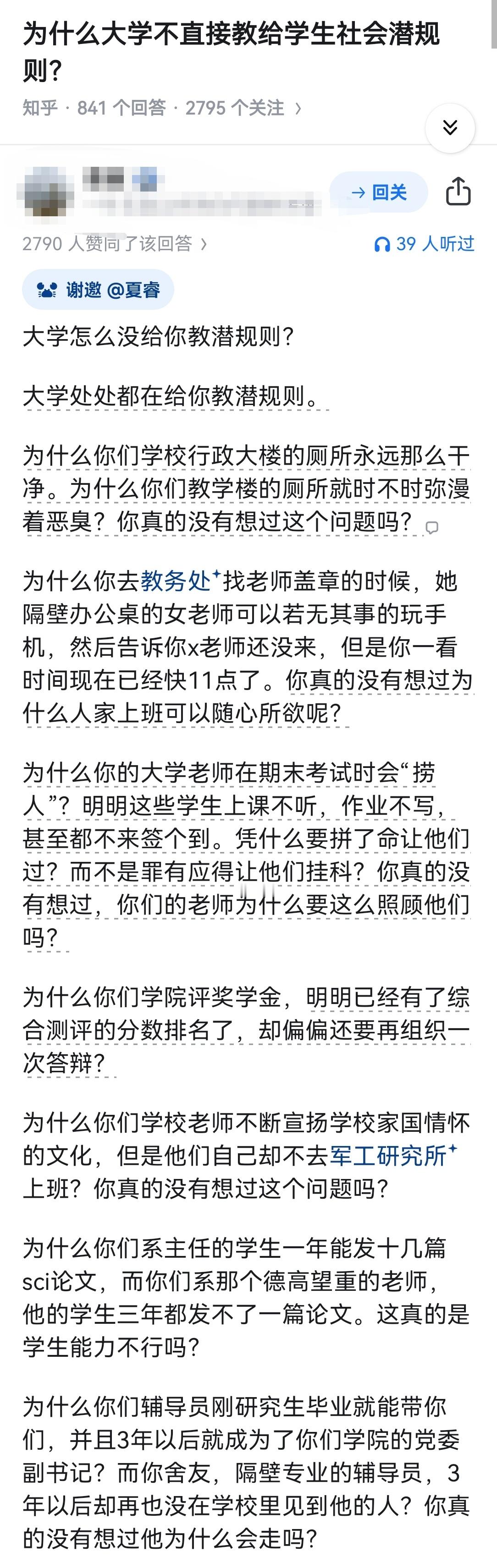当一位老师因公开课压力而选择轻生,舆论的焦点很容易被引向“心理承受能力”或“工作压力”的讨论。但这轻飘飘的“压力”二字,恰恰掩盖了悲剧背后最冰冷、最残酷的真相——那位老师,很可能不是被“工作”累死的,而是被一场精心策划、全员参与的“教育表演”所绞杀。 我们真正该追问的,不是校方该担何责,而是:为什么一堂本该促进教学交流的“公开课”,竟异化成了足以压垮一个鲜活生命的“公开处刑”? 一、公开课的“罗生门”:谁在台上,谁在台下? 想象一下这堂课的场景: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堂被排练了无数遍的“戏剧”,他们熟知每一个问题、每一次举手,甚至每一位同学回答的顺序。他们是训练有素的“演员”。 对听课的领导专家而言,这是一场教学成果的“汇演”,他们手持评分表,审视着教学环节的完整性、课堂互动的活跃度、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他们是严厉的“评委”。 而对那位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呢? 他早已不是“教师”,而是一个身兼“导演、编剧、主角”于一身的“提线木偶”。他的每一句话都经过字斟句酌,每一个动作都经过反复设计,课堂的每一分钟都必须精准卡点。 他的痛苦在于,他深知这堂课与“教育”的本质——即思想的碰撞与智慧的启迪——已相去甚远。但他必须倾尽全力,去维护这个完美的谎言。当一个人被迫在自己的信仰(教育求真)与现实的规则(表演求美)之间持续撕裂,精神的崩塌便开始了。 二、压垮骆驼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整个“生态系统” 将责任简单归咎于校方“施压”,是片面的。校方本身也身处一个更庞大的“表演式治理”系统之中。 这堂课早已不是一堂课,它是: 学校的“门面工程”:关系到学校的评级、领导的政绩、区域的排名。 教育的“橱窗展览”:用来向上级和外界展示“教学改革成果”和“素质教育成就”。 在这个系统里,一堂成功的公开课,必须是一场“零瑕疵”的演出。任何一点意外——一个学生的非常规提问,一个多媒体设备的故障——都可能被视为重大教学事故。 于是,压力被层层加码,从教育局到学校,从校长到教研组,最终全部压在授课老师一人身上。他背负的,是整个系统对“完美形象”的集体渴望。他不是在为自己上课,而是在为一个扭曲的“教育政绩观”进行一场终极献祭。 三、从“育人”到“演人”:教师尊严的陨落 教师的职业尊严,源于“传道授业解惑”过程中获得的价值感与成就感。但当公开课变成“公开演”,这种尊严便被彻底剥夺了。 当课堂变成舞台,学生变成道具,教师自己也沦为了一个“教育演员”。他无法享受教学相长的真实快乐,只能焦虑于评委的一个眼神、领导的一句评价。他的专业能力,被简化成了一张打分表上的数字;他的教育智慧,被异化成了操控一场表演的技术。 当一个灵魂工程师,发现自己每天都在建造“空中楼阁”,其内心的虚无与绝望,外人何以想象? 这种对职业价值的根本性否定,远比加班加点的劳累更具毁灭性。 结语:问责之后,更需“问魂” 讨论校方的法律责任是必要的,但若止步于此,无异于买椟还珠。真正的问责,是追问我们整个教育生态: 我们是否已经集体默许了这种“表演文化”的泛滥? 我们评价一个好老师、一所好学校的标准,究竟是看他们日复一日的育人成效,还是那一堂堂粉饰太平的“样板戏”? 悼念一位老师的离去,最好的方式不是再次陷入“减负”的空洞呼吁,而是勇敢地拆掉那个华而不实的“舞台”,把真实、有时甚至有些混乱但充满生命力的课堂,还给老师,还给学生。 否则,今天我们可以为公开课“逼死”一位老师而哀悼,明天又是否会为职称评审、为升学率、为另一场“完美表演”而失去更多? 是时候了,让教育回归“育人”的本真,而停止这场代价惨重的“演人”悲剧。 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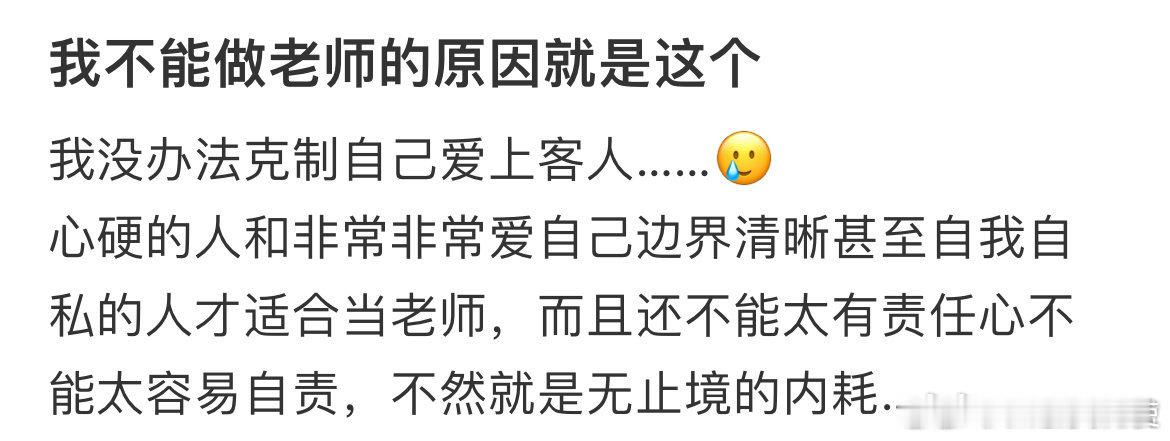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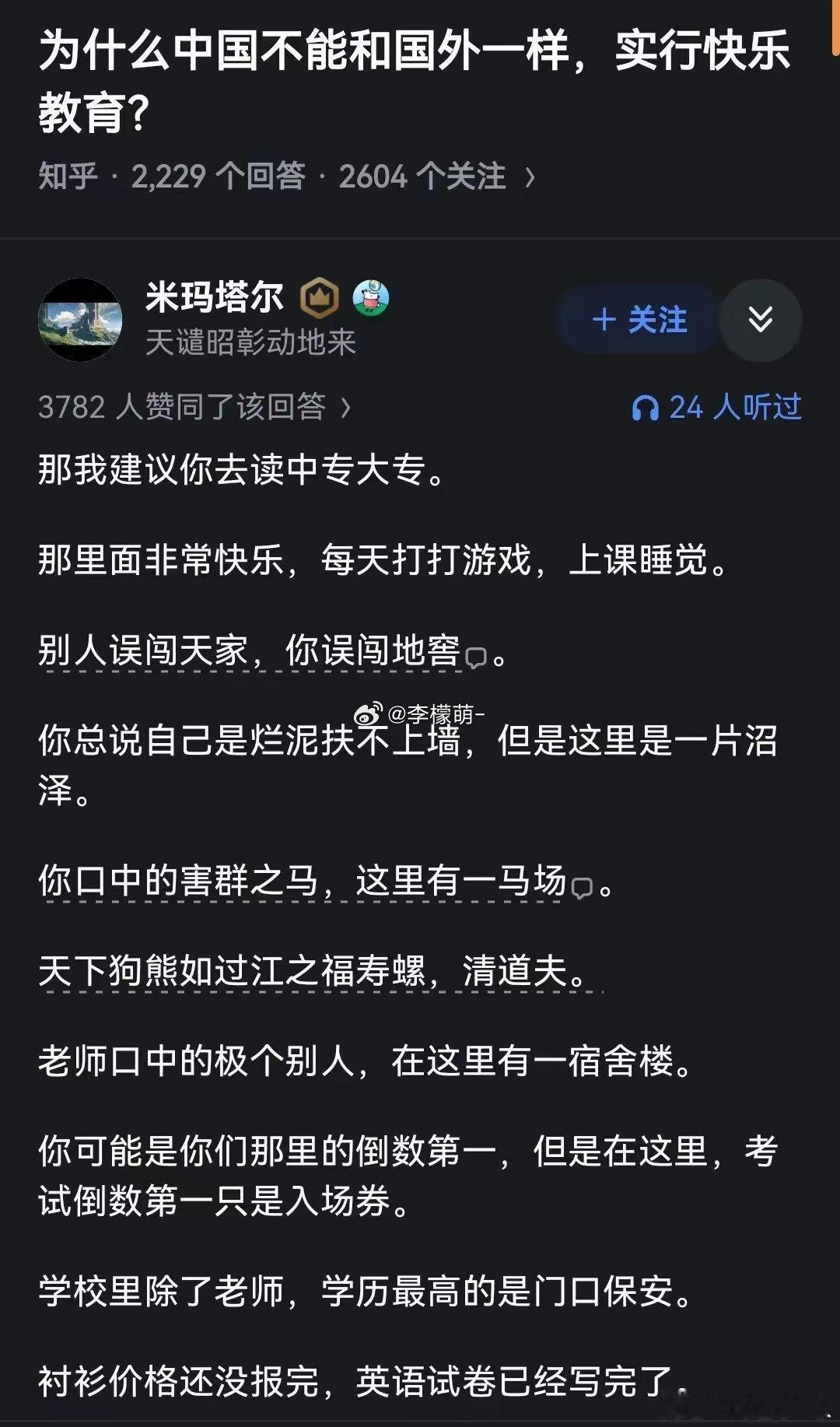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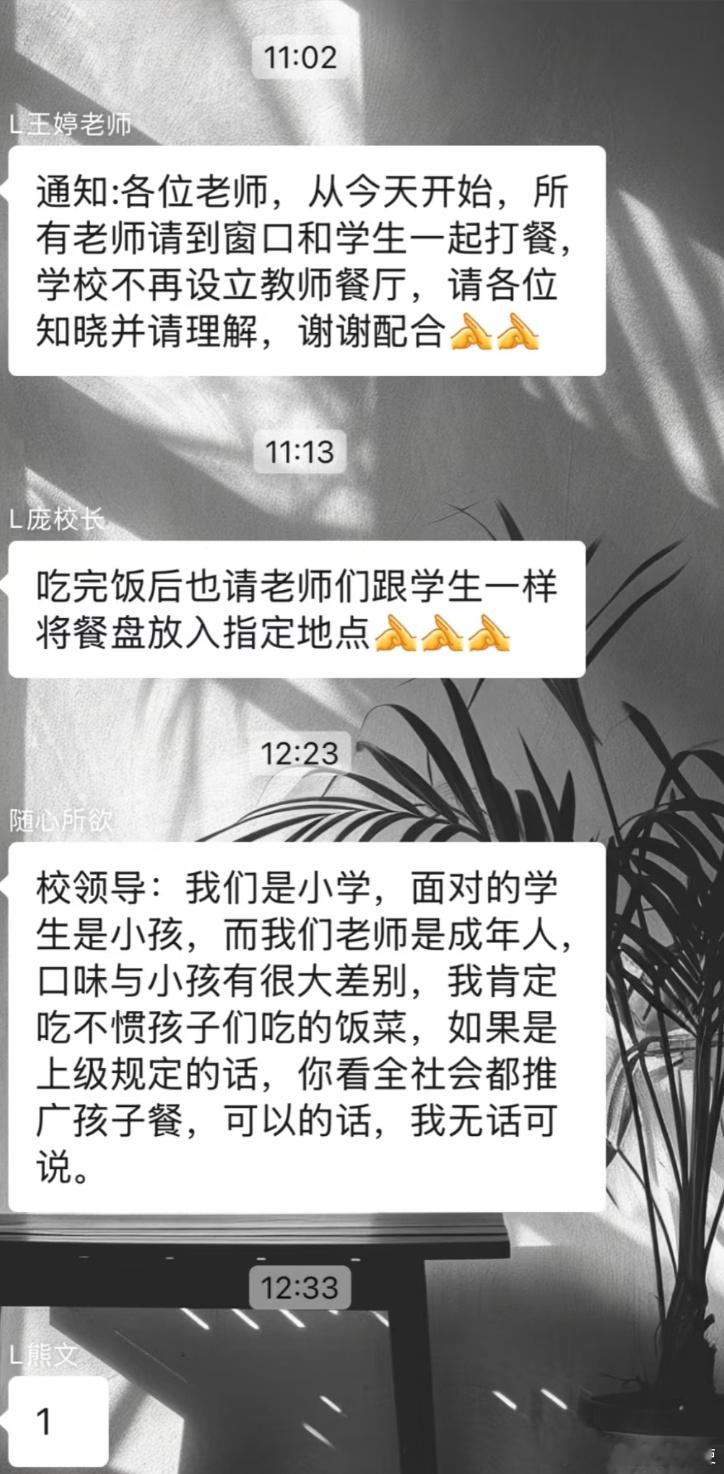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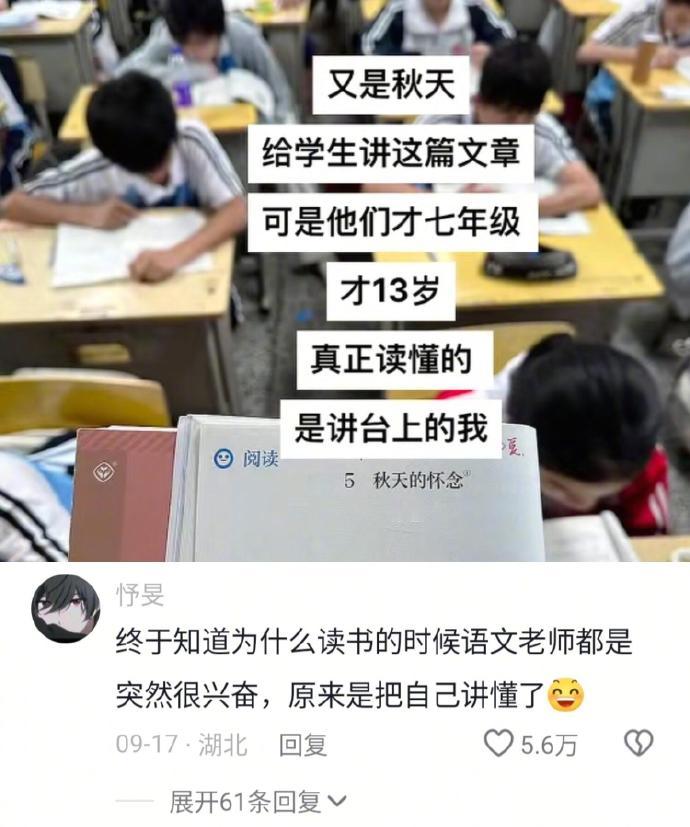
![[思考][思考][思考]](http://image.uczzd.cn/865200884053969355.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