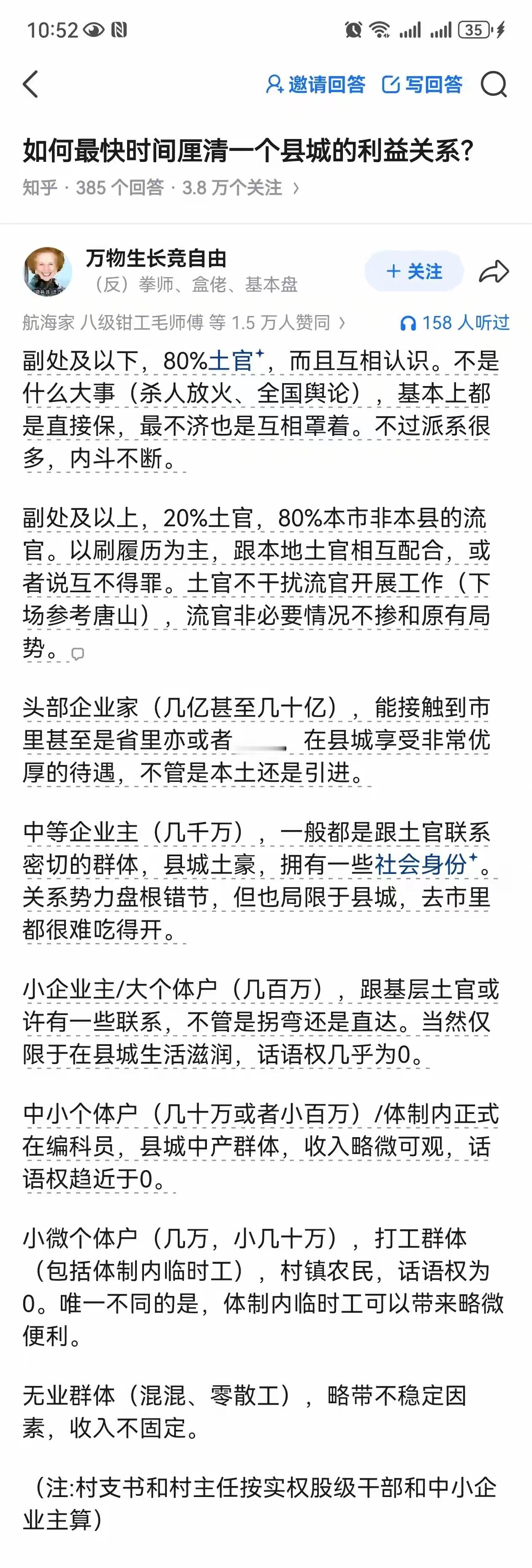1977年,安徽女知青于文娟,返城前夜把自己给了农村小伙:“你对我的好,我无以为报,让我们给过去一个交代吧!”谁知回城不久,她却突然消失不见,一生就此改变。 火车哐当哐当碾过铁轨时,于文娟攥着那袋花生的手指泛了白。 王胜利托人送来的这袋东西,壳上还沾着安徽稻田的泥星子,是她去年随口说好吃的玩意儿。 车窗外掠过的白杨树越来越密,北京的轮廓在雾霾里若隐若现,她摸了摸帆布包里那件缝了三个补丁的旧衬衫,心口突然像被稻芒扎了一下。 宿舍煤油灯昏黄的光晕里,王胜利的影子被拉得老长。 这个总爱扛着锄头傻笑的农村小伙,此刻正低着头搓衣角,“你走吧,城里才有电灯电话”。 话音没落就被她拽进蚊帐,粗布床单蹭着胳膊肘的感觉,比割稻子时被蚂蟥咬还让人发麻。 那天后半夜,她偷偷把攒了半年的粮票塞进他裤兜,这个连北京胡同都没见过的男人,还不知道城里的日子要靠这个续命。 胡同里的槐花开得正盛时,于文娟开始吃不下饭。 母亲炖的鸡汤刚端上桌,她就抱着痰盂干呕,白瓷碗沿上的指纹印子,让她想起王胜利递水时总在碗边留的那圈湿痕。 当医生把化验单塞给她时,窗外电线杆上的广播正喊着“恢复高考”,她突然想起那个秋夜,他躺在田埂上指着银河说“文娟你看,星星跟咱村的稻穗一样密”。 绿皮火车再到安徽地界时,于文娟的布鞋已经磨穿了底。 王胜利正在水田里插秧,泥水溅了满脸,看见她的瞬间手里的秧苗“啪嗒”掉在田里。 他光着脚跑过来的样子,让她想起第一次见面时,这个傻子也是这样冲进雨里给她送蓑衣,结果自己淋成落汤鸡。 “你咋回来了?”他的手在裤腿上擦了又擦,最后还是没敢碰她的肚子。 砖瓦房的烟囱升起第三缕烟时,王胜利正蹲在门槛上编竹筐。 儿子趴在他背上数刚学会的字,“爸,这个念‘家’”。 于文娟把晒好的花生倒进簸箕,哗啦啦的声响里,王胜利突然说“那年你走后,我把你宿舍的土都装了半袋”。 夕阳把两个人的影子叠在磨盘上,就像当年在晒谷场看电影时,他悄悄往她手里塞的烤红薯,烫得人心里发慌。 院角的老槐树又开花了,于文娟给孙子讲起那袋花生。 “你爷爷非说北京的花生没有咱村的甜”,她剥花生的手停了停,指腹上的老茧蹭过孙子的脸蛋,“其实啊,甜的不是花生”。 远处传来拖拉机的突突声,王胜利扛着锄头从果园回来,草帽檐下的皱纹里还沾着果霜,就像当年那个站在田埂上的年轻人,眼里盛着比银河还亮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