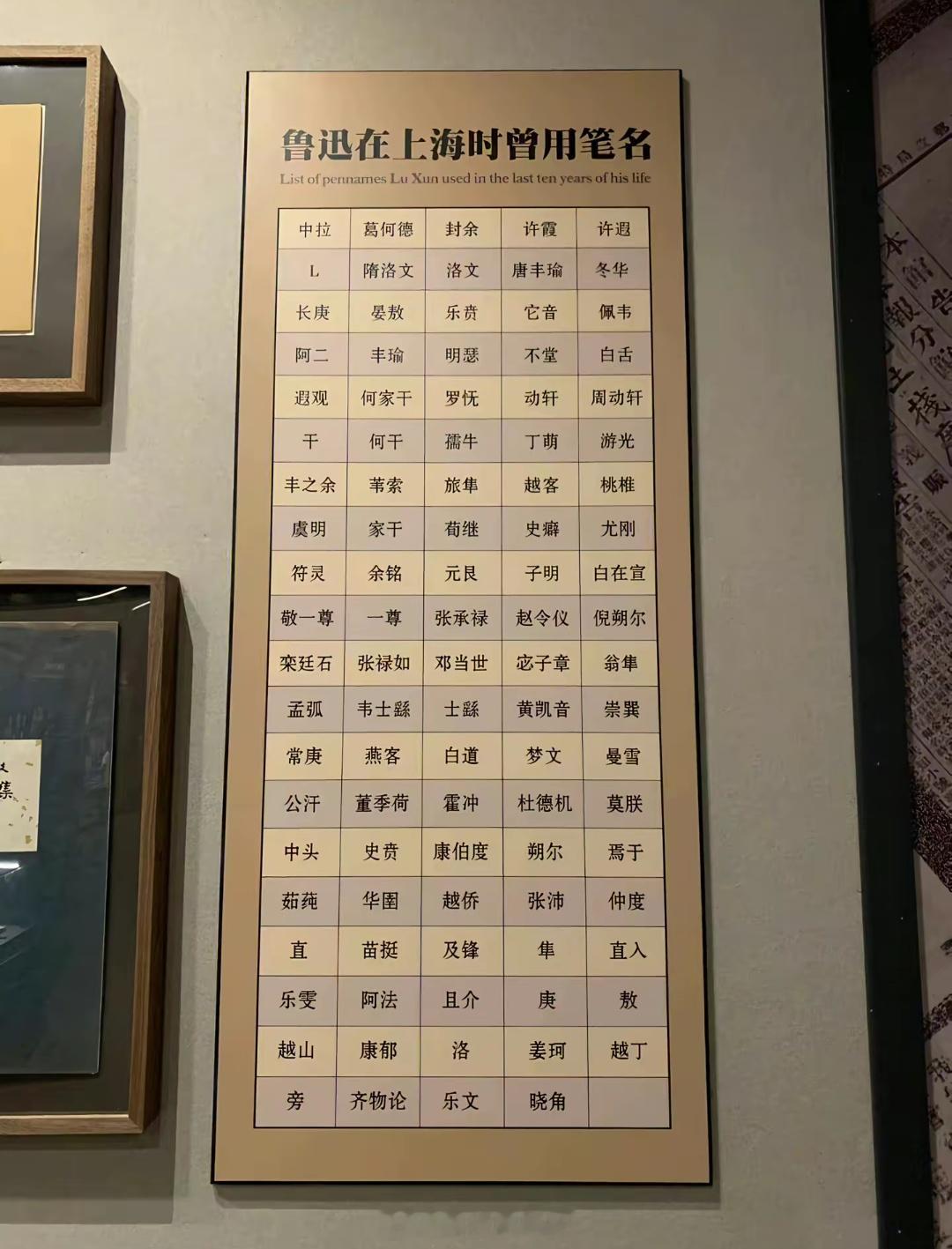清朝有个人花了二十二年,就为了让梁山一百零八将死得一个不剩,其中三十六人被凌迟处死,这个数字恰好对应天罡星数。 而这个人叫俞万春。 然而就在1860年,当太平军攻占苏州后,做了一件让当地文人目瞪口呆的事:他们径直找到当地收藏的《荡寇志》书版,毫不犹豫地付之一炬。 这把火烧得讽刺。 俞万春写作《荡寇志》,本是想用文字扑灭反抗之火,却被反抗之火先烧了个干净。 时间回到1826年,那时候俞万春开始动笔。 他设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都令人震惊的目标:在书里,把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全部、干净地“安排”掉,一个不留。 而且他做得极其讲究,像完成一套残酷的仪式。 三十六位最重要的“天罡星”,必须在东京被凌迟处死,数目要严丝合缝。 在俞万春的笔下,好汉们怎么成名,就让他们怎么败亡。 武神力竭而亡,神箭手被箭射穿,飞石将倒在洋枪下,神医死于庸医之手,神行太保被更快的人生擒。 要知道这种安排绝非随意。 正如写作讲究“凤头、猪肚、豹尾”的章法,俞万春的杀戮设计也遵循着某种内在结构美感。 俞万春的笔像一把冰冷的手术刀,执行着“诛心”。 而且他深谙写作之道,好的叙事需要“冲突”和“对比。 所以武松被三员猛将车轮战,活活累死。 花荣箭术无双,却被人一箭射穿咽喉张。 清飞石百发百中,结果让洋火枪一枪崩了脑袋。 神医安道全,死在庸医手里。 神行太保戴宗跑得快,偏偏遇上跑得更快的康捷,当场生擒。 还有地煞里头,孙立被写得最惨。 俞万春专门让祝家庄后人祝永清、祝万年把孙立抓住,用细钩钩皮肉,用小刀慢慢割,备好盐卤往伤口上浇,怕死得太快还灌人参汤吊命。 那么为什么单单把孙立往死里整? 其实因为当年梁山攻打祝家庄,孙立是卧底,出卖了自己的师兄铁棒栾廷玉,导致祝家庄覆灭。 俞万春年轻时跟着父亲镇压过瑶民起义,深知民团武装对朝廷的重要性。 而祝家庄就是民团。孙立背叛民团,在俞万春眼里,这比杀人放火还要可恨。 为支撑这场杀戮,俞万春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对立神话。 梁山有三十六天罡,他就创造出“雷部三十六将”下凡;梁山有地煞七十二煞,俞万春就配上十八散仙。 在文学创作中,这种对立结构制造了强烈的“冲突感”,这是吸引读者的重要元素。 书里,所有曾被梁山好汉伤害过的角色,祝家庄、曾头市的后人,扈成,乃至小泼皮张保,都组成了一支复仇大军。 他甚至还设计了一对与林冲遭遇相似的父女陈希真和陈丽卿,但他们没有“上梁山”,而是选择剿灭梁山来尽忠。 俞万春想说的很简单:被逼,不是你造反的理由。 而这就把《水浒传》最核心的“逼上梁山”逻辑给解构了。 当俞万春花了二十二年,终于写完了这个“拨乱反正”的故事。 但结局是梁山灰飞烟灭,忠臣良将尽得封赏,天子坐享太平。 他搁笔时,想必长舒一口气,自认完成了一桩捍卫纲常的伟业。 可惜,历史总爱开最辛辣的玩笑。 就在俞万春去世的第二年,太平天国起义的烈火便冲天而起,其规模与破坏力,远非水浒故事可比。 他书中那些被颂扬的“雷部神将”原型人物,在真实历史中或败亡,或变节,声名狼藉。 而他深情描绘的“圣君”宋徽宗,最终的结局是身死异乡,备受屈辱。 最讽刺的一击来自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占苏州后,迅速找到了当地收藏的《荡寇志》书版,付之一炬。 而鲁迅先生后来用八个字评价此书:“文章漂亮,思想煞风景。” 这判语精准。 俞万春的文笔足以描摹生动的打斗场面,唐猛捉豹那一段,写得不比武松打虎逊色。 但他倾注全部心血所要掐灭的,正是《水浒传》里那股让普通人共鸣的、不屈的郁气。 俞万春赢了笔下虚构的战争,却输掉了与真实历史人心的对抗。 因为他或许至死相信,自己用一部小说捍卫了永恒秩序。 然而,文字筑起的堤坝,在时代的洪流前往往不堪一击。 该崩塌的终会崩塌,该奔流的仍将奔流。 优秀的文学作品需要生活感悟力、艺术想象力和文字表现力。 而俞万春有不错的艺术想象力和文字表现力,但他的生活感悟力却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 写作的本质是叙事,而“叙事包括‘故事’和‘话语’两个方面。 故事指的是内容,话语就是形式”。俞万春借用了《水浒传》的故事内容,却赋予它完全不同的话语形式。 他似乎忘了,好的写作需要“写自己感受最深的”,而不是为服务意识形态而生硬创作。 在今天看来,《荡寇志》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旧式文人在时代变革前的固执与局限。 文学的生命力终究来自于真实的人性和时代气息,而非刻意为之的“拨乱反正”。 主要信源:(《荡寇志》王德威:《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