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大学的一节历史课,班主任突然有急事来不了,学校实在没办法,临时找了个快退休的老教授来替课。校长过来跟我们说情况,说这节课来的是位教授,我们当时都赶紧坐直了腰板,心说终于能听一节高大上的课了。 上课铃响过三分钟,老教授才慢悠悠地走进教室。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花白却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没拿课本和教案,只攥着一支粉笔。我们等着他讲那些宏大的历史叙事。教室里很静,只有头顶的老风扇在吱呀呀地转。 他站定,看了看我们,忽然笑了,问:“同学们,你们觉得历史是什么?” 大家有点懵,答案无非是课本里那些。他转过身,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字:“记忆”。粉笔灰在午后的阳光里轻轻飘着。 “我给你们讲个我自己的‘历史’吧,”他放下粉笔,拍了拍手上的灰,“很小的历史。” 他说,1968年,他在甘肃一个村子里,认识了一个叫小杏的姑娘。他们是知青,她是村里唯一念过初中的女孩。他给她讲城里的电车,她教他认地里的野菜。有年冬天,他发高烧,是小杏冒着雪走了十里地,去公社卫生院给他求来了几片药。 “后来呢?”有同学忍不住问。 “后来,”老教授顿了顿,窗外的光正好照在他侧脸上,“1971年,我拿到了回城的调令。走的那天,她在村口的老槐树下送我,塞给我两个热乎乎的煮鸡蛋。她说,‘回去好,回去有前途。’” 他沉默了半晌,教室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我回到城里,写过几封信,都石沉大海。再后来,听说她嫁给了同村一个木匠。”老教授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事,“前些年,我回去过一次。村子变样了,老槐树还在。我见到她了,我们都老了。她领着孙子,在村头晒太阳。聊起以前,她只笑着说,‘那时候,真苦啊。’” 他走回讲台,手轻轻按在粗糙的木面上。“这就是我要讲的历史。不是书上的帝王将相,是一个普通人记得的,两个热鸡蛋,一棵老槐树,和一句‘回去有前途’。历史啊,就是无数个这样的‘记得’堆起来的。你们以后,也会成为别人记忆里的历史。” 下课铃响了。他点点头,慢悠悠地收拾起那支用了一半的粉笔,走出了教室。我们坐在原地,没人立刻起身。阳光把黑板上的“记忆”两个字照得有些模糊,风扇还在转着,不知谁的书页被风吹得哗啦响了一声。 那节课后,我常常会想起那两个煮鸡蛋。原来历史这么近,近到只是一段未曾说出口的牵挂,一次夕阳下的告别。它藏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皱纹里,静静地,等着被一阵风吹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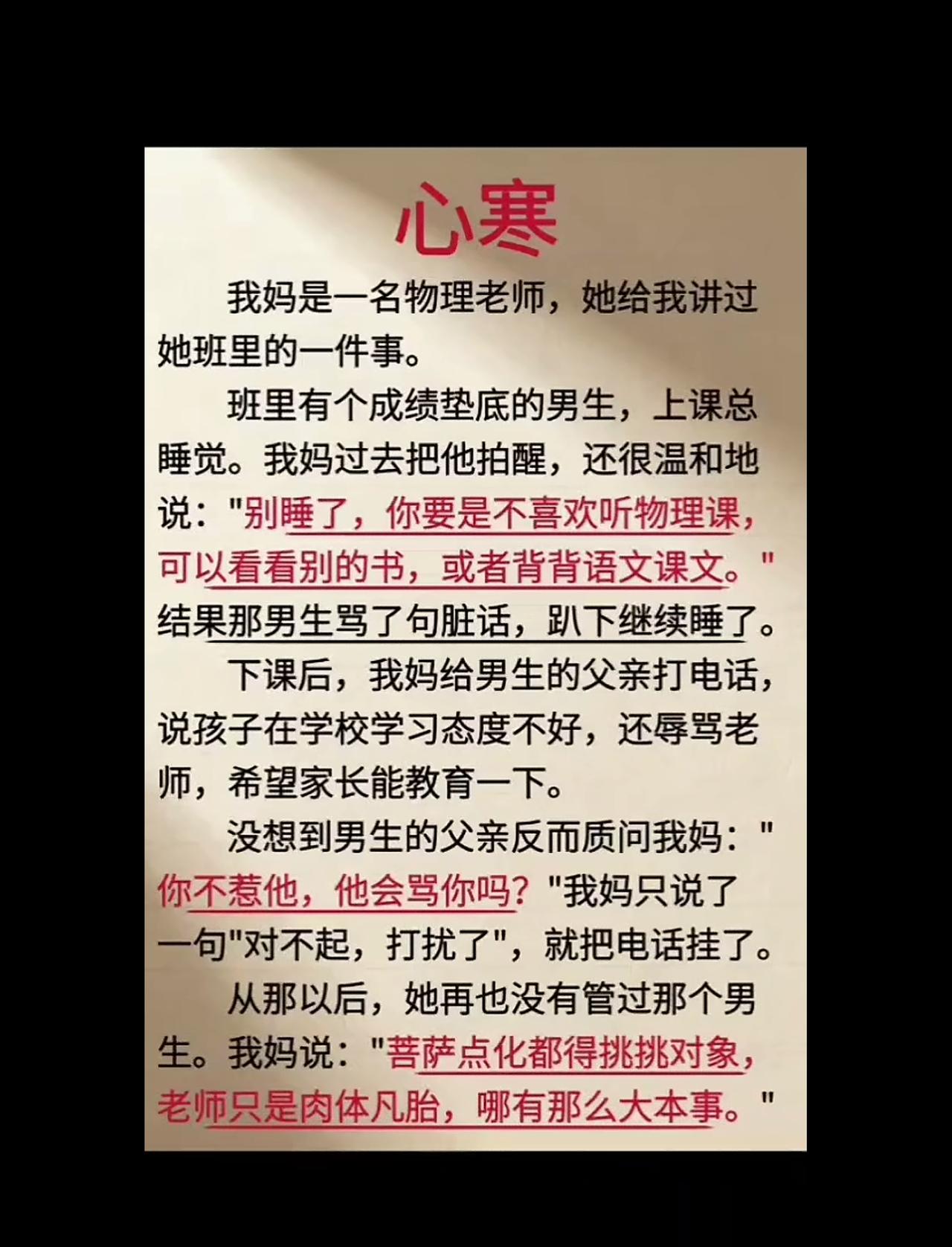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