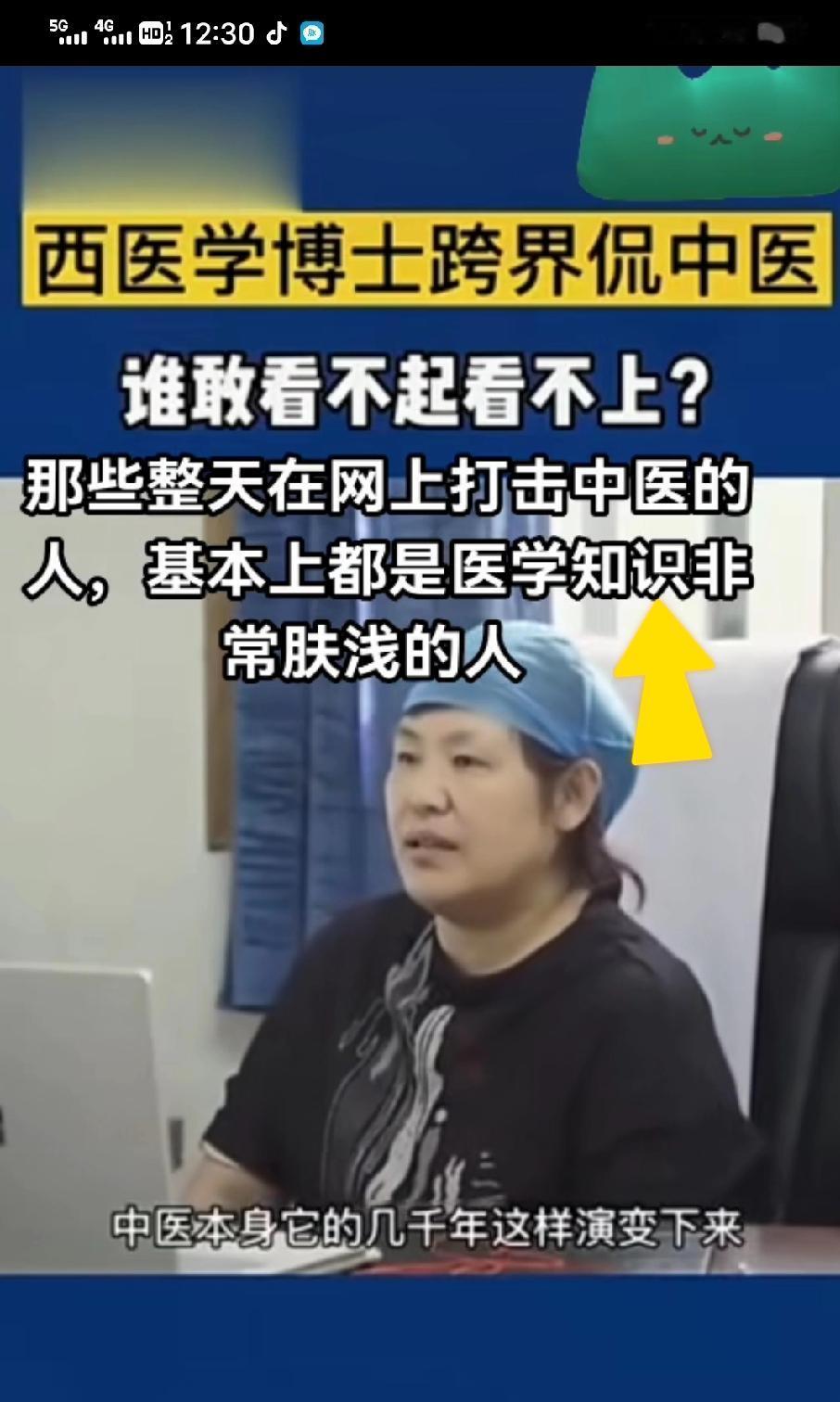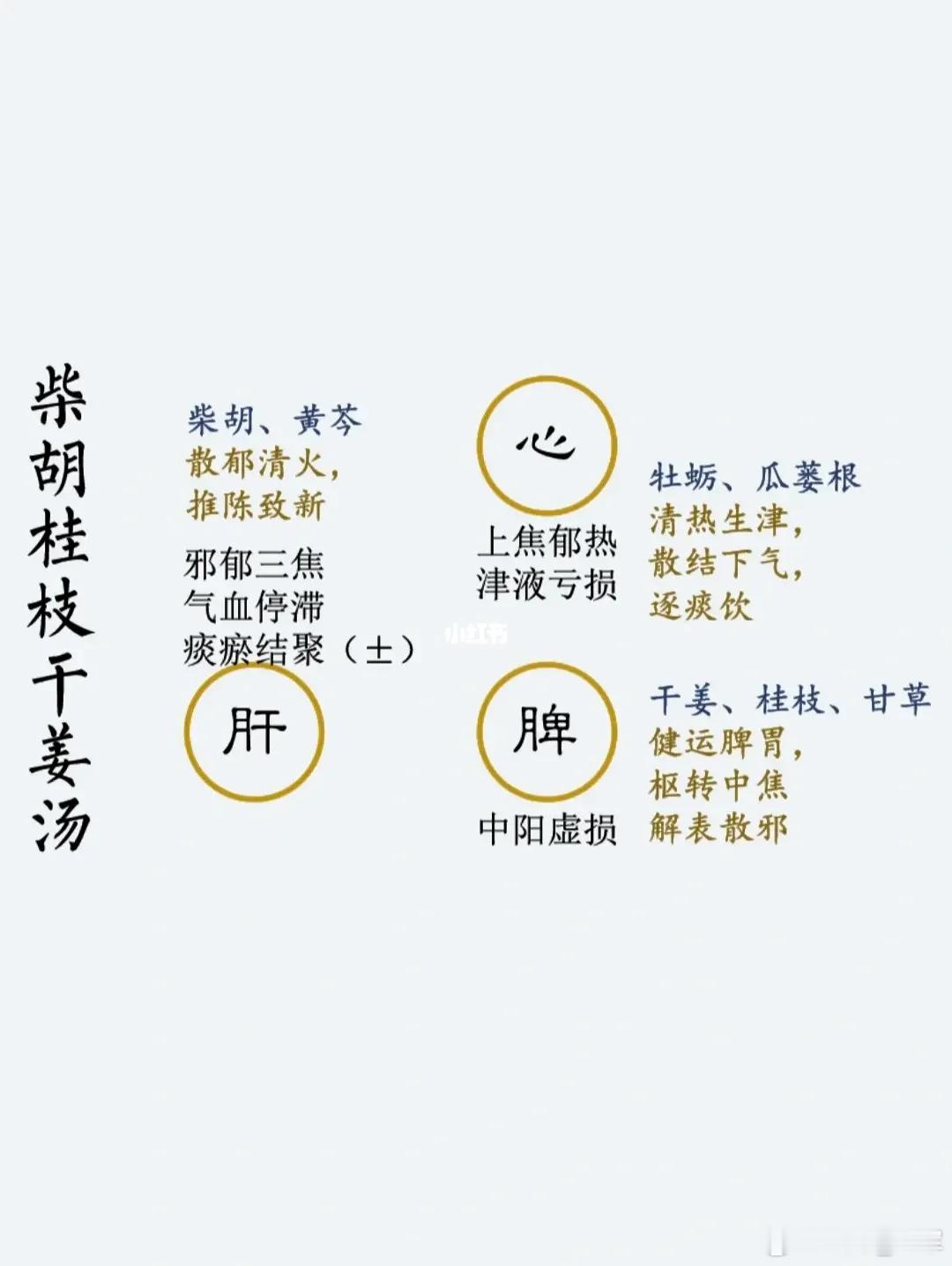《伤寒论》第104条:伤寒十三日不解,胸胁满而呕,日晡所发潮热,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证,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医以丸药下之,此非其治也。潮热者,实也。先宜服小柴胡汤以解外,后以柴胡加芒硝汤主之。
注解:太阳伤寒已十三日不解,胸胁满而呕为少阳柴胡证,日晡所发热为阳明里实证。此属少阳阳明并病,本大柴胡汤证,如与大柴胡汤下之,里外当俱解,而不得利,今反微利者,知医以其他丸药下之,乃非法误治之过。今潮热仍然里实,但以微利,故宜先与小柴胡汤以解其外,而后再与柴胡加芒硝汤兼攻其里。

按:半表半里在里之外,小柴胡汤以解外,是指半表半里的少阳证,不要以为是解太阳在表的证。
《伤寒论》第144条:妇人中风,七八日续得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者,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
注解:妇人患太阳中风证,于七八日时,又续得往来寒热发作有时,而正来潮的月经适于此时而中断,此为邪热乘往来之虚而内入血室,经血即热而中断,故使寒热如疟状而发作有吋,宜小柴胡汤主之。
按:热入血室为证不一,若本条之塞热如疟状发作有时, 为小柴胡汤证,故以小柴胡汤主之。但不要以为小柴胡汤即热入血室的专用方,用其他的方药也可治热入血室。
《伤寒论》第149条: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結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
注解:蒸蒸而振,即蒸蒸觉热,同时并振战恶寒的意思,亦即所谓战汗的瞑眩状态。

伤寒五六日,常为病传少阳的时期,呕而发热,则为柴胡汤证已备,而医以他药下,若柴胡证还在者,可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而不为逆,其人必蒸蒸而振,遂即发热汗出而解。若下后心下满而硬痛者,则已成结胸,宜以大陷胸汤主之。若只心满而不痛者,则为痞,此非柴胡汤所宜,而宜半夏泻心汤。
按:此述误下少阳柴胡汤证而致结胸者,并提出小柴胡汤证、大陷胸汤证、半夏泻心汤证的鉴别法,亦宜细研。
《伤寒论》第229条:阳明病,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胁满不去者,与小柴胡汤。
注解:阳明病,虽发潮热,但大便溏而小便自可,不宜攻下甚明。尤其胸胁满不去,则柴胡汤证还在,故以小柴 胡汤主之。
按:本条所论亦少阳阳明并病之属,日本汤本求真于《皇汉医学》中谓:“以余之实验,则本方不特限于本病,凡一般之急性、亚急性、慢性胃肠炎,尤以小儿之疫痢,消化不良证等,最有奇效。
若效力微弱时宜加芍药;有不消化之便或粘液、粘血便时,宜加大黄。有口舌干燥、发热、烦渴等证时,当加石膏。盖余根据本条及下条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及黄芩汤、黄芩加半夏生姜汤、白虎汤诸条,潜心精思,综合玩索而得之者也。此说甚佳,颇能发挥古方之用。
经方大家胡希恕老师小女六岁时患中毒性痢疾,高烧40度,住院输液、 用西药治疗,高烧不退、并令转传染病院。时已过夜半,无法叫车,乃负之归家,与大柴胡加石膏汤,次日即愈。又以小柴胡加生石膏汤,治一重笃的噤口痢,七八日未易一药而愈,今并附此以供参考。

《伤寒论》第230条: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苔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岀而解。
注解:阳明病,虽不大便,但舌苔白而不黄,热还未尽入里。胁下硬满而呕,更是柴胡之证,此亦少阳阳明并病,故可与小柴胡通其上焦,则津液得下,胃气自和。上下既通,表里气畅,故身当濈然汗出而解。
《伤寒论》第231条:阳明中风,脉弦浮大而短气,腹部满,胁下及心痛,久按之气不通,鼻干,不得汗,嗜卧,身及目悉黄,小便难,有潮热,时时哕,耳前后肿,刺之小差。外不解,病过十日,脉续浮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无余证者,与麻黄汤,若不尿,腹满加哕者,不治。
注解:弦为少阳脉,浮为太阳脉,大为阳明脉。短气腹部满、胁下及心痛、久按之气不通,属少阳证;鼻干属阳明证;不得汗属太阳证;嗜卧属少阳证;一身面目黑黄、小便难为黄疸病,有潮热、时时哕属阳明证;耳前后肿属少阳证。据以上的脉证,显系三阳合病而并发黄疸和腹水。刺之小差, 谓经过针刺治疗证稍减轻,病过十天而脉仍续浮者,可与小柴胡汤。若脉但浮而无余证者,可与麻黄汤。若上之腹水证,虽利其小便而终不尿,腹仍满,并加哕逆不已,则胃气已败,故谓不治。
按:本条似述黄疸并发腹水而现三阳合病的重证,与小柴胡汤固无不可,但麻黄汤之用,殊难理解,其中必有错筒,故于麻黄汤删去此条。实践证明,黄疸型肝炎并发腹水者,确多预后不良,谓为不治并非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