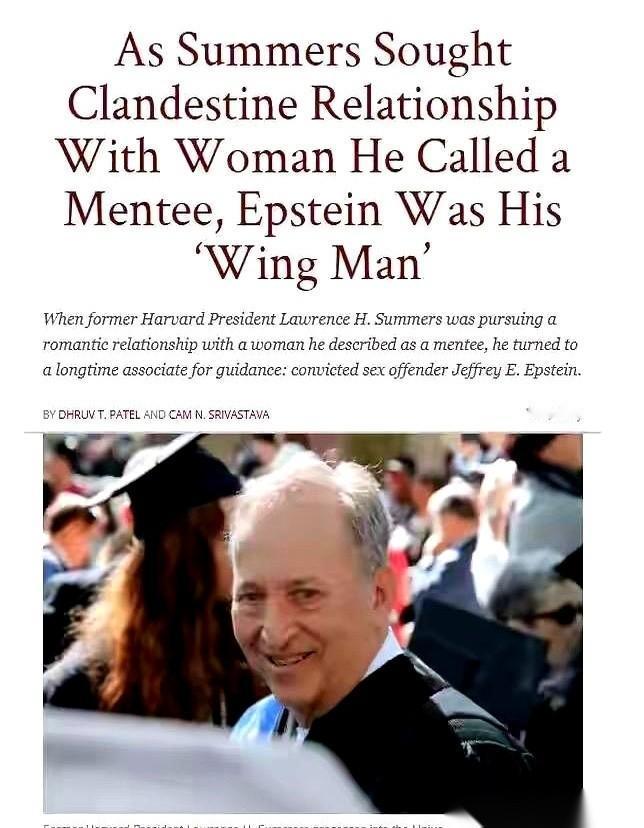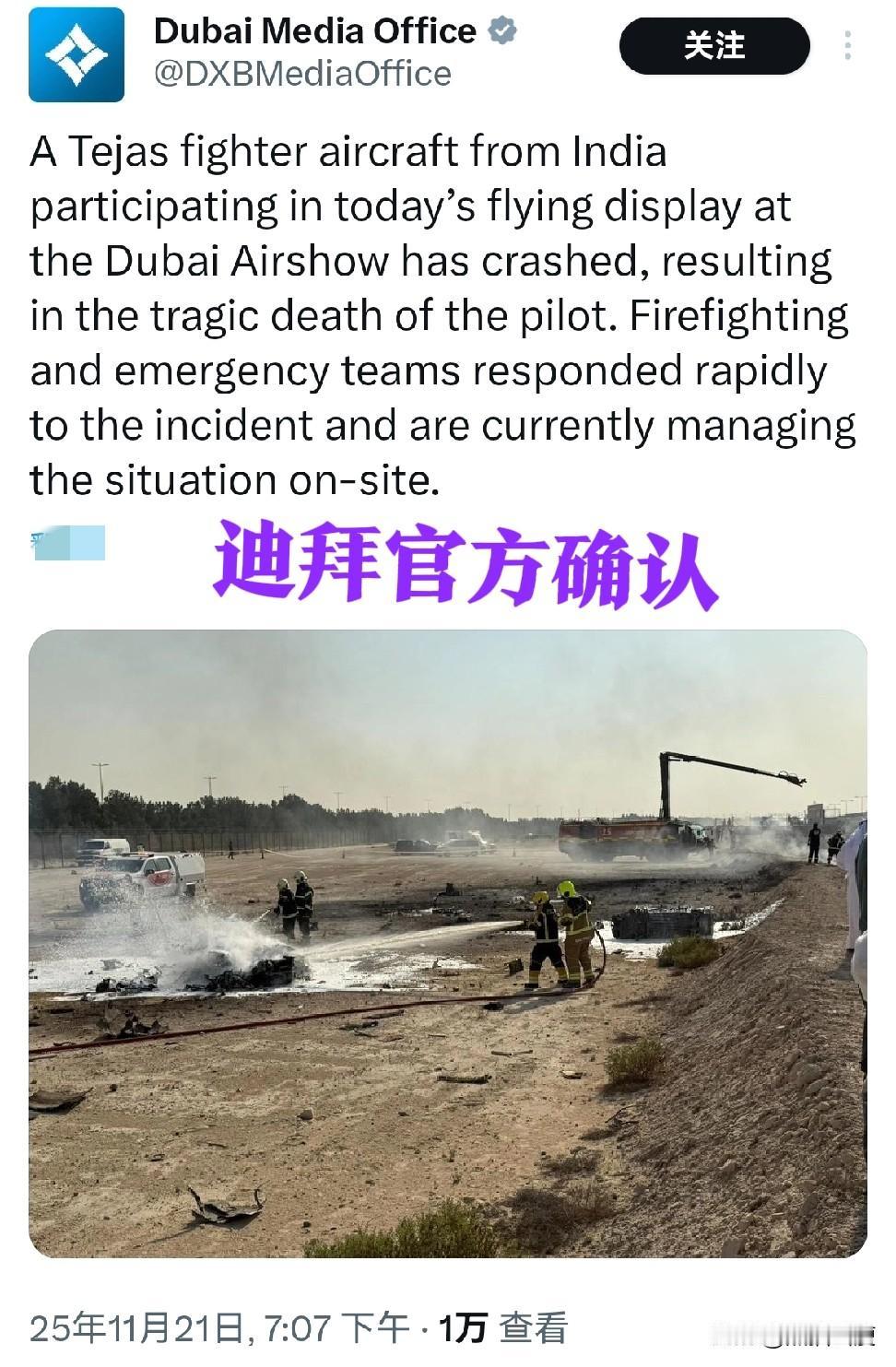义结金兰
唐末年间,福州南台镇,云烟环绕,闽江之水映着天光。镇中有二少年,谢必安和范无咎。谢必安身材高瘦,性情温和,面白如玉;范无咎却黑面短躯,直爽耿直。二人自幼同窗共读,虽家境迥异,却情同手足。
少年时,二人常结伴行善。遇孤寡则捐衣施饭,见不平则拔刀相助。谢必安常道:“人活于世,安于心则安于命。”范无咎笑答:“若有不义之人,我便使他无救!”两人相视大笑,自此立誓——“同生共死,不负此心。”
镇上人皆称他们为“信义二友”。

暴雨之约
一日夏末,闷雷滚动,乌云压顶。二人听闻有户人家被歹人欺诈,他们便一同前往行侠仗义。路过南台桥的时候。江风忽起,天色骤暗。
谢必安望天,说道:“恐将有雨,我家离此不远,我取伞来。”范无咎笑道:“好,我在桥下等你。”
“无咎兄稍候,我去去就回。”
谢必安脚步匆匆而去。然天怒突至,雷霆震野,暴雨如注,江水一刻之间暴涨如魔。
桥下浪翻,水声轰鸣。范无咎立于水边,衣袂尽湿,却仍仰头望着桥头的方向。路过的百姓劝他:“范爷,桥下危险,速速远离江边!”他摇头:“七爷言会回,我若先走,便失信于义。”
水涨至腰,涨至胸,涨至颈。范无咎终仍不动,直至浪卷其身,沉入闽江暗流之中。
那一刻,风雨撕天,雷火照亮水面,唯余他最后一句低语:“必安兄,信我——我未违约。”

殉义成魂
待谢必安携伞而返,江畔早成汪洋。
桥下无人,唯见断草随波。
他沿江狂奔呼喊,嗓音撕裂。路过的百姓劝他:“范爷恐已…”他却不信,只一遍遍呼:“无咎兄…无咎兄…”
至夜半,雷声止,江面平。月光似银,照出水中漂浮的青布衣角。谢必安扑入江中,抱出冰冷的尸体,放声痛哭。
哭声惊动城隍庙中的香火。殿中神像似也垂泪。
翌日清晨,谢必安披麻戴孝,立于南台桥头,自系白绫,向天立誓:“若有来世,我愿与无咎兄并肩,行于天地之间,不负信义,不负此生。”
言毕,踢断桥柱,自缢而亡。血落舌下,舌长垂胸,面色苍白,形容凄绝。
地府封命
阴风起,天地寂。两魂同入冥府,阎罗王亲临殿上。
阎罗王看到二魂,叹曰:“此二人,生于凡尘,义重山海。范无咎死于信,谢必安亡于义。信义二字,正是人间根本。”
于是赐封:谢必安为“白无常”,职司阳魂勾摄;范无咎为“黑无常”,职司阴魂拘捕。
一白一黑,阴阳互济,自此镇守城隍门下,行走人间,专勾恶魂,不扰善者。
阎罗王又曰:“白者象明,黑者象幽;谢者酬信,范者警戒。酬谢神明,则必安;犯法害人,则无救。”
两人叩首,谢曰:“愿尽职于阴阳,常存义于生死。”

南台桥下的风
自此之后,凡有行旅至南台桥下,夜半可闻阴风轻吟,似有二人笑语。
“必安兄,雨似小了。”
“无咎兄,伞我已取来。”
风声渐远,化为幽幽铃响。人间信义,亦随之长存。
有说桥边常见白身黑影一长一短,前者笑颜,后者肃面,巡夜而行。见善者拂袖安抚,见恶者冷目拘魂。人称——“白黑无常,信义二使。”
他们不只是阴司的勾魂者,更是人世信义不灭的象征。
尾声
谢必安之“白”,非仅肤色之白,而是“心存明照”;范无咎之“黑”,非仅面貌之黑,而是“行守至正”。
白者安魂,黑者断恶;一笑一怒,皆为公正。
他们行走千年,提醒世人:“世有信义,生死皆安;若弃信义,天命难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