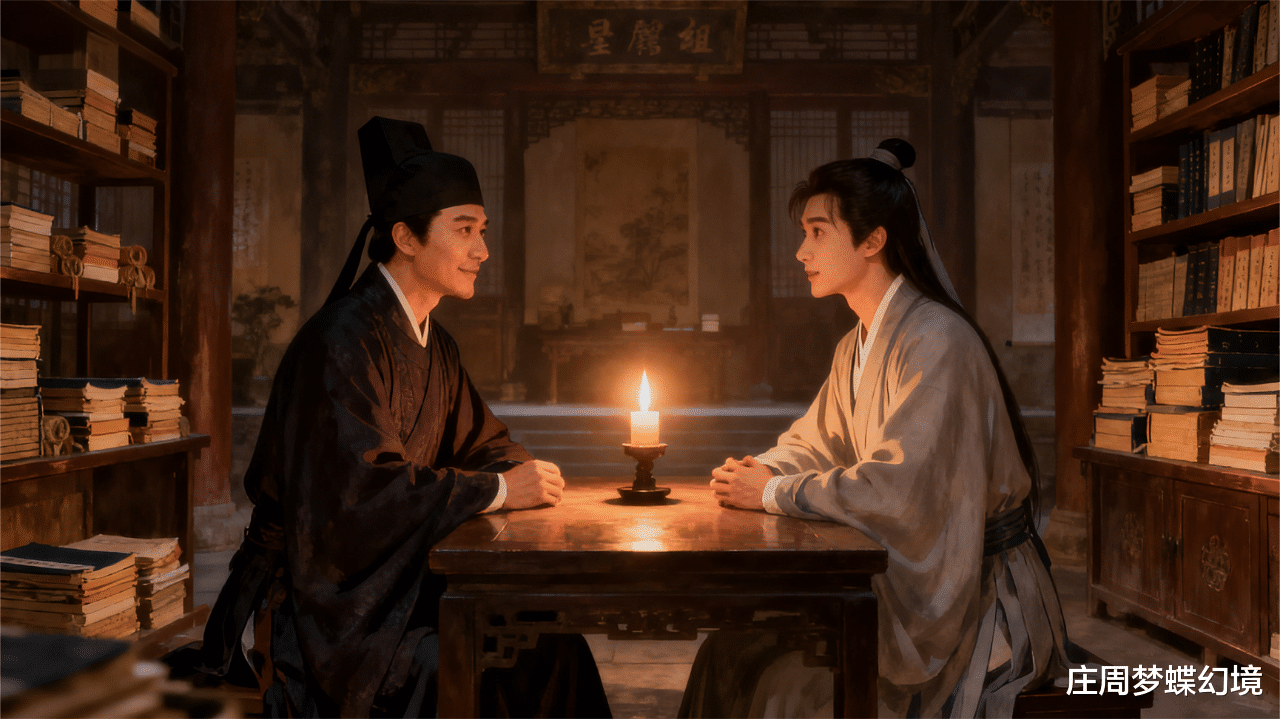才高不遇困科场,魂随知己证文章;寒士孤魂酬知遇,半生沦落诉荒唐;文冠当时偏命舛,魂归功名慰孤肠;一第难酬平生志,魂魄犹为
才高不遇困科场,魂随知己证文章;寒士孤魂酬知遇,半生沦落诉荒唐;文冠当时偏命舛,魂归功名慰孤肠;一第难酬平生志,魂魄犹为知己忙;科场误尽英才路,魂逐丁公吐气扬。
(正文开始)
河南淮阳有个姓叶的书生,没人知道他的全名。他写的诗文在当时堪称一绝,可就是时运不济,多年在科举考场上蹉跎困顿,始终没能出人头地。

恰逢关东人丁乘鹤来淮阳当县令,读到叶生的文章后,大为惊叹,立刻召见他面谈。一番交流下来,丁县令对他越发赏识,不仅让他住进县衙里安心读书,还时常送钱送粮,帮他贴补家用。赶上省里的科试,丁县令在学政官面前极力举荐叶生,他果然拔得头筹。丁县令对他期望极高,乡试结束后,特意找来他的考卷细读,一边拍着桌子一边赞叹写得好。谁料命运弄人,就像杜甫说的“文章憎命达”,好文章偏要妨害好运气。放榜那天,叶生还是名落孙山。他失魂落魄地回了家,想到辜负了丁县令的知遇之恩,更是羞愧难当,没过多久就瘦得皮包骨头,整日呆坐着像尊木偶。丁县令听说后,赶紧把他叫来安慰,叶生却只是不停地掉眼泪。丁县令怜惜他的才华,约定等自己任期满后回京,就带他一起北上。叶生又感激又敬佩,辞别县令后就闭门不出,再也无心应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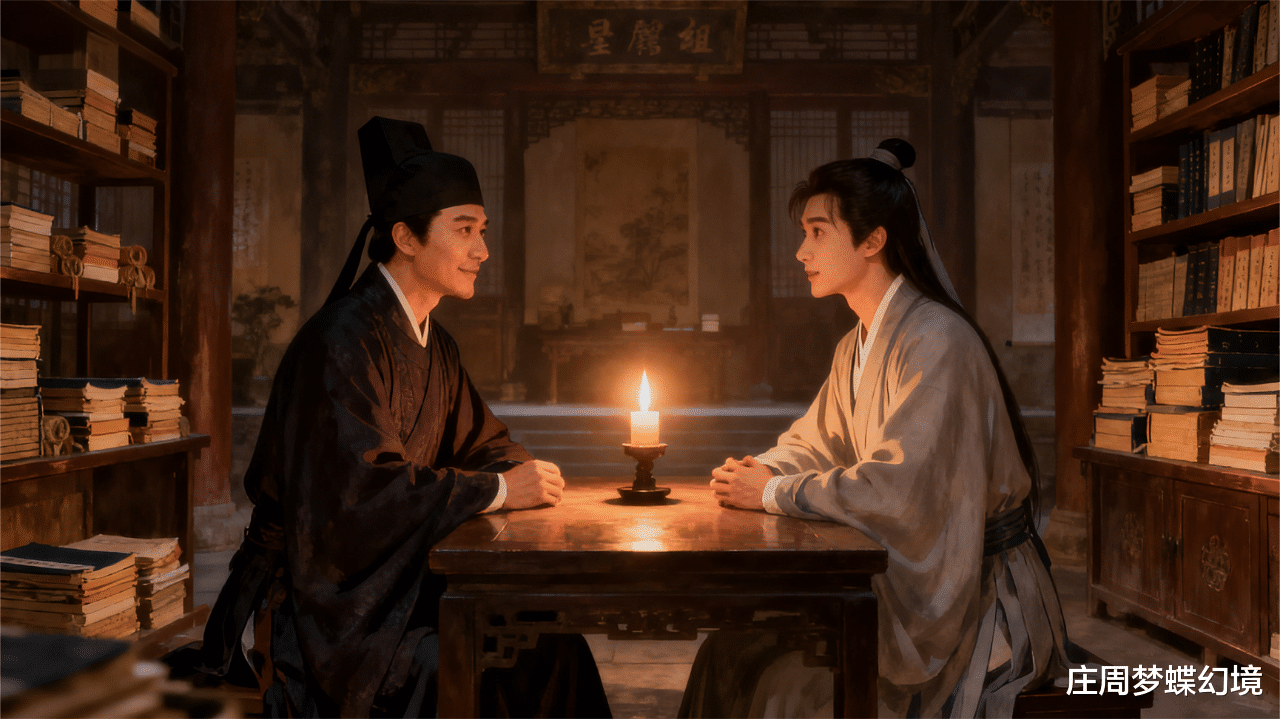
没几天,叶生就一病不起。丁县令时常派人来看望送药,可吃了上百副药,病情始终不见好转。这时恰逢丁县令因为顶撞上司被罢官,正要卸任返乡,他特意写了封信给叶生,大致意思是:“我不久就要回东边老家了,之所以迟迟不动身,就是在等你。只要你早上能来,我傍晚就出发。”信送到叶生床头,他捧着信纸痛哭流涕,托送信人回复:“我病得太重,怕是一时好不了,您还是先走吧。”丁县令听了回话,却不忍心独自离去,依旧耐心等着。又过了几天,守门人突然来报,说叶生到了。丁县令又惊又喜,连忙出门迎接。叶生愧疚地说:“我这点病拖累您久等,心里实在不安,幸好现在能跟您走了。”丁县令当即收拾行装,次日一早就出发了。

回到老家后,丁县令让儿子丁再昌拜叶生为师,日夜跟随他学习。当时丁再昌才十六岁,还不会写文章,但天资极聪颖,凡是学过的诗文,读两三遍就能背下来。跟着叶生学了一年,就能下笔成文了。加上丁县令四处打点,他顺利考进了县学,成了秀才。叶生把自己多年为科举准备的范文全都整理出来,教给丁再昌。后来乡试时,考题竟然和叶生教的七道题一模一样,丁再昌一举考中了亚魁。有一天,丁县令对叶生感叹:“您只拿出一点本事,就让我的儿子出人头地,可您这样的大才却一直被埋没,这可怎么办啊!”叶生却说:“这大概是命中注定吧。能借着您家的福运,让我的文章扬眉吐气,让天下人知道我半生落魄,不是文章写得差,我就心满意足了。况且读书人能得一知己,本就没什么遗憾,何必非要穿上官服,才算功成名就呢?”丁县令见叶生长年在外,担心耽误他回原籍参加岁试,就劝他回乡。叶生听后脸色黯然,显得很不高兴。丁县令不忍心勉强,就嘱咐儿子到京城后帮叶生捐个监生资格。后来丁再昌在京城会试中又考中了,被任命为部里的主政官,他带着叶生一起进了国子监,朝夕相伴。过了一年,叶生以监生身份参加顺天府乡试,终于考中了举人。

恰逢丁再昌被派到南河负责治水事务,他对叶生说:“这次去的地方离您家乡不远,您如今功成名就,正好衣锦还乡,多痛快啊!”叶生也很高兴,选了个吉日动身。到了淮阳地界,丁再昌派车马送叶生回家。叶生看着自家萧条的门户,心里一阵酸楚。他犹豫着走进院子,妻子正拿着簸箕出来,一见他就吓得扔掉簸箕,转身就跑。叶生凄然喊道:“我现在考中举人了!不过三四年没见,你怎么就不认识我了?”妻子远远地喊道:“你早就死了,别胡说什么中举!我之所以一直没把你下葬,是因为家里穷、孩子小。如今大儿子也长大了,正要找地方安葬你,你别装神弄鬼吓唬人!”叶生听了这话,顿时愣在原地,满心怅然。他慢慢走进屋里,看见自己的棺材赫然摆在那里,刚一扑过去,身体就消失了。妻子惊得回头,只见他的衣帽鞋袜像蝉蜕一样掉在地上,当即大哭起来,抱着衣服悲痛欲绝。

儿子从私塾放学回来,看见门口停着车马,打听清楚来历后,吓得飞奔回家告诉母亲。母亲流着泪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又仔细询问丁再昌的随从,才知道前因后果。随从回去复命,丁再昌听后,眼泪直流,立刻驾车赶到叶家吊唁,拿出钱财为叶生操办丧事,按照举人的礼仪将他安葬。他还送给叶生儿子一大笔钱,请了好老师教他读书,又在学政那里为他打点。过了一年,叶生的儿子也考进了县学。蒲松龄评论说:“为了知己,连自己死了都忘了吗?听到的人可能会怀疑,但我深信不疑。心意相通的女子,能为情魂离躯体;相隔千里的好友,在梦中也能认出相见的路。更何况文章笔墨凝结着读书人的心血,这种精神共鸣,本就关乎我们的性命啊!“可叹啊!知音难遇,时运不济。身影孤单时,只能对着影子发愁;傲骨铮铮者,只能自我怜惜。失意时连面目都显得可憎,连鬼怪都来嘲弄;屡次落榜后,再好的文章也被挑出毛病。古往今来,因怀才不遇而痛哭的人,叶生就像当年献玉被砍脚的卞和;那些被埋没的奇才,又能遇到谁来当识才的伯乐呢?

“怀抱着名片求人,字迹都磨掉了也无人理睬;侧身远望,天下之大竟无容身之处。人活在世上,也只能闭眼随波逐流,听凭命运摆布罢了。天下像叶生这样才华出众却沦落失意的人,还有很多,可又能去哪里找丁乘鹤这样的知己,让人甘愿生死相随呢?唉!”
(正文完)
蒲松龄笔下的鬼神狐魅,从非荒诞虚妄的迷信之说,而是寄寓孤愤的现实镜像。正如《叶生》中的魂魄相随,本质是才士对知己之遇的赤诚、对功名未竟的不甘,更是对科举制度扼杀人才的沉痛控诉。那些跨越生死的执念,不过是封建时代底层文人的心声呐喊 —— 当正道难行、才华难伸,便只能借幽冥之境,求一份公道与认可。拨开神异的面纱,我们看见的是世道的不公、人心的向背,以及千百年来未曾消散的 “士为知己者死” 的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