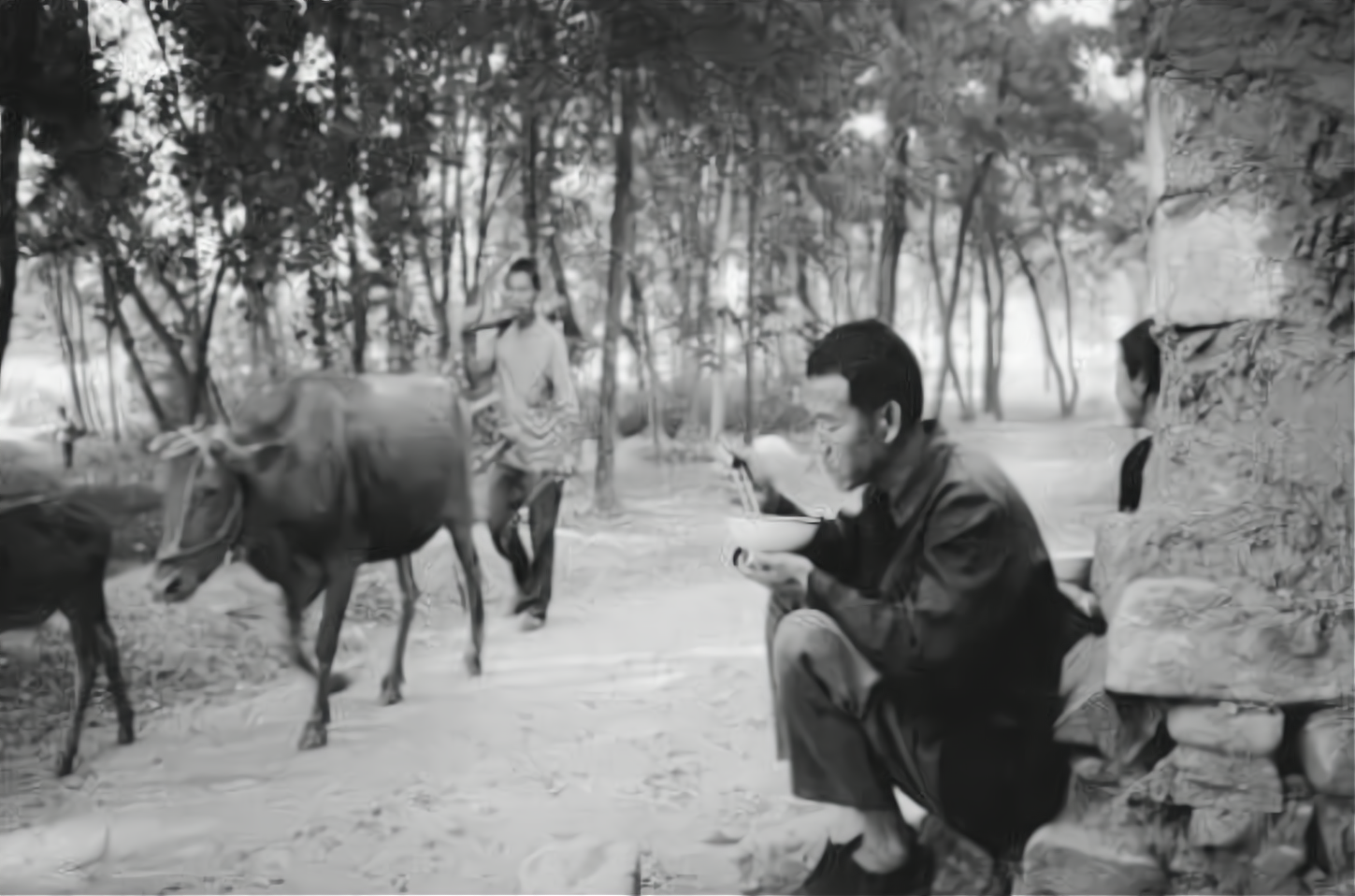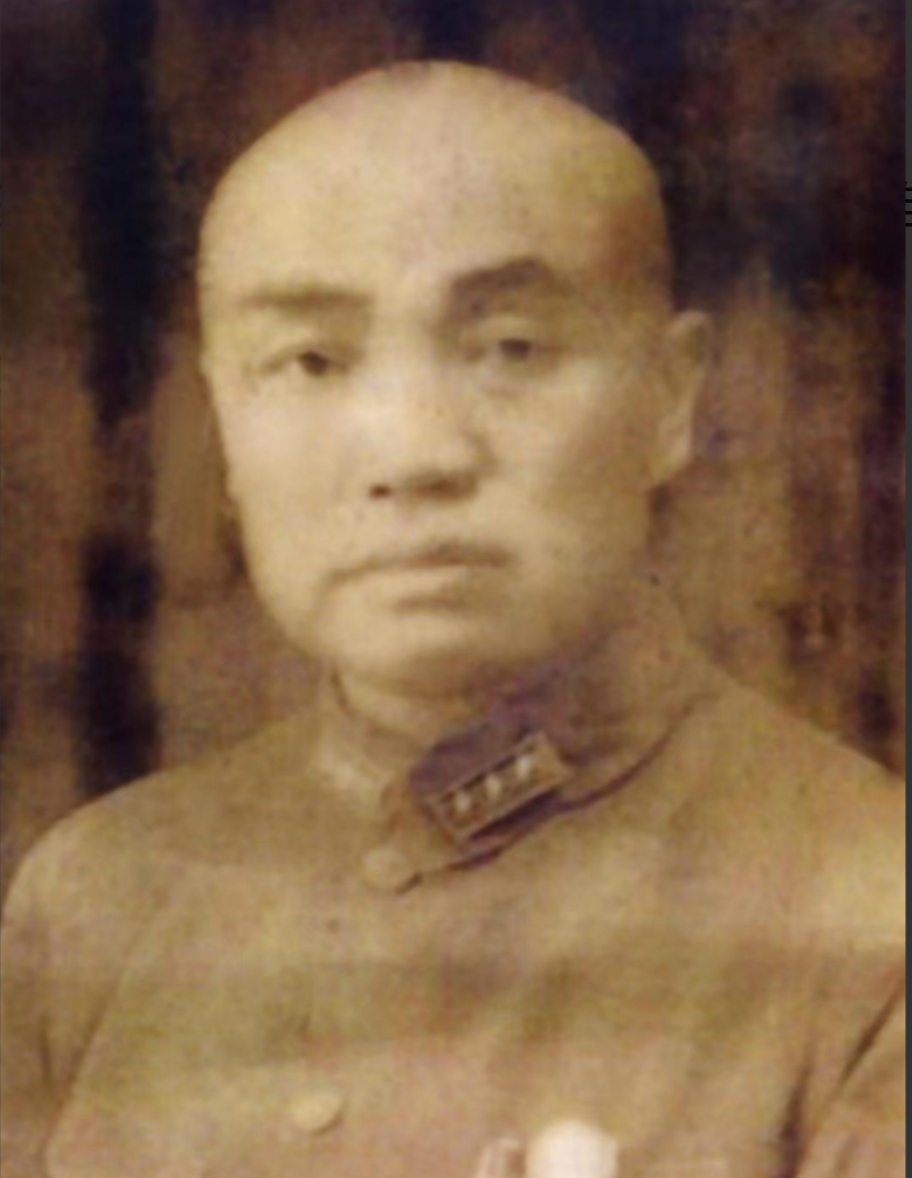1947年8月,6纵17旅旅长率部解放了家乡,请假回乡探亲。旅长荣归故里,他的叔叔做了1碗面条招待,还在面条上放上了1块发黑的鸡肉块。
那年的中原大地正处在解放战争的转折点上,刘邓大军遵照中央指示,正朝着大别山方向实施战略挺进。
在这支队伍里,六纵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刚刚率部攻克豫南新集镇,正站在临时指挥所门口向师长请假,他老家所在的柴山堡距离新集镇仅三十里地,这是自1932年离家参军后,十五年来首次有机会踏上故土。
得到师长批准的李德生带着警卫员匆匆上路,正值盛夏午后,蝉鸣声裹着热浪扑面而来。两人沿着崎岖山路疾行,军装后背早被汗水浸透。
随着记忆中的村落轮廓逐渐清晰,李德生的脚步反而迟疑起来,本该炊烟袅袅的时辰,整个村庄却寂静得反常,连声犬吠都听不到。
村口老槐树下突然闪过人影,戴着破草帽的老汉正要往林子里钻,被警卫员三步并作两步追上。
当李德生看清老汉布满皱纹的面容,喉咙顿时发紧,这是他亲叔叔李长顺。十五年前离家时还壮实的汉子,如今佝偻着背,脸上新添了道寸长的刀疤。
跟着叔叔走进村子的路上,李德生终于知道了这些年乡亲们的遭遇:自从他参加红军,还乡团三天两头来搜捕,父母在第三次围剿时被活活烧死在老屋里。
如今整个柴山堡家家户户都像惊弓之鸟,听到点动静就往山里躲,看着路边坍塌的土坯房和荒草丛生的田地,这位在战场上指挥若定的旅长红了眼眶。
听说李家小子当了大官回来,村民们陆续从藏身处探出头来,他们围在村头晒谷场上,看着李德生身上打着补丁却整齐干净的军装,眼里既有羡慕也有畏惧。
几个光屁股娃娃躲在大人身后,偷偷摸着警卫员腰间的皮带扣。
李长顺把侄子领进自家茅屋,说是要准备接风饭,说是家,其实就半间草房,土墙上挂着几串发霉的玉米,墙角堆着半袋糠皮。
老汉从灶台底翻出个粗陶碗,用葫芦瓢舀了瓢井水冲了冲,转身从房梁上取下个油纸包,里面躺着块黑黢黢的咸鸡块,表面结着盐霜,看样子至少存了两年。
当两碗清汤寡水的杂粮面端上桌时,每碗面上都摆着片黑乎乎的鸡肉,李德生捧着豁口的陶碗,注意到叔叔布满裂口的手指在微微发抖。
警卫员嚼到发硬的咸肉时差点硌了牙,刚要开口就被旅长用眼神制止,这顿饭吃得安静,只有竹筷碰碗的叮当声。
返程路上,李德生把身上所有边区票都塞给了叔叔,这个在战场上见惯生死的汉子,望着山坡下破败的村落,第一次和警卫员说起家乡的老规矩:逢年过节切两片咸肉摆在客人碗里,客人懂事就会把肉放回灶台,那是全村人共用的门面,要留着招待下一拨客人。
警卫员摸着鼓鼓的胃袋,想起自己吃掉的那块咸肉,脸上火辣辣地烧。
这次探亲给李德生的震动不亚于任何一场战役,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已成为开国少将的他仍保持着每月往老家汇钱的习惯。
村里后来用这些钱重修了被烧毁的祠堂,在废墟上建起小学,当年躲在大人们身后的光屁股娃娃,如今正坐在教室里念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