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曙光集》的时候,我没有习惯性地查看一下目录,找一找有多少篇是我没有读过的,从而为自己减轻一些心理负担。因为通过事先的翻阅,我已经意识到这是一本全新的书,其中的每一篇、每一个细节都透着作者杨振宁先生和编译者翁帆女士的细致和用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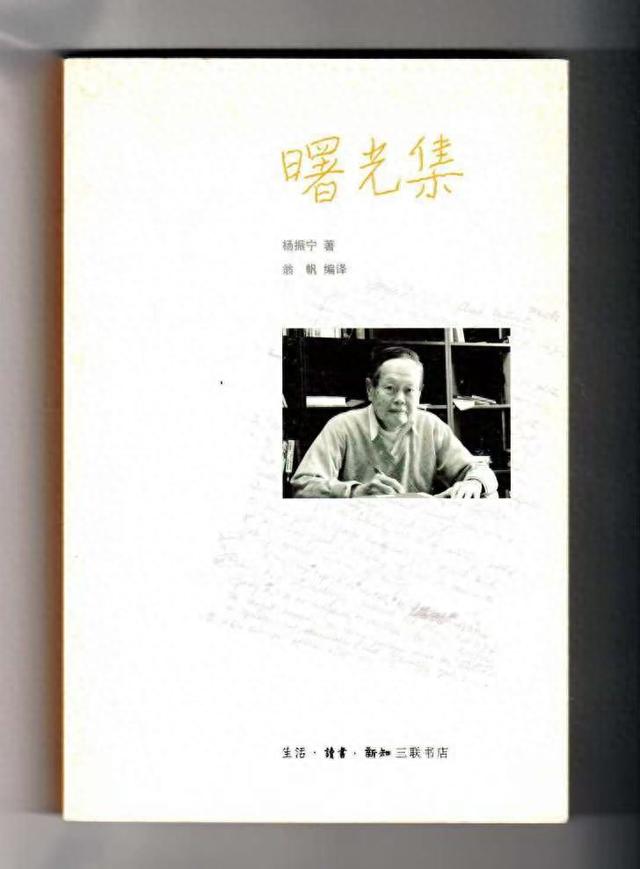
《曙光集》应该是继1983年出版的英文版《杨振宁论文选集》之后,杨振宁先生亲自深度参与编写的又一本书,51篇文章里,包括杨先生的个人作品,媒体访谈,别人的书信和文章,其中22篇有杨先生写的后记,这种做法无疑是英文版《杨振宁论文选集》的延续,很有意义,也很好看。这些后记无论长短,均言之有物,不可或缺。有些学术性强一些的文章不是很看得懂,但我会很认真地读一读杨先生的后记,从而得到一些信息和收获。
如果说在此之前读杨先生的作品,在意的是专业知识、杨先生的经历、观点和见解,那么在《曙光集》里,我读到更多的是文学的韵味和精彩。简洁干脆的文字透着非同一般的才华和激情,对于一位80多岁的老科学家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
从《前言》开始,这种非常的感觉便呈现出来,整篇文章的架构和立意让人耳目一新,大开大合的同时,给人以启发和思考。真正的大家手笔,华彩文章。
从鲁迅那段“假如一间铁屋子”,到王国维的遗嘱,再到陈寅恪的挽词及其1938年南迁蒙自后写的诗《南湖即景》,然后杨先生写道:
鲁迅、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个长夜。我和联大同学们就成长于此似无止尽的长夜里。
幸运的,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我今年八十五岁,看不到天大亮了。翁帆答应替我看到……
杨先生写于2007年底的这篇《前言》,让我感觉到一种高度和力量,同时也有那么一些遗憾甚至伤感。一句“翁帆答应替我看到”,让人不免百感交集。
从一些新的文章、信件里,我们可以看到杨先生并不是无原则的、盲目的歌颂派,他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他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因为出发点是公心,所以他没有什么顾忌。
在《吴健雄致杨振宁的一封信》的后记里,杨先生写道:“我曾经说过科学研究要成功,有三个必要的条件:眼光、坚持、动力,吴健雄确是三者具备。……而最重要的是她的眼光:当时许多别的一流物理学家都认为这么困难的实验,做出来只不过是再证明宇称确实是守恒,不值得去做。可是她‘独具慧眼’,认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不守恒过去既未被人研究过,那么不论结果如何,这就是值得做的实验。这是她眼光过人的地方。”
应该说,眼光、坚持、动力,是科学研究成功的必要条件,也是我们做成很多事情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杨振宁先生和吴健雄先生都是我们的榜样。
《曙光集》里两篇杨先生的学生和同事写的文章《杨振宁对我的教育》《杨振宁——一个保守的革命者》都很值得一读,它们可以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杨振宁先生。
他的学生,也是他第一个研究生回忆起和杨先生在一起的日子,有这么一段话:“就这样日复一日,从来没有如此努力工作,也从来没有如此感到快活。办公室的气氛非常温馨、安静,连空气也充满着智力的亢奋。许多出色的工作得益于那种讨论的氛围,而且,说真的,那种气氛一直到今天仍是出成果的源泉。”
他的同事在文章里写道:“杨教授是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20世纪物理学的卓越设计师。从当年在中国当学生到以后成为石溪的哲人,引导他思考的,一直是他对精确分析和数学形式美的热爱。这热爱导致了他对物理学最深远的和最有创见的贡献——和米尔斯发现的非阿贝尔规范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所发现的非阿贝尔规范场已渐渐成为比宇称不守恒更美妙、更重要的贡献。”
应该说,这样的回忆和评价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杨振宁先生,了解这位我们身边的科学巨人的人格魅力和巨大成就。
收录书中的几个访谈也很全面和精彩,即便是面对对中国不那么友好的记者,杨先生都能够给予坦率、准确的回答,客观的讲述、理性的分析,动情之处、深情之处,都相当感染人。
杨先生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到他一生中很多的“幸运”,并说“一生这么多幸运很少有的”。的确,在杨先生百年人生中,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研究,一直都比较幸运和顺利的。但是,如果换以一个思路,我们会发现,杨先生那么多的“幸运”与他的父母点拨、教育和帮助,以及他自身的努力与坚持分不开的。一个人即便是天资过人,如果没有“努力和坚持”,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杨先生的“幸运”不仅是偶然,也不仅是运气。他以自己的速度“赶上了”,他以自己的敏锐“抓住了”,他以自己的恒心“等到了结果”,他以自己的毅力“坚持到了最后”。
他是幸运的,他更是智慧的。
《曙光集》由生活·读者1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8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16开平装。2018年9月出版了“十年增订版”,16开精装,封面的红色显得沉稳喜庆,大气而厚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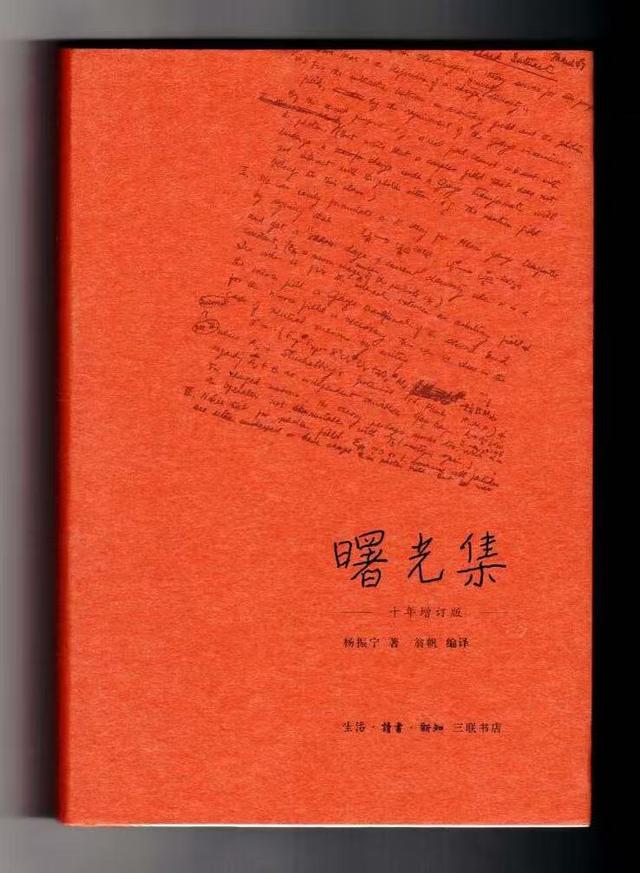
增订版增加了6篇文章,包括排在卷首的《物理学的未来》以及《谈谈物理学研究》《几位物理学家的故事》(副标题略去)等3篇专业一些的文章。另外三篇里,给我印象最为深刻是《母亲和我》,虽然杨先生说因为他“写作速度极慢”,他“不再尝试(像《父亲与我》)那样展开写一篇《母亲和我》了”。但尽管只是几个片段,依然可以让读者感受到他母亲的勤劳、镇静和坚定不移,以及他对于母亲深沉而绵长的爱与怀念。
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曙光集》两种版本呈现出各自独特的价值,从版本角度来说,二者更是不可替代和或缺。作为一名读者和作为一名藏书者,我对此状况的心态迥然不同。因为过于细微,三言两语也很难说得清楚,就不啰嗦了。
其实,我挺期待《曙光集》能够有更新的版本出现。
刘政屏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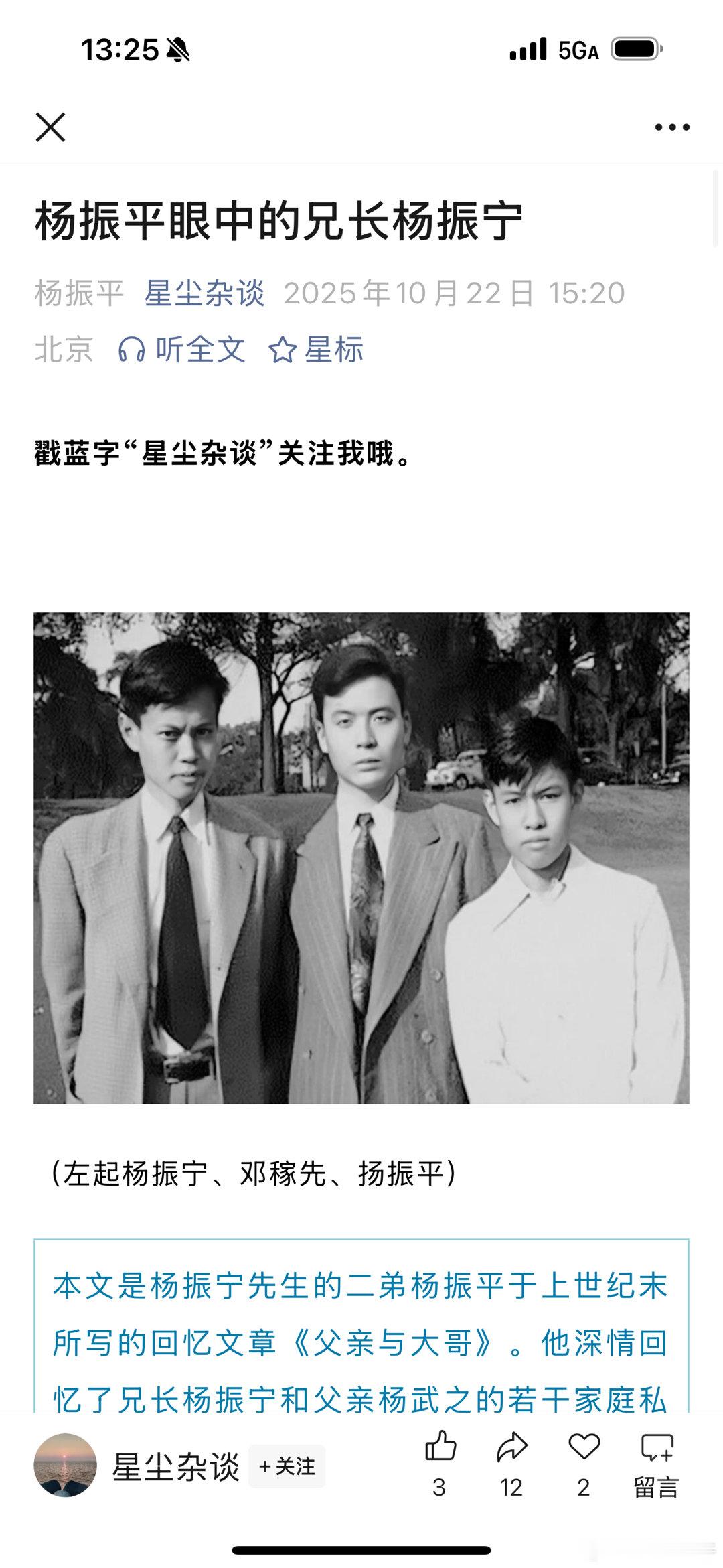






评论列表